【自由副刊】 劉旭鈞/何必朝聖,何必當真?
◎劉旭鈞
在經過惠勒堂時,朝聖者暗自等待楊牧曾提及的,一幅在雨中前往加利弗館的油畫,似乎如此場景足以構成應許的完成:所以,這裡就是一切開始的地方嗎,是牧神追隨神駒的地方嗎,是神駒死後郭松棻只能離開的地方嗎。或者,是傅柯講學、寫作、向外遊蕩以預備死亡的地方嗎。
(我跟同行的外文系友人抱怨自己這學期沒有在惠勒堂上課的命,她說,喔,所以這是它正式的名字嗎?這是她第一次聽到它的中文。我說不是。但這是楊牧翻的。)
可是站在那裡我感到羞慚,因為自己不是文學院的人,人生進出文學院的次數屈指可數:考大學那年,我站在某校的校史館前等待進入裡頭的日文系面試。一對也是來面試的母女走過來,問滿嘴御飯糰的我怎麼走去文學院,她們要去外文系。我知道是哪一條,總之就是自己走不了的那一條。進入考場我撒了一個謊,我知道自己不會再回來。
幾年後,牧神去世;又幾年,樹也去世。我發現自己沒有哀悼的資格,因為牧神只能是某些人的神。每次去那座大公園裡考試或找朋友都感到羨慕,尤其經過那片玻璃帷幕,上面寫著,活在我們所追求的同情與智慧裡。同情的意思太困難,古典學的教養太昂貴,但智慧似乎比較容易――比較容易宣稱,比較容易輕賤,且總是動輒唇槍舌劍。同情與智慧,濫情與虛偽,其實也相當和諧。
(在惠勒堂對面的大樓,修辭學系的教授聽到「阿岡本」時,不屑地指著漢娜.鄂蘭封面說:「當你能讀大師時,為何還要讀弟子?」)
另一群焦慮的人開始努力翻書,他們是言必稱理論的創作者。而時間也不厚待創作者,他們速讀然後速寫,以姓氏、概念、詞彙、主義,拼裝出另一種聲音。這是一種智慧嗎?沒有人知道,但大家都覺得自己快要沒有時間了,每個人都渴望說話。90年代爭辯過的空白與焦慮,我們在20年代共襄盛舉。
站在惠勒堂前,我也快要沒有時間了。這甚至不能說是真正的朝聖,我只是來這裡交換一年而已,就連這種事情都有所謂真朝聖與假朝聖。我告訴一位以為倪匡拿過諾獎的人,路易絲.葛綠珂明年好像會到此地誦詩,他在一週後手持詩集笑著炫耀:我就是個跟風仔。當我明確感覺到自己的情緒,我了解自己也只是濫情與虛偽的一員,戮力於區分真貨與假貨。我們也都曾聽過這樣的鬼故事:有人每隔一陣子就會被問「你是否讀過╳╳」,無論╳╳是詩歌小說或論文,無論發問者是創作者或研究生,他們心滿意足,為彼此打分數。於是我們持續在聖地以外打轉,邊轉邊遺忘那些同情與智慧、略過楊牧書寫的吳鳳、美化自己的焦慮與欲望、相信真的有聖地;甚至也許,我們也可以說服自己相信:為了朝聖,種種較量與競爭,其實也是一種同情與智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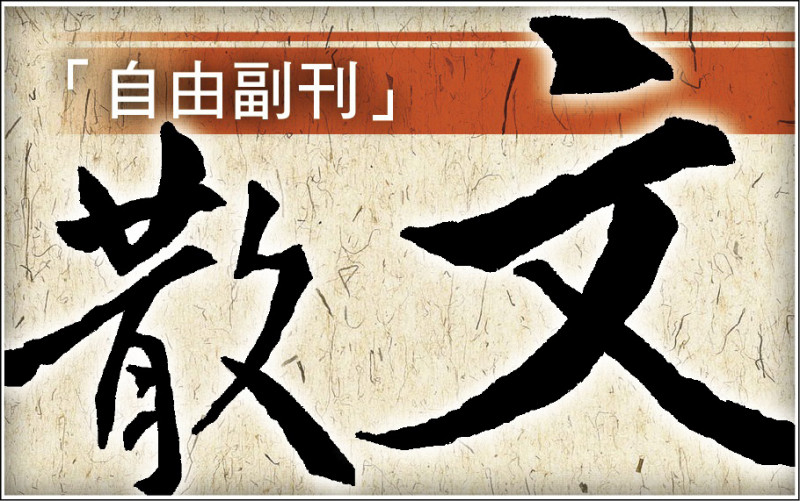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