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黃雅歆/臨終練習 - 2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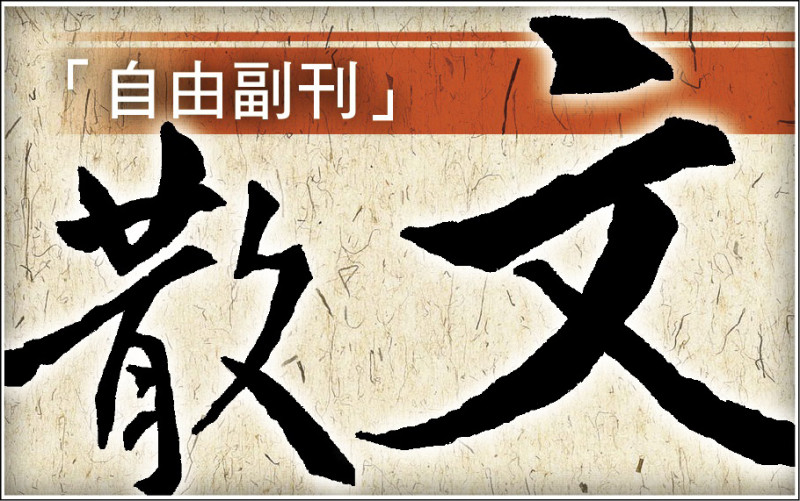 ◎黃雅歆
◎黃雅歆
◎黃雅歆
他的老妻自然還懷抱著康復一起回家的冀望,因此每每面對我們總表達難受、想要結束這一切的他,面對老妻的垂詢卻都表示尚好可接受。他的不忍成為自我生命的拔河,直到老妻覺察後同樣不忍,決定前去與他告別。
她天天到病房時都沒有哭,就是在耳邊告訴他要加油,問他會不會痛,得到不會的答案,就很安心。明白「真相」後與他講話是第一次掉眼淚,我知道她心理準備好要放手了。她跟他說謝謝你,跟你結婚六十多年很幸福很感謝沒有後悔,不要擔心我,你很痛不要忍,沒辦法再努力就不要勉強……
我便離開病房無法好好聽下去。
白首相伴不易,接受死亡不易,彼此相映的不忍讓彼此堅強。
這日之後的上午他似乎較為精神,鍾愛的孫女們圍著他說話,小孫女要回實驗室、大孫女準備搭機返回東京。他虛弱但意識如常地叮嚀,並催促著不需為他逗留。下午我們回家暫歇,狀況急轉直下,正是東京航班起飛的時刻。
我握著他的手到最後。手掌綿厚而柔軟。他沒有被送進加護病房孤單地面對、身上沒有任何管線、沒有覆面的高壓氧、不曾被綁束,維持了生命的尊嚴。這是最後一件能抗壓為他做到的事。
「安詳離世」的說法對逝者與生者都是安慰。但臨終終究不是輕描淡寫的事。我感受他喘、他費力呼吸、逐漸失去回應的能力、以及據說最後才會消失的聽覺,在耳邊告訴他放心自由。
父女的羈絆今世已修完。從此岸到彼岸,勿言來世,未需來世。
彼岸
到了彼岸的他,只能用擲筊來溝通了。但他早已寫下手諭,巍巍顫顫的筆觸,字卻依然好看,在他所能顧及的範圍下交代了身後的細節。正如他一生由內到外的一絲不苟。
所以有些儀式的對話可以變得簡單。禮儀師:「傳統上女兒是不行的。」「但是他明確寫下來了。」禮儀師:「是的,但是這樣其實不好。我必須告訴你們。」「不好,是對誰不好?」禮儀師:「對後代不好。」「後代?……後代就是我們,沒有別人。」
他從未強迫我們為他做任何事,連祖宗牌位都是「邀請」而不是「要求」,他知道這不是施予女兒的恩惠,我們也有權利說不。這些親緣上的羈絆與理解,又何嘗是習俗或外人能明白的。身後儀式裡最大的是亡者與「送亡」者,不是禮儀師法師牧師或任何性別所成立的主宰者。
但總有些零星的事還是好想問他。
想起他最後的請求是喝水,氧氣的供給讓他喉乾如灼燒,「我想喝水我好渴給我喝水好不好……」水分可以由管線注入但不是啊不是這樣,再多的水都澆不到喉間的火源。
我想起夏目漱石的晚年因長期胃病被限食,但他非常喜歡吃,曾在日記寫道:「粥也美味,餅乾也美味,燕麥粥也美味,人生能品嘗美味的餐點就是福氣。」他到病故之前都一直在央求「讓我吃東西」,卻經常不可得。嚴重內出血送醫時,「胃部突出,宛如葫蘆。」依他兒子所記,父親最後說的一句話是「我想吃東西」。於是在醫師的評估下,「給他喝了一匙葡萄酒。『好喝。』在這匙葡萄酒中,父親細細品味最後的希望,又靜靜閉上眼。」
但那時的他不能直接喝水,我又再度無情地拒絕了他。因為一點點水進入咽喉都是毒藥,都將引起劇烈的窒息嗆咳,我們只能搔不到癢處的,將浸溼的棉棒在他口腔深處與唇上繞一繞。
我所有的「無情」他都明白嗎?擲筊詢問後迅速得到了聖筊,此時始恍然,天國或樂園或亡靈的存在並非相信與不信的辯證,而是生者慰藉的需求。有些「存在」,是不存在之後才開始的。
告別式上我不發一語(對於行禮如儀我偶爾恍神),只在心裡想著:我們該如何告別呢。
父後一年不過節。在我生日以及他百日之前,我說:一起重遊舊地吧。東京電車中央線,我與他個人最後的珍貴記憶。
第一次到日本客座的那年夏天,他說要來看看我所在的地方(而此後再也無力出國了)。他是開心的,我知道;他也是不放心的,我也知道。即使我已成長不再年輕,仍永遠是個「小」女兒。
一下機我就感覺他跟著來了(是愚想也是真實),我沿路跟他說:記得這裡吧那裡吧。你那時說大學區這裡真好我說是啊是啊。後來開心在八王子買到一頂好看又實惠帽子,滿意極了說:是日本製的欸(總是在意價格也在意品質)。
經過十多年,整理遺物時它依然保存良好。遺物終需隨主人捨離,而人生需重整的,當然不只遺物。
從東京回來後,被告知體內的生命計時器忽然又啟動倒數。這次眼前的世界沒有飄浮,景物也沒有毛邊,背負的責任亦已鬆綁。他帶我走過了臨終練習,多麼令人疲憊又多麼踏實。讓我準備好隨時從此岸走向彼岸。
我沒有跟他相約在彼岸。
我們道謝,我們告別,我們一切隨風,從此都要自由。●
☆藝文新聞不漏接,按讚追蹤粉絲頁。
☆更多重要藝文新聞訊息,請上自由藝文網。
熱門賽事、球星動態不漏接
發燒文章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