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凌性傑/心裡的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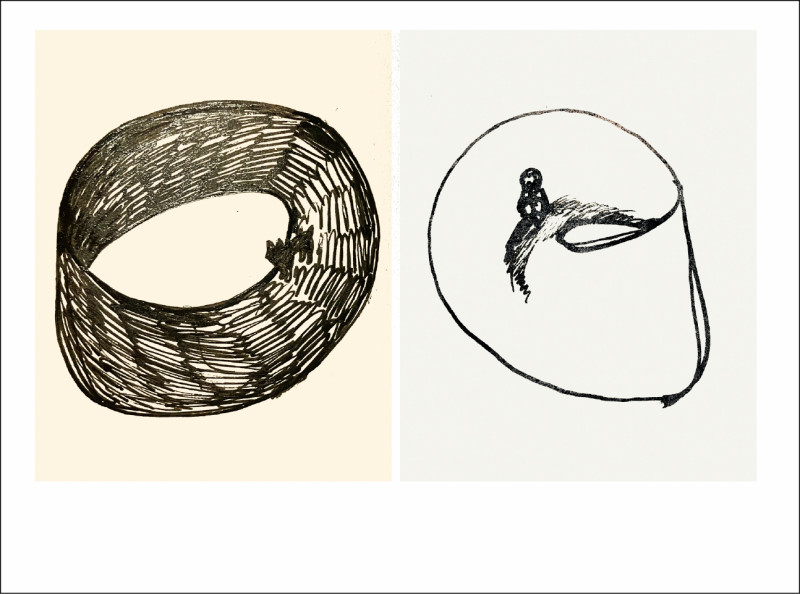 圖◎郭鑒予
圖◎郭鑒予
◎凌性傑 圖◎郭鑒予
「人生即遍路」,總在為了某些事情用盡力氣之後,我想起俳句詩人種田山頭火的這個句子。
種田山頭火(1882-1940),本名種田正一,出生於山口縣的富裕地主之家。他幼年時遭逢母親自殺,造成一輩子的陰影。二十歲那年,山頭火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就讀,兩年後因酒癮及精神耗弱退學。退學回家後的這段時間,他的父親投資失利,開始變賣田產,從此舉債度日。家庭經濟由盛轉衰,山頭火娶妻生子後又離家、離婚,一度浪遊於東京。生活困頓,他只能藉由酒精麻痺自己,往往喝到泥醉。1924年,酒醉後的山頭火,正面跳向一列正要開過來的火車,所幸火車在前方不遠處剎車停下,這才得以大難不死。這事情其實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自殺未遂。幸虧在朋友幫助之下,山頭火寄身於曹洞宗的報恩寺,受到住持望月義庵的照顧,漸漸找到安頓生命的方式。山頭火後來便在報恩寺剃度出家,成為行乞僧人。他隻影前行,漫步人生路,憑著一杖、一笠、一缽展開雲遊,足跡遍及九州、山陰、山陽、四國,亦完成四國八十八所的遍路參拜。1940年,五十八歲的種田山頭火逝世於松山市一草庵。
一直在路上修行的山頭火,曾在書信中寫道:「我只有一個人繼續蹣跚走我一個人的道路。」對他來說,活著的意義就是寫俳句,俳句就是他的生活。山頭火日記中提到,最渴求的願望只有兩個:「其一是真正寫出屬於自己的俳句。另一則是迅速往生,即使生病也不會痛苦很久,不會麻煩到別人。」一路向生命的終極意義堅定走去,這大概也是一種步行禪。閱讀山頭火的生平與俳句,我直覺聯想到電影《非誠勿擾》出現過的對話:活著就是一種修行。遍路人生的修行法門無他,唯有一步一步走下去,並且當心腳下。
為什麼說人生即遍路呢?遍路一詞,要從四國出身的弘法大師空海說起。
空海俗名佐伯真魚,774年生於讚岐國(今四國的香川縣)。804年,他登上遣唐船,隨遣唐使入唐求法。空海胸懷大志,一心尋訪名師,最後來到長安青龍寺,受業於惠果大師,繼承密宗嫡傳法脈。806年,空海在大唐留學告一段落,帶回祕法心要與珍貴典籍,從此在日本開宗立派。他的學說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為主要依據,修行法門重視念誦真言(咒語),故稱為「真言宗」。
遍路的意思是巡禮、參拜、朝聖,原是日本真言宗的修行方式之一。四國遍路是一條日本的古老朝聖路線,從空海大師以來,至今已有一千兩百年歷史。這條環島路線總長約一千四百公里,參拜行程跨越四個古國:阿波、土佐、伊予、讚岐(即今之德島縣、高知縣、愛媛縣、香川縣)。全程徒步行走,最快大約需要四十五天時間才能走完。空海大師四十二歲時,為了消解世人的災厄,巡遊四國各地布教。與弘法大師空海布教有淵源的八十八所靈場(寺院),稱為四國八十八所。發心遍路者可以依寺院番號次序參拜,也可以反方向逆序參拜,不照次序來當然也行,端看個人意願。從番號第一所的靈山寺依次走到第八十八所的大窪寺,其歷程分別代表「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四個修行階段。遍路者的草笠、香袋、金剛杖上,均標記著「同行二人」四字。金剛杖代表空海大師的化身,意謂遍路者不是孤伶伶的一個人,艱辛的修行路上一直都有空海大師相伴,所以上面寫著「同行二人」。
一千兩百年來,無數僧侶、信眾來到四國,追隨弘法大師的足跡。到了現代,四國遍路早已不只是佛教徒的修行之路,這條路線還廣受健行者與觀光客的喜愛。不分種族、性別、宗教,踏上遍路之旅,或許每個人目的不同,但其中或多或少有一種神聖的暗示──透過長時間的步行來探問自我,暫時遠離世俗功利的算計,滌淨自己的執念,獲得清明的智慧。為了鍛鍊體魄、沉澱心靈也好,為了消除悔愧、發願祈福也罷,這樣的巡禮大概也是修復、再造自我的路程。傳統的遍路是全程徒步,但後來也發展出單車騎行、搭公車電車、甚至包車這些模式完成遍路。騎單車遍路至少要十二天,開車大概也要十天左右。有旅遊業者推出遍路套裝行程,這對時間有限或行動不那麼方便的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朋友跟我說起,有信念的四國遍路者偶然相遇時,彼此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不要過問對方踏上這條遍路的理由。走上遍路,是信念的落實,也是個人儀式的開始。所謂信念,從來不會是坦途,很難輕鬆了事。起心動念要完成遍路,大概有強烈的自我鞭策作用。想必是靈魂受到敲打,才做出不得不出發的決定。上路之時或許還懷著祕不可說的罪孽,又或者是背負著深切懺悔,這一切一切的答案,自己不見得都說得清楚,問了只是徒增尷尬,有緣走在同一條路上,又何必苦苦追問。
就像有人喜歡問,為什麼寫散文,為什麼不多寫,為什麼寫這個不寫那個……?面對這些問題,我只能微笑著不說話。有一些不太懂分寸的熟人(真的只是熟人而非朋友),對我過日子的方式很有意見,並且以揣測別人的生活為樂。跟這樣的人講話心容易累,話題談不下去了,我往往選擇迴避,心思再次繞路遠走。
為什麼想去四國遍路,跟為什麼要寫散文的問題很像。路就在那裡,走不走得出去都是自己的事。想做就去做是一種自由,因為有得選擇。選擇之後要去承擔形式與束縛,似乎又不那麼自由了。
知道四國遍路的訊息之後,我一直想像著身穿白衣、頭戴草笠、持金剛杖的自己,走在一片靜默之中。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份念想始終沒有付諸行動。而心裡的曲曲折折,早就成為我的精神遍路。這心裡的遍路,既無現實的風吹日曬雨淋,也沒有耗費半點體力,但我總覺得想多了就有點疲累。某個週末午後,我與友人在西門町閒逛,邊走邊聊四國遍路的事。朋友突然說想去附近拜拜,遂一起進了天后宮。在供奉媽祖的天后宮,赫然發現有空海大師塑像,心頭震動不已。媽祖跟空海大師同在一座廟宇中受到信徒供奉,本土道教與日本佛教在此交會融合,這歷史緣由太過錯綜複雜,王曉鈴《從弘法寺到天后宮:走訪日治時期臺北朝聖之路》已經有完整的考察紀錄。此後,每當我鬱結難解,就會去西門町天后宮拜媽祖,在空海大師跟前說說話,就當是走了一趟遍路。而真正的遍路行程,還停留在設想之中。
佛教用語中有一個美麗的詞彙叫雲水,用來稱呼出家人。雲水僧也叫雲遊僧,遊歷四方的僧人彷彿行雲漂浮不定,彷彿流水自在無礙。關於雲和水的聯想太多了,我喜歡蘇東坡用行雲流水來比喻寫文章的狀態,神思該怎麼流動就怎麼流動,該怎麼停止就怎麼停止。在文字裡跋涉,我期待達到這種境界,即使耗盡力氣卻又看似毫不費力。看遍了水去雲回,那就再看看自己被歲月催逼洗磨之後還剩下多少真心。
寫散文這件事,也像是我心裡的遍路。心裡的遍路何其尷尬,明明發願要把四國八十八所走遍,結果卻是先去了其他地方。更有一種灰心的狀態,計畫中想寫的都沒寫好,寫出來的都是無可挽回的失落。也幸好有這心裡的遍路,讓失去成為一門藝術。
書寫時我相信,先安頓好自己的生活與心情,才能安頓好散文。知道一切事物有個盡頭在那裡,讓我寫散文時更無後顧之憂。曾經交會過的,我不一定都願意記得。不再往來的人,我會在心裡的遍路上跟他們鄭重告別,甚至感歎這場告別是不是來得太晚。被醜惡的人事弄到心累的時候,還好有張國榮〈沉默是金〉提供慰藉與箴言:「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繼續行灑脫地做人」。灑脫而不冒犯他人,敢於拒絕他人的冒犯及傷害,那正是我要的。
動身去澎湖花火節之前,先在自己任教的學校看了一場小型煙火。第七十六屆學生畢業典禮當晚,我看著煙花亂飛,火光出現又熄滅,一個階段已經完成,新的階段正要開始,有些人後會有期,有些人此生不必再相見。遂在手機裡寫下幾句廢話:「一起懷念吧。下次見面就是下次了,聊起過去就是過去了,現在已經開始懷念了。」在每一個當下,提醒自己回到當下,當然也是廢話。但這廢話裡有豁達,不擔憂未來,不懊悔過去,自由就在這樣的心境裡。
也許值得慶幸,已經永遠失去的那些人事物,在我心裡有另一個意義:與之相遇又分離其實並未真正失去什麼,而是藉由這諸多經歷,一起交融在生命的總和之中。
生命的總和是什麼?我不是太明白。只知道渺小脆弱如我,已經參與在這個無比開闊的總和裡。●
發燒文章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