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 陳宗暉/中途媽媽 - 2之1
◎陳宗暉 圖◎余嘉琪
繼母離家出走至今已經十二年。說她離家出走,好像也不太對,她只是從樓上搬到樓下,從此與我和父親展開分層獨居的生活。家人可以相安無事住在一起的日子,是有限的。
想起繼母剛來家裡的那一年,我還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國中生。我和妹妹都還沒適應單親家庭,就又可以假裝跟其他同學一樣,母親欄位有名字可以填寫,不必再填進那個陌生又討厭的「歿」字。
經人介紹,約會幾次,父親第一次帶她回來讓我和妹妹認識的那一天,她一進門就低聲說:「這個家怎麼都沒有裝潢?」她難道不知道這個家剛落成不久就辦了一場悠長的喪禮。
傳說中,繼母都是壞心且刻薄的,但那畢竟是別人家的傳說。癌末的媽媽在病床上向爸爸囑咐,「以後你如果要再娶,那個人,一定要對他們兩個小孩好才行。」
她是一名藥師。那時我們家被母親病逝的不安與恐懼蒙眼綑綁,父親特別重視養生與健康。藥師雖然不是醫生,但似乎也是一帖解藥。
藥師讀金庸,也讀《三國演義》、《紅樓夢》,這些父親都未曾讀過。「聽爸爸說,妳喜歡讀詩詞,也喜歡聽音樂,是古典音樂嗎?」我試圖開啟話題、向她靠攏。「我都聽搖滾樂。」話題旋即終止。她沒在客套。共同興趣只是一種話題而已,關鍵還是能不能同居相處。
隔天,父親問我和妹妹的意見,當時的我們只是覺得,家裡有一個媽媽總是比較好的。跟大家一樣總是比較好。我們都很懷念有媽媽的感覺。於是,他們還沒成為好朋友,就打算先結婚了。
那時的她和父親都還沒四十歲,卻也不得不盡快結婚成家。中年人有時也只是國中生,衝動時大家似乎都一樣。
成家很匆忙,持家很漫長。家人可以相安無事住在一起的日子是有限的。在同一個屋簷下相處太久就會忍不住吵架。
影劇新聞裡常常出現的「個性不合」,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後來,我們都在忍耐,我們都在憋氣。「我不在,對大家都好。」繼母有時會回來拿她當年沒帶走的物品。家裡維持著她離開時的模樣,她的東西沒人敢動。她說她是故意沒有一次全部拿完的,有一天總會全部拿完。
「老的時候,我會自己找一個地方去死。」她還住在樓上的時候,冷靜時也經常如此宣告。我們期待她是一個「媽媽」,但她其實沒有打算空降別人家裡擔任誰的媽媽。一開始或許也有試過,只是中途放棄了。這不是誰的錯,只是彼此不適合長久住在一起而已。沒有嘗試一起住過還真的不知道。
她是一個「中途媽媽」,偶然住進我們這個來不及裝潢的中途之家。中途媽媽只能陪你一段。小別有其必要。一年一度有其必要。遠遠問候,自己一個人也要好好生活。人與人之間,與其說血緣,不如說緣分。朋友難得,先成為朋友再說吧。我和我的繼母曾經是很好的朋友。
國中生的年紀不大不小,在學校需要朋友,在家裡需要媽媽。中午請假參加父親的婚禮,導師獲知請假事由,就算下午還要段考也只能答應。
有些長輩只會在婚喪喜慶才會遇見。我和妹妹因為晚到所以坐在角落的位子,穿著學校制服的我們,好像走進別人的婚宴,遠遠看著新娘和新郎,妝容讓他們變成我們不太熟悉的樣子。誰坐在誰的旁邊,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有人在哭,遊走在席間放聲哭泣的姑婆來到大紅圓桌旁,我們不太認識她,她卻對著我和妹妹說:「你們好可憐,怎麼會這麼可憐。」不知道她哀憐的是之前的那場喪禮還是這場熱鬧不起來的婚禮。
她的哭聲終究還是被現場的音樂聲掩蓋過去。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位姑婆。其實在場吃喝的親戚們,對我來說,大部分都是最後一次相見了,自此生離死別。大人的場合我還不懂,雖然這是自己父親的場合,然而,我和妹妹是應該在場的嗎?我不記得新郎父親的笑容。我不知道,喪偶的悲傷究竟要維持多久,才能符合大家的期待。
下午返校的時候,覺得我已經跟早上的自己不一樣了。「你中午去哪裡?」鄰座同學好奇問我。「去找我媽。」好久好久沒有說出這個單字。
那天放學回家,知道原本少了一個人的家裡從今天起就多了一個人。有點緊張,也有點雀躍。終於回到家,白天的一切好像夢境一樣。我和妹妹一放下書包就跑進爸爸的房間,齊聲喊她:「媽媽!」
她還穿著白紗裙,坐在傍晚西曬的房間地板上。「媽媽」兩個字飛撲而至,她一臉招架不住的表情,仰頭扶額,但她還是笑了。這個懵懂的新娘就這樣成為別人的媽媽,這或許是她一生中最冒險的決定。
沒有人告訴我和妹妹應該怎麼稱呼她。外婆沒有吩咐我們要不要叫她「媽媽」,外婆只是提醒我們:「吃飯前要記得叫她一起來吃。」
繼母的書櫃有一整排食譜。她怎麼練習烹飪,我們就怎麼吃。一開始其實是她煮好以後叫我們來吃。我們圍著餐桌練習當家人。繼母規定,吃飯時就專心吃飯,不能一邊看電視。白天各自上班上學,一家人也只有在晚餐時間有機會可以面對面聚在一起。也只有在這樣的四人餐桌旁,我和妹妹才得以放心說話。說今天學校發生什麼好事或壞事,摸索人際。說假日全家準備要去哪裡玩,見識地理。
從那時開始,家裡就少有客人來訪。廚房只有數量剛好的碗盤餐具,客廳只有數量剛好的室內拖鞋。家裡多了一個人,少了一群人。
在學校和同學吵架絕交,感覺孤單的時候,繼母安慰我說,書就是她從小到大最好的朋友,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
自己跟自己說話,難過的時候就寫日記。參加學校的作文比賽獲得的獎品,拆封後發現竟是女用手錶,意思好像就是要我拿去轉送給她。
除了國文老師,她是唯一支持我選填中文系的大人。「自己的決定,你要自己負責。」她語帶輕鬆地說。那時的我因此感到勇氣倍增,敢於違背父親的意見,瞞著他報名,瞞著他準備面試。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或許更能無條件支持另一個人,因為不必替他擔憂與負責。儘管如此,她還是特地買了一本新的《古文觀止》,而不是直接拿她的書櫃裡的那本舊書送給我。
一家人經常在書店裡各逛各的。從小就知道,家人是可以分開行動的。閱讀本來就是獨自的事情。一家人一起散步,直到火車站前這條大路兩旁的書店與唱片行接二連三倒閉為止。
繼母善於步行。除夕年夜飯後,夜間穿梭巷弄小路,賞閱別人家的春聯,一家人趕在子時之前,散步至土地公廟迎接廟門開。新年繼續走春,一家人一前一後,分隊散步,看別人舉家出遊,看別人聚在家裡團圓。一直走,一直走到大年初二再也沒有娘家可回,而我和妹妹也不必一天之內趕著回去兩個娘家。
可以一起散步,走很久的朋友。可以一起看風景的朋友。有一年的中秋節,我和繼母相遇在廚房,她一時興起,把燈關掉。滿月在窗外隆重誕生,好像在看一部露天電影,彼此沒有說話。那時想到的竟是一句「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無聲的溝通,有時是巧合的默契,有時是自以為是的誤解。
偶然在路上遇見國小同學,「你的新媽媽對你好嗎?」他一臉擔憂地這樣問我。那時我也笑笑沒有說話。
我們家經常以紙條溝通。廚房餐桌上,經常出現的紙條內容是:「晚餐自理!」爸爸媽媽沒有煮飯,那就自己煮。只要有食材,就不會讓自己餓到。家裡有食譜可以翻,電視裡有烹飪節目可以學。一家人各有各的廚藝,各有各的廚具,繼母添購的高級平底鍋,把手上貼著:「非主人,請勿用!」米桶裡的泡麵、罐頭與零食,都是繼母愛吃的東西。半夜肚子餓,我和妹妹有時會偷拿桶內的袋裝泡麵,捏碎直接吃。
餐桌上的紙條旁,有時會留下鈔票,那是因為他們又去外地旅遊過夜了。繼母剛拿到駕照不久,開車載父親經中橫到花蓮玩。他們兩人還需要更多的結伴旅行以培養感情。
清明節,自己去媽媽的墓地除草。繼母不掃墓,也不掃別人家的墓,可是她會在廚房鋪排一整桌賞心悅目的什錦春捲等候我們回來。她會準備水果,對我說:「拿去頂樓拜你媽媽。」
繼母的頭髮總是自己剪。有一天,繼母說她也可以幫我剪頭髮。也許是為了省錢,也許是想讓我淡忘一些事情。即使是沒有感覺的頭髮,身體也都記得。繼母熱愛打掃,擅自丟棄或轉送我們兒時留下的物品。對她來說,別人的回憶都是囤積的垃圾而已。
丟不掉的是媽媽的照片。「你們兩個都只會記得自己的媽媽。」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還活著的繼母哽咽。照片紀念的都是逝去的人事啊。(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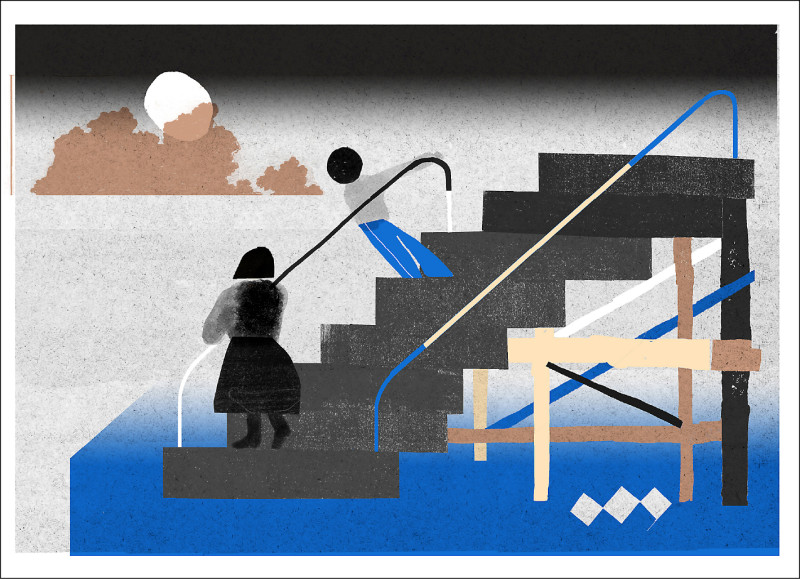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