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火與霧 〈上〉
 圖◎焯両黃
圖◎焯両黃
◎黃錦樹 圖◎焯両黃
將近二十年前我偶然寫了篇小說,虛構了一位敘事者和他那因左傾而被軍警圍剿重傷、以致孤獨地死於叢林的沼澤裡的哥哥;而受困於獨自發現的祕密的敘事者此後自我流放於台灣、困於中國上古文字的隱微幽密,再也不曾返鄉。
但我每回返鄉,都有想再去看看的衝動,如同探視故人。
那片沼澤一直都在的。因位於火車路旁,應該是受保護的國有地,這一帶僅有的雨林畸零地。而那條建於殖民地時代、連接新加坡與吉隆坡的鐵路,數十年來沒有什麼改變,依舊單軌,依然鏽色。不管這幾十年來大馬賺了多少外匯,鐵路和公家醫院還懷舊似地維持著殖民時代的超低水平。據說它還在默默地在等待中國把它升級成高鐵,好讓北方的客人可以從西伯利亞一路奔向新加坡,那古陸塊盡頭的城市。
每回返鄉都會去看看舊家遺址,雖然舊園的面貌已非舊觀。
它早已是三哥的火龍果園了。
三哥是母親眾多兒子中,唯一不曾離家到外頭闖蕩的。小學畢業即到鎮上去當店員,換過幾家店;年歲稍長,隨二哥做燒焊鐵工,做了好多年。在我成長的年歲,常看到他在二哥調不到工人時,他都忠心耿耿地陪著他哥哥加班,再怎麼重大的假日都不例外。有時聽他們說凌晨即出發,往北直奔向國北邊陲的園坵,紅毛人的油棕廠只有那樣的假日休息,需在那期間把工作做好,兩兄弟回到家時一身油汙惡臭。
兩兄弟均因暴食而腆著大肚腩,吃得既快又多,數十年如一日。
但每年年終,二哥多賺的錢足以讓他換一輛進口車,舊車直接折抵給車商。而多年來,三哥都只騎一輛很普通的機車,後來我們騎的舊車也是他留給我們的。不只一次聽他感慨說他的工人朋友某某因為有車子就載得到女孩子,多年困在樹林裡,也不曾聽說他有女友。
母親屢屢感慨說:三哥賺沒錢。一直為他的婚姻操心,心疼他「頭燒耳熱」時沒人照顧、衣服在幾個姊妹出嫁後即沒人幫他洗。
而他每個月要拿出大概十分之一的薪水貼補家用,下班時偶爾還會順道買些肉回家。
許多年裡的週末或假日,他都會邀我們這些弟弟大老遠地到鎮上電影院去看電影(多是些俗濫的港片),看完電影去吃雲吞麵,都是他付的錢。
一起到外頭吃飯,一貫是由他買單的。
他也一貫地以我們做為他虛擬的談話對象,心情好時滔滔不絕地說著他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政治議題,執政黨或反對黨某某的私事,明星的緋聞,富豪的私生活……很可能直接來自做工時同儕的閒談。
但如果他心情不好,就會板著一張殺人犯似的臭臉,彷彿可以看到那上頭冒著一股熱騰騰的黑氣。
之後他不跟二哥做了,轉行做「土水」,仍舊住在家裡。家裡發電機壞了或什麼特重的東西要搬動,都倚賴他的力氣。深夜暗林中有什麼風吹草動,相較於瘦弱的父親,他是真正安定的力量。
畢業那年,在等待留學的空檔裡,我隨著他到建築工地去當雜工,希望可以賺到一些旅費。
因我反應非常遲鈍,老闆屢屢當我的面說:「做工要用腦,你哥的腦真好,講一遍就會了。」而他看到我又犯錯時,便趕緊過來示範一下正確的做法,只輕輕地說了句:「以後不要那樣做,而是這樣做。」那時才知道短短數年他已深得工頭兼老闆的器重,把全部功夫大都傳授給他了。
午餐的錢,茶點的錢,他都毫不猶豫地付了。
但不知道後來為什麼他又放棄了水泥,回去和二哥做鐵工。母親的說法是,二哥長期工人不足,一直叫他回去。他一直是個很聽話的弟弟。
「沒有人願意陪他假日加班,只有這個弟弟不計較,肯陪他做最髒最辛苦的工作。」
二哥繼續換車,且買了大房子。
聽說他貸款買了輛小車,非常開心。排隊買了間廉價屋。
又一年,聽說他把廉價屋出脫,貸款買了間新蓋花園屋的角頭間。
母親說他工作時從四樓墜下,幸虧一隻手抓到鷹架,沒摔死,但脊椎卻嚴重拉傷了,再不能提重物。一直猶豫要不要去動手術。如果動手術,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工作,擔心房子會不保。
那時我已出來工作,還沒有任何貸款。我跟母親說,如果他要開刀,療養期間房貸就由我幫他繳吧。但他還是沒敢去開刀,他聽說馬來西亞的醫院一向成功率不高,很多病人即使能活著離開病房,也癱瘓了。
痛時吃止痛藥撐著。後來也一直一跛一跛的。
年歲漸大,不能再做粗活,考慮轉行。
在父親死亡的次年,母親透過管道幫他娶了太太,是個印尼華裔。他辭了鐵工,打算轉行務農。母親為他向可能出錢的孩子徵募基金,對象都是他的弟弟妹妹們,說來組個公司吧。以舊園為基礎,在務農有所成的小哥的協助下。因而那年返鄉,發現記憶中的樹和房子都不見了,「吃驚」兩個字不足以形容那種震撼。那榴槤,那芒果,那山竹,那紅毛丹,毫不留情地剷除了。如果父親還在,一定不會是這個樣子。但如果他還在,一定也是老病纏身,且飽受親人的冷漠的折磨,一如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的狀況。母親病後的這些年一定也深深地領略了,成年的子女無法充分地回應伊對於愛與呵護的需求。
當然沒有人會問我的意見,連知會都沒有──連我幾個弟弟妹妹結婚,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往好處想,都是為了讓我免於奔波。
自離鄉念書後,每回見面,都可以感受到他日益增強的冷漠。有時甚至流露出遠超過冷漠的嫌惡,「你們這些出國念書的,哼!」也許平日母親經常在他們面前熱烈地稱讚我們在社會上僥倖得到的一點虛幻的名聲吧。
聽說他當了爸爸。嫂子生了個女兒。又一個女兒。再一個女兒。有一年我適回鄉,聽到母親和她女兒的電話裡說,「沒魚蝦也好。」
聽說他確診罹糖尿病。暴瘦。
為了防盜,那園子被鐵籬笆圍了起來,進出都要開鎖、上鎖。裡頭養了一大群狗,聘了兩位印尼外勞,就住在園子裡。
去年因二姊夫猝逝,二嫂乳癌復發病危、母親病倒而隻身返鄉看看。駕照早已作廢,仍偷偷騎著機車到處逛。想到舊園看看,也向正要到園裡去的三嫂說了,她開著車先到園裡去。離鄉太久,不免生疏,拐錯了一個園,拐到另一塊長滿雜草的園子去了。待到找到正確的路,機車在軟爛的山路扭來扭去地抵達時,卻發現嫂嫂已把鐵門的大鎖牢牢地鎖上了。我原以為她會虛扣著。
熄了火,依稀聽到狗吠聲,但沒有看到人的動靜。
他們工作所在的鐵皮寮離我在的位置有數百米遠,喊叫也是徒然。我發了一會呆。鐵籬笆內側,從前父親種了幾行咖啡樹,花開時蜜蜂嗡鬧,白花馥郁。我身後那片膠林,樹都很老了,樹身的傷痕縱橫交錯、墨黑,有一種說不出的衰敗的感覺。那膠園裡的舊寮子還在,還是水泥的牆。園主是一對恩愛夫妻,妻子微胖、見到人總是笑嘻嘻的。夫妻倆每日一起割膠,同進同出,但多年前那年輕的太太心臟病猝逝,那位先生從此愁容度日,獨自割膠、收膠,在寮子裡發呆,大概也免不了喝燒酒吧。
只好倒車,只聽見乾涸溝渠層積的落葉堆嘩的一聲響,一隻四腳蛇正仰頭往隔壁園裡灌木叢竄。機車發動時,草叢裡更驚起一窩雉。公雞拖著長長的尾巴,飛到高枝,母雉和小雞落在較低短的樹幹上。
與舊園毗鄰的那塊膠園,父母口中的「潮州芭」,地主是潮州人,子女分散在多個國家。據說因產權問題複雜一直沒被建商買去「開發」,因而一直處於較原始的狀態。多半也因為不臨路。多年來雜木密密實實地長起來,有的長成和老膠樹一般高的大樹了,高高拔起的麵包樹、芒果、榴槤、尖刺懾人的黃藤、一種果實幹生纍纍的無花果,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熱帶雜木。
那裡仍然有人割膠,就在樹旁劈出獸徑般的窄道。
潮州芭旁是另一塊膠園,那裡雜草都被除草劑清除得乾乾淨淨的,膠樹的割痕也是新的,林中的小徑也清晰可辨。打從機車一進入林子,就發現有一大群小猴子沿著樹梢從四方悄悄地圍了過來。仔細看看,小猴子還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不過是土地公大小,小的如小貓,母猴抱在懷裡,看來是一家子,有二、三十隻之多。一度牠們靠得非常近,圍繞著我移動。頭頂上的樹梢不斷發出聲響,枝葉彈動,從一棵樹跳過另一棵樹,一點都不怕生,和園主之間的互動應該很好。
經過園中的小工寮,鐵皮屋頂外,三面鐵皮都圍了半截。裡頭空蕩蕩的,大概只做為停機車、放膠桶之用。
到路的盡頭我停下,停好機車,猴群也就止息在機車旁的幾棵樹上,竊竊私語。
牠們沒有跟上來。
撥開灌木,我信步走進潮州芭,但樹實在太密了,根本不可能趨近舊園。連籬笆也近不了。想想也沒什麼意思,就退出來了。
沿著路的盡頭再往裡走,橡膠樹沒了,零落的幾棵大小不一的雜木,一看葉形,是台灣也很常見的江某。憑著記憶去尋找那條源自沼澤的小水溝,雜草間有一汪綠色的小水窪,一根老而矮的江某樹繁葉茂地守護著。小水溝勉強淌著流水,穿過草莖,厚厚的一層鏽。沒有看到魚。水溝上架了根廢枕木,鐵道隱約可見。
小水溝的源頭的那片沼澤就在不遠處,另一塊膠園的盡頭。幾年前返鄉,拜訪一位在附近租地種植玉米的姻親時,偶然發現他租的那塊地的盡頭恰是那片沼澤,但那地方已騰出一大片明亮的天空。他逕直把租來的地延伸到鐵道旁,用挖土機把那一小片僅存的雨林給剷除了。樹的屍骸,一堆堆的,之間是一灘灘綠色的死水。
返程順道去看了二嫂。二哥搬了新家以為可以改善風水,但二嫂乳癌復發治療仍舊失敗。已是癌末,瘦弱軟癱得無法站起來,化療讓她落盡了猶未白的髮。她家寬敞的客廳擺了張床墊,白日他把她從房裡抱出來放在那張墊子上,不停歇地開著電視。已婚的姪女帶著三個孩子陪伴她母親,侍候她吃、喝、拉、撒。不到五十的她,被迫等待死亡。
那年她初嫁,不過十八歲,還是個清秀瘦弱的少女,但已經懷孕多個月了。二哥用「先下手為強」的絕招把她娶過來,在膠林裡與他暴躁的弟弟、嚴苛的母親同住,辛苦地適應他們多年養成的生活習慣(不乏惡習),被塑造得逆來順受,隨遇而安,也是個幾乎百依百順的妻子。
返鄉那些天,我每日的標準行程便是如此。早上去看看母親,之後去看看嫂嫂,接下來的時間便空蕩蕩而百無聊賴了。有時回頭去陪母親,聽她重播她的抱怨。
中風後的母親情感上變得非常倚賴,那陣子她住三哥家。
角頭間的花園洋房,還算滿寬敞的,屋旁還有一小片地。門口種了棵芒果樹,我記得那棵芒果樹,每趟返鄉都看到它的成長,總是結實纍纍。
三哥家打從鐵門一打開,從車庫開始就堆滿雜物,各式各樣的機械零件、電鑽、馬達、割草機、鋤頭、鎌刀……油漆機油、肥料、農藥、包裝紙等,一直堆到屋裡。再從客廳堆到廚房,從茶葉到不知道什麼大包小包的。不理人的小女孩們,如果不是在吃飯、邊看電視邊做功課,就是打電動。
如果早上太早去,或晚上過去,三哥夫婦都會在的,三哥已恢復以前的胖了,總是專注地看著電視。他們經常帶外食,席地而吃,在一堆報紙茶壺間。我們沒聊上幾句話,好像都天性沉默寡言,或是初識。(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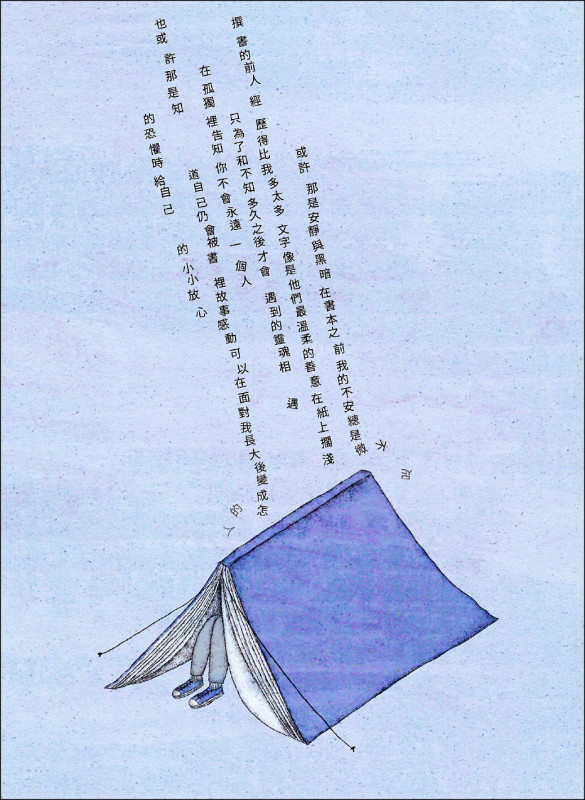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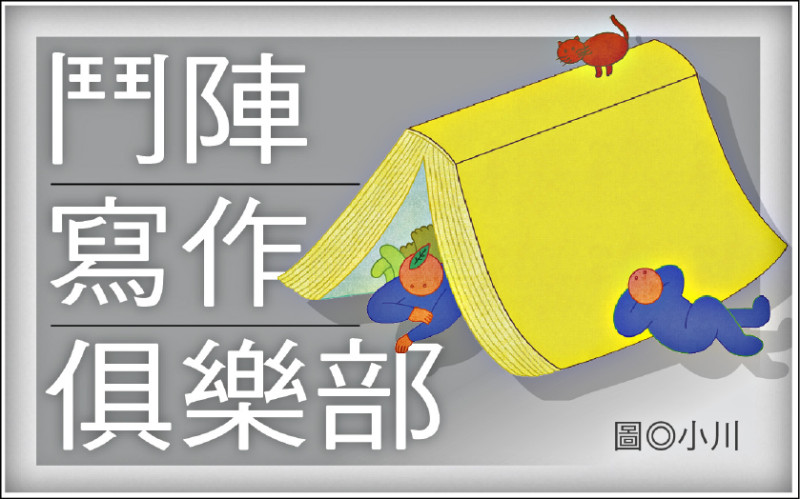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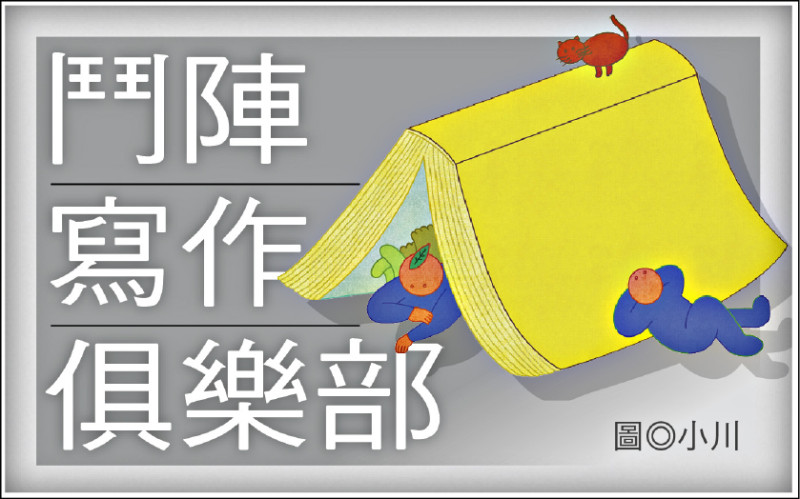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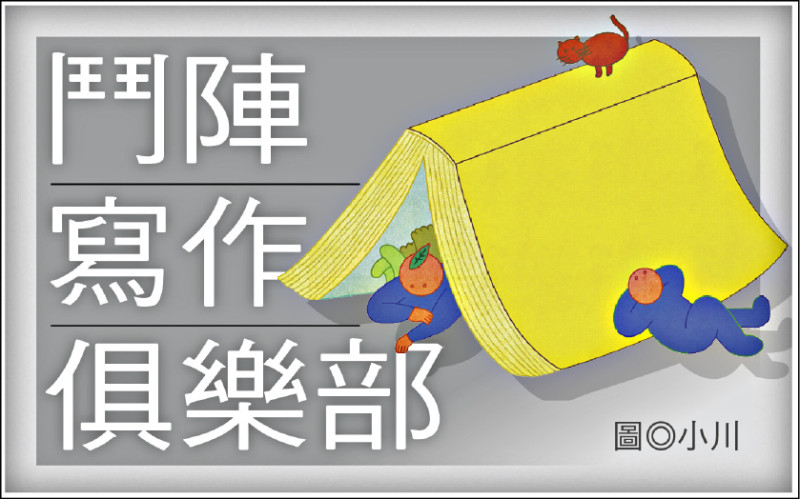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