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猴蔗花開
◎阿默 圖◎書卷
少年時期,每天行走往返於學校與家之間的濁水溪底,看溪水由湯湯漭夏到湉湉寒冬,看甜根子草由茁茁然的酣春到花絮翻飛的靜秋,順著溪流往前看,天邊不時出現鑲著霞光的雲彩,回頭望,崖谷盡處是巍巍玉山。少年的自己常凝眉思索,天下何其之大,我,將何去何從?國中畢業之後,隨著對門的吳雪娥到台北投靠她的姑姑,姑姑家住在大直低矮的眷村裡,白天姑姑擠進屋簷下搭出的小廚房裡炒菜,晚上餐桌挪開鋪上鋪蓋就是我們兩個女孩睡覺的地方。姑丈是位敦厚溫和的長輩,幾天後幫我們各找到幫傭的工作,雪娥讓一輛豪華的轎車接往松山,而我的雇主羅太太在中學任職,教我用手撕開潔美嫩黃的高麗菜,丟入大蒜辣椒片兒爆香的鍋裡,灑上鎮江烏醋炒成酸辣玻璃菜,教我揉麵糰成皮兒加餡包成胖胖的餃子,要我喊她身懷六甲的媳婦少奶奶,雇用我是因為準備照顧即將出生的小娃兒。
當羅家所有的人都上班了之後,我一個人清掃屋內,洗衣澆花、煮中飯給自己吃,空餘的時間就坐在大餐桌前讀著從家鄉帶來的書,或寫信寫日記,等待黃昏時太太買菜回來,依她的交代做晚餐,晚上羅家的人大都圍坐在電視機前團聚,邊吃著昂貴的富士蘋果,邊聊雷恩歐尼爾在《小城風雨》裡的演技,而我則回到屬於自己的小房間裡拿筆在月曆上將當日畫去,思念家鄉的愁漸濃漸苦。羅家的小姐明白一個孩子從鄉下初初進到都市裡的徬徨心情,不時趁沒事的晚上帶我散步到師大對面金山街邊上去吃一碗紅燒牛肉湯麵,那些日子裡,那一碗麵倒成了我的安慰。
羅家大少爺在瑞芳擁有一家紡織廠,少奶奶則是外商公司的祕書,很得老闆器重,當她生下小艾的時候,十七歲的我隨著他們一家三口搬回永和與她的母親同住,外婆姓殷是貴州人,炒得一手好菜,可當她歪在椅子上翹起二郎腿,不發一言邊吸著香菸,邊拿她那銳利的眼瞧人時,著實令人不寒而慄。
大多時候外婆許是嫌我笨拙不讓我做家事,只要我抱著、哄著小艾就行,當外婆約了牌搭子來家裡打牌時,抱著小艾我到鄰家去看梅香將一個一個塑膠零件組成一枝俗艷的花,滿客廳一簍一簍紅的花綠的葉,不懂何以梅香的雇主願意讓自己的客廳成為她的工廠。
有一次,抱著小艾我走過馬路,彎進一道荒涼的小徑去找在巷子裡幫各家洗衣的阿儉,去的時候太陽正在偏西的當兒,小艾洗過澡的身子在和煦的陽光裡散發著嬰兒香皂的香味兒,來到阿儉臨時搭建低矮的家,她的四個小孩在門口玩耍,最大的一個男孩揮著木棒的模樣兒和年紀都像極了我的弟弟,進屋看見阿儉正在煙裡煮飯,從牆板隙縫透進來的光影中漂浮著煙塵,也漂浮著阿儉臉上憨然的笑容,牆上掛著的一隻長著綠霉的火腿,這些情景讓我想到遙遠窮鄉僻壤裡的我的父母、我的家。
想家是一回事, 心中的苦悶是一回事,當時是這麼清楚地知道著。
另一個苦悶的人是外婆的兒子,一方面在台大念書,一方面已在商職夜校教書,是一個跟姊姊一樣優秀的青年,然不知為何他總是在長時間埋首書堆之後仰天長嘯:「媽!我恨妳!」一開始聽得我膽戰心驚,不知所措。後來漸漸了解這個家的情況,當初迫於情況緊急,外婆一人帶著三個兒女隨政府撤退來台,其中最小的男孩還在襁褓之中,家鄉還留有未及攜出的長子與隨軍在外的丈夫,二十餘年來的思念牽掛加上生活煎熬,折磨得她不成人形,性格大變,接著兩個女兒陸續成婚離家,宛似「寡母孤兒」的母子相處更形困難。
外婆沉默地接受著一聲聲「媽!我恨妳!」,在幫小艾洗澡、餵食時乾癟的臉上卻常現著喜悅歡愉的笑容,這也許是少奶奶之所以努力克服萬難一心想要搬回娘家住的原因吧!回想起來,處在這樣的家庭,對心智依然單純的我有些困難,努力適應之餘偶爾也會感歎自己的十八歲,正值嫩紅纖綠的青春,應當在中學裡讀〈長恨歌〉,應當背著背包與同年齡的男孩女孩,在橫貫公路上跟隨救國團飄蕩的旗子健走,然而我沒有;難得放假回鄉時,母親握著我的手流淚,自責地說生活讓我成為三十歲的婦人,可這幫傭的工作其實很好,羅家待人是寬厚的,而外婆性情雖怪異我知道她其實是愛護我的,寄人籬下使年輕的我有著深刻的體驗,這當中夾雜著自己認定的奮鬥意志與不解事的自尊,一方面安慰自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方面又為著星蒜事兒,咬著嘴唇哭濕了枕頭,年輕、矛盾而幼稚的心時時謹慎防備著,卻又熱情地準備隨時打開。
有時看著懷裡熟睡的小艾,想著,設若有一天我離開了這裡,幼小的她將不知曾經有我抱著她在黃昏的夕照裡將臉埋進她肉肉的胸前,聞著她身上的香息,更將忘記在她生命之初曾經咯咯笑著對我伸出全然信任的胖小手,迎著我對她的擁抱。
只是,在我處的小角落裡,面對台北如許繁華的巨大城市一直有被淹沒的感覺,卻又不甘於如此輕易放棄,請了半天假搭車到樹林找到在成衣廠任車縫工的同學,到的當時還是她們上工時間,強烈日光燈照耀下數百坪空間堆積著成品、半成品衣物與少數走動的女工,大多數的女孩子們埋首車縫機與衣物堆裡快速地完成屬於自己的部分,廠房裡除了咧咧機器聲就是比之更高分貝的收音機聲音,震耳欲聾。同學一邊熟練地將衣領子車上衣身一邊大聲地詢問我想不要過來工作:「論件計酬,每天加班的話……一個月大約可以領到一千兩百塊。」回永和的路上街燈漸次亮起,當公車司機急急將車駛上大橋時,一輪濛著街塵的落日正黯然沒入樓宇林立的西邊天際,凝望著新店溪緩緩流動的水紋不禁思念起家鄉濁水溪的黃昏,額頭貼著車窗任由喉嚨漸緊鼻頭漸酸……在這樣的日子裡接到父親從家鄉寄來的信是莫大的安慰,身分證背面的學歷欄僅寫著「識字」的父親信寫來簡短而有力:「兒!在台北好吧?家中極好,稻已在上月收割,幾日前橋又流走,近日勿回家。」信尾署名「父字」,父親總單方面地認定我隨時可以回家,信裡總會交代路況,擔憂地無非是怕回鄉的孩子會望著獨浪翻騰的溪因無路可回而焦慮。另一天裡接到父親的信卻囑咐我回家,那是另一個工作機會他已為我報名了,我必須回鄉參加考試,就這樣斷然離開了台北市,至今三十年不曾重回台北,不曾好好再看一眼讓我度過愁苦年少的街市。
如今,寄居台北市的生活早成了塵封的歲月,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將之保留在心裡的一個角落裡。大直的姑姑在她父母相繼離世後已不再回鄉,羅家的消息也只剩下財經新聞裡股票行情的一欄,想來小艾定然在優渥的生活中長大、接受教育甚至結婚生子,不清楚我在照顧她時是否只是把她當成工作的對象,確定的是她陪伴我度過甚長的苦悶時期,她跟我兩個世界唯一聯繫的是我的思念,在年年的思念裡我描繪著她七歲長髮著公主裝的模樣,算記著她讀國中、高中或進大學的時候,時常我會翻開案上那本封面泛黃斑駁的《辭彙》,底頁用稚嫩的筆跡寫著「民國六十二年,購於永和」,正是小艾出生的那年,如今她三十餘歲該是個成熟的大女孩,是不是像我女兒這般模樣兒?美麗、纖細、專注……這時節濁水溪猴蔗又花開似雪,當年懷抱著小艾時心裡惦念的正是這連綿的花海,而今卻每年看花想小艾。
噯!小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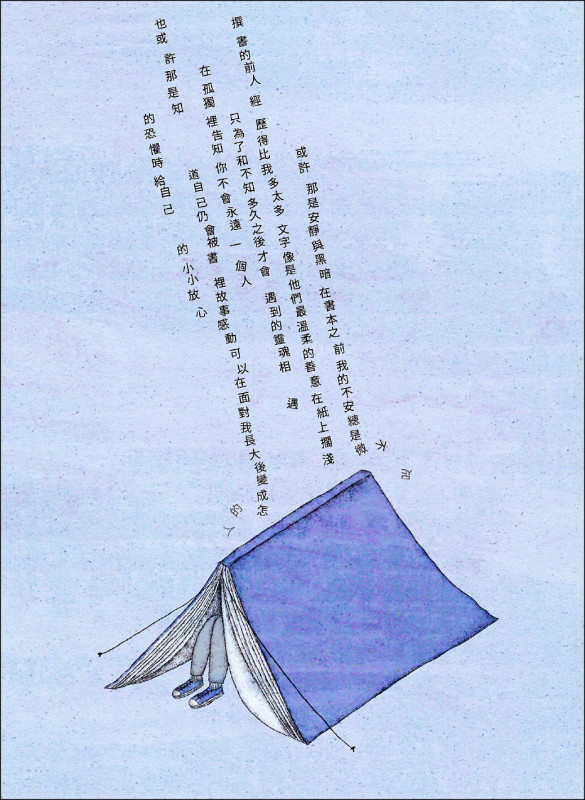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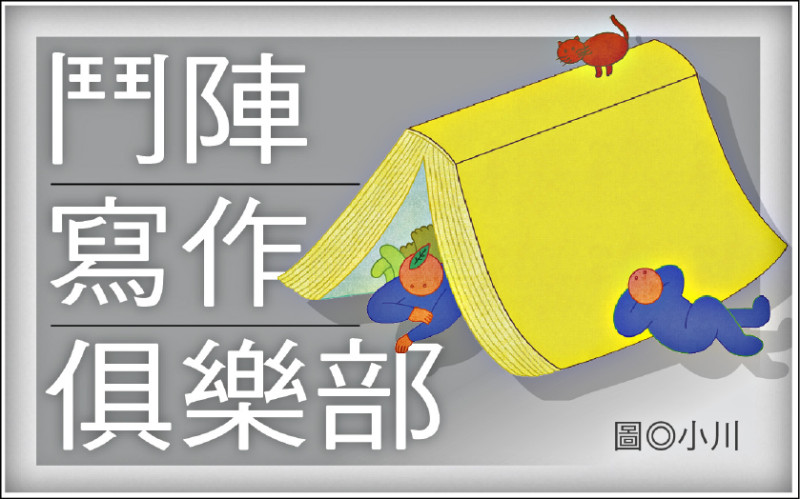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