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屋頂
◎脫貝殼 圖◎阿尼默
若一鏡能夠到底,先會看到從門透進的光照亮鐵皮屋內的所有細節。脫絮般毀損的石棉瓦屋頂,因水滲漏鏽蝕的鐵條支架。沿著水塔壁緣用磚塊砌出的兩間房,在幾何學的限制下無法自成封閉空間,其中的一間住著我,另一間堆置雜物。站在走廊的一端往盡頭看去,留在記憶中的永遠是對比驚人的光亮室外。不同於高感光的影像紀錄,光亮室外有株桃樹,很清晰,並不像電影中的畫面會讓強光吃掉細微的枝葉。桃樹愈長愈大,已經沒有滿足它生長的器皿。如今,桃樹被養在廢棄的浴缸內,很旺盛活著,體格又美又壯,不輸活在農場中的桃樹。
我爸的解釋:「每一種植物都有成長的極限。」像樟樹或茄冬,整間屋子裝滿土也不夠它長,因此在自家屋頂種這類樹種,就以賞形為主,搭配的盆與景才是重點。而桃樹無形,養它就是要結果,要滿足這類野趣非得先滿足桃樹的生長不可。而我們這個家的成長,也像屋頂這些旺盛的植物。家中第三個小孩誕生後,父親找來他的朋友在屋頂搭起鐵皮屋,占去原有半個屋頂,所有的植物被移到另一邊去。在我搬上來住的前一個晚上,父親對我說:「看,你終於有自己的空間。」那年我剛升國中,因童年驟離而深感不安,並不了解「自己的空間」有多了不起。半年內,潮溼的水塔誘發我的過敏性鼻炎,在夜裡,幾乎是吃著鼻涕睡去。
那之後的每一天,我放學回家必須負責所有盆栽的澆水。父親還要我將尿液留在奶粉罐中,每隔幾日將奶粉罐中的尿液倒至水桶以一比十的比例稀釋,平均分配在每株植物。我成了園丁,也像是農場主人,孤獨享用水泥叢林中的旺盛綠意。某日下樓用餐,在餐後的閒談中,父親無來由說到:「最好的飲料,是將香蕉皮打成果汁喝下。」我感到莫名的認同,似乎這個理論是每個人都該知道的。夜裡,我突然覺得父親的香蕉皮理論來自於隔壁儲藏室。我用輕緩的步伐走進儲藏室,拿出夾放於角落藤椅底下的色情雜誌,確認父親所說「最好的飲料」,其實是雜誌內推薦的壯陽偏方。在那之後的幾年,我們父子倆很有默契地利用「角落的藤椅」交換最新閱讀的色情雜誌。一直到我離家讀大學後,鐵皮屋被拆,我們都沒揭穿這件事。
有一陣子,在屋頂蓋鐵皮屋變成流行。很快地,多了一間鐵皮屋在隔壁。我也多了一個鄰居,是個中年女人。女人的作息與我顛倒,我會在上課的路途中遇見她走回來。或者是下課後,在我澆水的同時,碰上她出門。
她身上總有濃郁的香水,低調的眼神,與勉強的笑容。我想,祕密就像塑膠袋裡頭的金魚,悶在裡頭還能活上一陣子,一旦戳破了,可就沒了。女人有時不用出門上班,見到我出來澆水,多半會自動進入屋內。那一天,她手倚在半人高的圍牆上看著我澆水,她不在意圍牆邊的尿桶騷味。也許看出我的緊張,她率先打破沉默。
「小弟,可以剪幾朵開過的曇花給我嗎?」女人指向垂沉無力的白色花瓣說。
「喔。」我繼續往桃樹根灌水。
「小弟,我喉嚨不舒服,人家說開過的曇花與冰糖熬成湯很有效。」「我沒有剪刀,妳自己過來剪。」女人回到屋內拿出剪刀,一開始想遞給我,但看我還在澆另面牆邊的絲瓜藤架,便決定自己翻過牆來。那一刻讓時間暫停。尤其當我看到女人只穿件內褲,蹲在一具具垂下的曇花前。
「小弟,我可以剪幾朵?」她左手扶托起白底透紅的花瓣,腳下穿著黑膠高底涼鞋。我聞不到她慣有的香味,空氣中只有土壤浸過水的味。
「隨便!」我儘快將頭轉回,不小心又讓水柱噴斷絲瓜藤上的花苞。
「那我先剪下兩個,有用的話再過來剪喔。」女人翻了牆進屋。
夜裡,女人敲了我的窗子,遞進一碗熱騰騰的湯。冰糖的香氣裡有曇花含蘊,她說小時候曇花開畢,人們將其剪下,熬成湯後互相分送。她看屋頂花開花腐,覺得浪費,所以找個藉口剪花熬湯。此刻的她又像是一位大嬸般親切,我一邊吹著湯一邊想著。
那天,對於女人身體的奇探窺視不再侷限於雜誌中那些誇耀悖實的肢體動作,而是活生生地活在這面牆的背後。那之後的許多個晚上,有個夢境反覆出現:那女人化身為農婦,不斷笑著對我撒米,而我,只是一隻小小雞。
母親開始對著父親抱怨,說太多的盆栽,太重,壓得屋頂受不了開始漏水。父親反駁太重的是那間鐵皮屋,更何況現在有兩間,難道要把鐵皮屋拆了讓我搬下來住嗎?「哇,原來我早已不跟你們住在一塊了。」我想。
那天,我刻意不清理排水口,讓水淹滿了屋頂。
「水災了,水災了。」女人的聲音傳來,她又穿著內褲坐在圍牆上。
「妳不用上班嗎?」「一個月總有些時候不用上班。」女人指了指內褲的位置。
「那妳也不要只穿件內褲吧?」「不希望弄髒衣服,反正沒人會到屋頂。」女人跳了下來,走近絲瓜藤架。「才一個月,就長了這麼多絲瓜。小弟,你真是會照顧。給我一條絲瓜好不好?」「拿去吧,反正我們家吃不了這麼多。」那個晚上,雨開始下。下得很怨又恨,父親打電話上來。說是颱風接近了,要我出去把盆栽搬進來。我出了另一道門,發覺風雨大得誇張,我先看到女人站在門外,我對著她吼,要她進屋內。她指向屋頂,我才知道她的屋頂不知被那來的鐵皮扎破。
「先進來我這邊吧!」我轉頭看了看絲瓜藤架,毀得差不多了。
「不行,我的衣服都在裡頭。」女人的臉看起來像在哭。
「那我幫妳搬過來。」我翻了牆過去。女人依舊穿著內褲,只不過雨水淋濕她的身體,她的內褲被染得紅紅的。
「算了,你不用幫我。」「不行啦,這樣不行啦。」我進了她的屋子看,一張床與桌,靠牆的衣櫃與電鍋、碗筷,這就是全部了。水順著鐵皮扎破的洞流入屋內,一切都濕了。
女人進屋,坐在床邊,水淹過她與我的腳踝。屋內的燈也熄了,風雨聲交雜她的啜泣聲。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不久後我父親拿著手電筒進來,他照了照女人,然後抓住我,帶我回到隔壁樓下。隔天我再回到屋頂,雨停了,女人不見了,桃樹仍舊精神地活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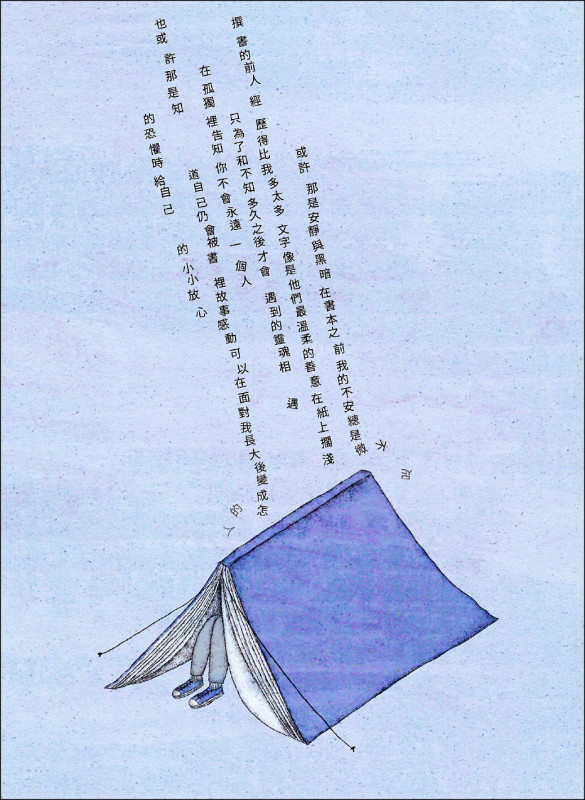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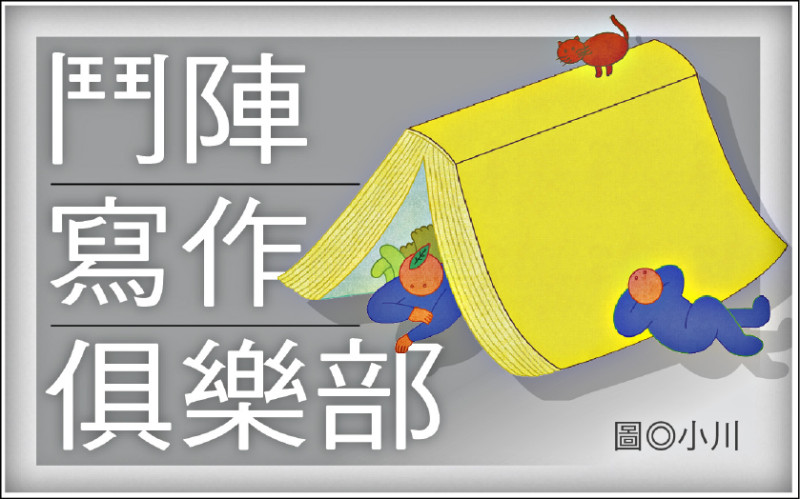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