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摯敵
我誠摯以對的仇敵-中
〈閱讀小說〉◎胡淑雯 圖◎吳孟芸
天空奄奄一息,大雨又要下了。權勢者懶得提供任何友善的手勢。
這理直氣壯的蔑視,就是我爸告訴我的,比沉默更嚴厲的沉默。像一片久病不癒的皮膚,呼不出一口乾淨的空氣。
我父親只能默守他寡言的習慣,把伸出的右手收回、收回、收回他所來自並且終將歸屬的、不可離越的那個空間。退回、退回、退回界線這邊。
此後我便暗自,將王子視做仇敵。鍛鍊我的眼神,眼白、眼珠、眼白與眼珠的比例,付出卑屈之人對卑鄙之人的、卑屈的鄙視。但是,我該如何有效傳達我的鄙視,像一個高明的球員那樣,把球準確地傳到對方手中?──妳如何懲罰報復一個、對妳無動於衷的人呢?王子看不見我的鄙視,因為他根本就不看我。他對女孩的品味,就像任何精準的投資行為一樣毫不浪費,只將注意力交給與他同類之人、同位同階之人。
我的鄙視像一個又一個被漏接的球,跟父親伸出的右手一樣,在等待中一再一再落空。等得太久,於是連等待也算不上了。
復仇行動輾轉反側,流連退化,成了空想。我幻想與王子接吻的一刻,咬破他嘴唇並且摀著鼻子說,你的嘴巴有惡臭──先有征服,才有宰制,先有暴力的施展,才有關係的扭轉,但是王子並不,並不回應我的幻想,獨留我陷落在自己的角色當中,入戲很深,強扮勇敢好戰的女兒,不畏低俗地記取仇恨,在發出惡臭的黑暗當中匍匐,匍匐於孩子氣的復仇行動。
我幻想他捧著一份赤誠要我解開,卻被我一手推翻摔得滿地破碎。我排練、排練、排練推翻的手勢,反覆反覆排練,卻不曾正式上場演出。因為男主角總是缺席。
於是排練取代了演出,成為目的。像一顆自戀的星球,以其對自身的嘲弄不斷內旋、內旋,自轉於抑鬱的仇緒當中──除非,除非女主角提出邀請,請男主角入戲;除非我走上前去介紹自己:哈囉,你好,我是受過你父親羞辱的那個、泊車員的女兒。
(假如妳不敢表明身分,不敢揭露自己,又要如何以復仇者的氣勢,強取對方的注意力?噢噢但是妳說:我不想再重述那件事了,我只想把它藏起來,藏起它所有的聲音、顏色、光線與氣味──再高級的餐館都免不了的,漂白水腐敗的消毒味──把它藏入記憶的底層,埋進墳場或垃圾堆。把它藏進羞辱中,藏進一個不再對自己開啟也不會對別人開啟的空間,就像一隻老鼠躲在餿水裡面。)然而挫敗的仇恨不會潰散,只會轉向。轉向另一些可供報復的對象。
模仿並報復他們班上來了一個奇怪的女生,而且她很不幸地,長得並不漂亮。那張並不漂亮的怪臉上,抽搐著一種我們看不懂的表情,像在生氣、發問,又像在抵抗什麼。嘴巴毫無意外地總在意外的時刻,掉出幾個重重的大字,彷彿罵人,卻不知罵的是誰。像是智能障礙,又像是精神異常。她為大家提供的最新娛樂,就是嘲笑與模仿。
我從不幫她解圍,見到有人受欺負,我感到一點安慰。奇的是她特別喜歡接近我,羞怯的手拉著我的衣袖,彷彿在說:請妳保護我就像我願意保護妳一樣。我不讓她跟,跑得老遠讓她追不上,見她跑丟了鞋子,就幸災樂禍地停下來觀賞,觀賞人的尊嚴像破鞋被踢打的景象,在這對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的災難中,尋找樂趣。模仿他們,模仿我的同學,玩他們的遊戲,說他們說的話,把自己變成他們一樣,讓他們將我銷毀,我就能得到安全。
有時候,數學老師會選定一個乖巧的女生,代他執行懲罰。「這次月考,有十七個同學比上次退步五分,罰跑操場五圈,請許清芬同學帶隊監察。」正午的陽光鞭打著受刑人的自尊,我站在樹蔭底下,面無表情,數著圈圈,控制速度,禁止抄取捷徑,禁止縮減半徑,禁止懶散的步行。「還有三圈,跑快一點」,享受恨的樂趣。
孩童提起刀刃或者無端端嫉妒一個女生,覺得她象徵了一切我所沒有的東西。在幫導師登錄考試成績的時候,揉揉辛苦的眼睛,把她獲得的九十八分,改成六十八分,再暗暗對自己感到羞恥。
然而她是這樣一個,溫室裡養出的一朵純潔小花,輕易對我付出信任,開開心心地問我:「王子說他寧願喜歡我,也不喜歡尹筱容──這是什麼意思?是喜歡我的意思嗎?」我回答:「寧願是什麼意思?寧願是很勉強的意思。與其喜歡尹筱容、不如喜歡妳,那應該就是兩個都不喜歡的意思。」我當然不會說,寧願這個詞,很有可能,是一個驕傲的男孩,經過某種害羞的扭轉而發出的,攻擊性的告白。
我恨我的同學。我恨他們。我恨她。
這仇恨又豢養出比仇恨更低俗的情感,嫉妒,進而構成對自己的羞辱。我帶著這份醜陋的恐懼,為自己的人格尋找庇護,發現嫉妒最好的庇護所就是喜歡、喜歡、喜歡自己嫉妒的那個女孩,把她當做最好的朋友,一起做功課,一起吃便當,為她整理辮子,寫很多信給她。
以誇張的愛與崇拜,化解誇張的仇恨,在虛情假意的友誼當中,安置我不安的羞恥心,以及,怎麼也打發不掉的施虐衝動。
體育課,測百米。我邁開小鹿般輕盈的腿,全速奔跑,愈跑愈靠近,愈跑愈靠近她的右後方,像個忠誠的影子,拚命追上身體,為她加油打氣,崇拜她,激勵她,然後移出左腳,絆倒她。兩個人都受了傷,我比她傷得更重一點。為了彌補自己所受的傷害,不得不去傷害我家對面的鄰家女孩,林麗鶯,那個總是騎著三輪車,幫媽媽送水果的女孩。
我把男孩們給的情書與卡片攤開──那一個個漂亮而無用的東西、進口的文具、捨不得離開紙盒的禮物……攤開,攤開,像展示會一樣全部攤開,告訴她我擁有什麼,好讓她記起自己被剝奪的一切。我把最好的東西收起來,留下幾樣便宜的小玩意,大方宣告,「這些我不想要了,喜歡的話可以送妳。」炫耀著不屬於我的財富,侮辱著並不專屬於她的匱乏。
──請妳羨慕,請妳嫉妒,請妳記住,記住妳被剝奪的一切。記住:妳被剝奪到甚至不認為自己遭到剝奪,因為妳已經習慣於一無所有。記住:妳再怎麼自命為「森林中最美麗的一隻黃鶯」,再怎麼聰明可愛,都只能得到一點點(也就是,少失去一點點)。妳的生命仰賴妳這個族群與階級的安分守己。就像我爸我媽,他們人生至今的最大成就,不過是,把女兒送進私立小學,讓她跨過他們跨不過的那條界線,進入世界另一邊,給小費的那邊,背向自己的身世,離開收小費這邊。
妳媽賺的錢不夠給小費,也捨不得進餐廳。妳媽連衛生棉的花費都苛扣下來,要妳拿衛生紙替代。妳趴在我腿上哭泣起來,要我把上次用剩的衛生棉送給妳。我給了妳一片、兩片、三片,為了表現優越感。然後不再理會妳的索求,為了彰顯我的權力。
鶯鶯妳覺得我很惡毒吧。妳若報復不了我,就去欺負比妳更弱的人吧。等到下一個可憐鬼哭喪著臉說林麗鶯妳好毒的時候,妳也許就能懂得這個、我比妳更早懂得的道理──不正義的遭遇,在孩童身上展現的最大不義,就是使她失去正義感。
凍傷的葡萄葡萄被回憶的溫度軟化了,滲出水來。
故事從破了皮的紫色傷口瀰漫出來……確實是爛了,那葡萄。頭幾顆吃起來還算鮮美,經過回憶的加溫,一顆一顆趨向疲爛,化做出水的膿包,再不久就要脫皮了。彷彿靈魂卸下肉身,皮膚上冒出痛苦的汗。
然而紫色的傷口拒絕停止吵鬧,拒絕被拋入遺忘。在被重新記憶之前,遺忘是對創傷的不敬。只不過,那些事真的很小。太小、太小、太小了。以致其中的仇隙,也小到滑稽的程度。只突顯了記仇者的卑微與小氣。
小鼻小眼的。不合這時代的口味。
「可以了吧,」不耐煩的聽眾舉起酒杯,「故事說完了吧?說完我敬妳一杯,慶祝這故事終於結束了。」他絲毫沒有興趣追問,追問後來呢,後來妳找到機會報仇了嗎?他乾掉一杯稠體般冰凍的伏特加,繼續追酒,無意追加故事的細節。
「太舊了,這種故事太舊了,」他說。所謂「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故事,已經已經過時了。
昨天才發生的事,明日就乏善可陳,何況十幾二十年前的事?──除非,他說,除非妳口中的這個部長真有其人、而且他至今依然非常有名、非常有權力。
他要我指出部長的真實身分,供他進行一篇獨家報導。「否則,」他以資深記者的世故告訴我:「這故事是沒人要聽的。」看看那串葡萄,爛得不成樣子,只有拾荒人堅持它還沒有壞,不計較它退冰後脫皮的醜態,還有那,果肉中揮發不去的、魚血與生肉的腐敗感。
時代已經變了。過去的已經退了流行。
只有我無法忘記,除非讓我像出水痘一樣大肆發燒胡言亂語到喉嚨壞損,無力再說一次為止──我要將這個故事獻給你,英俊的王子,年少的權勢者,我誠摯以對的仇敵。我之所以要把這十二歲的私仇舊恨說出來,是為了清算並且杜絕它,杜絕它對我的影響力。我要把這個故事獻給你,我的摯敵,這是復仇的唯一方法。復仇,為了不再以你為敵。
這也許就是我跟這個時代、最大的疏離。在一個推翻父親、否決家庭的年代,不斷追念父親。
褪色的白會像什麼?我想念上一次,與父親的身體接觸。
那是多久以前?我彷彿不記得了。是他打我的那一次?還是我打他的那一次?只記得在那次的碰撞中,驚訝於父親掌心的觸感,粗硬得傷人,烈火燎過的樹皮一般。我驚訝因為我感到陌生──自從我長大、長自卑、長出心事、開始說謊以來,就不曾再碰過父親了。
倒是有一張相片,我穿著布袋戲風格的俠客披風,頂著史豔文的高辮子,抱住他修長的大腿,我們兩個都笑得很大,很開心。那是父女情同父女、父女還沒被離間的日子。小學之前的日子。沒有誰以誰為傲,沒有誰以誰為恥。
那時候,我心底還沒長出第三隻眼睛,以之瞪視我的父親母親、他們指甲裡的污垢。那時候,我的背上也還沒長出眼睛,以之監視那些跟蹤我回家的男孩們。我在到家的前一站跳下公車,在凌亂的巷弄裡東轉西轉,彎進公寓的樓梯間,竊賊般躲在暗處,好不容易甩脫了,仍不敢直接回家,鑽進租書店蜂巢般的書架間,繼續避風頭。等我確定他們真的真的錯過了我,才怯生生回到街上,重組我錯亂的方向感。
我穿過臭烘烘漲滿動物屍臭的菜場,把男孩送給我的玫瑰花丟進水溝,再跨過水溝,像跨過一道畫開兩個世界的界線,回家。玫瑰不該越界來到我家,我們家這裡的男人是不送花的。在這不斷滴落汗水、專注於生存的小街小巷當中,花朵是一種騷擾、一種充滿侵略性的象徵,尤其玫瑰,那軟弱而無用的美麗,最能刺痛人心。
我的父親,在我日復一日的沉默疏離當中,一天失去一點溫柔,離開自己的本性,離開我,離開那曾經在鏡頭前大笑的神情,離開那親暱抱著他大腿的女兒。那是一張黑白照片,但我記得自己身穿的那件披風是大紅色的,單純以致傻氣,不懂得隱瞞,不計較美醜。我五歲,我爸三十歲,比現在的我還要年輕。
我不記得上一次,與父親的身體接觸,是多久以前?是他打我的那一次?還是我打他的那一次?我只記得後來,我緊緊抱住他,無法出聲說我愛你。我閉著眼睛看他,將視神經移到指尖,感覺他僵硬的背脊瘦薄如紙、起伏不定。
那是一個無手無臂的擁抱,無實無體,沒有溫度。只是意象,只是夢境。
夢裡只有一種顏色,一種彷彿不斷褪去的白色。
白色褪了色,可以褪成什麼顏色?那或許不是顏色的刪除,而是某種汙垢的添加、雜質的增生──白玫瑰花瓣上生出的第一個斑點。牙齒上殘留的、語言的穢物。老牆上發腫的一塊皮屑。
發酸的乳汁。被汙染的夢。仇視的眼神中、慌張自責而飄移不定的眼白,像一株送葬的百合,蕊心的花粉隨風飛散,弄髒自己,也弄髒了別人。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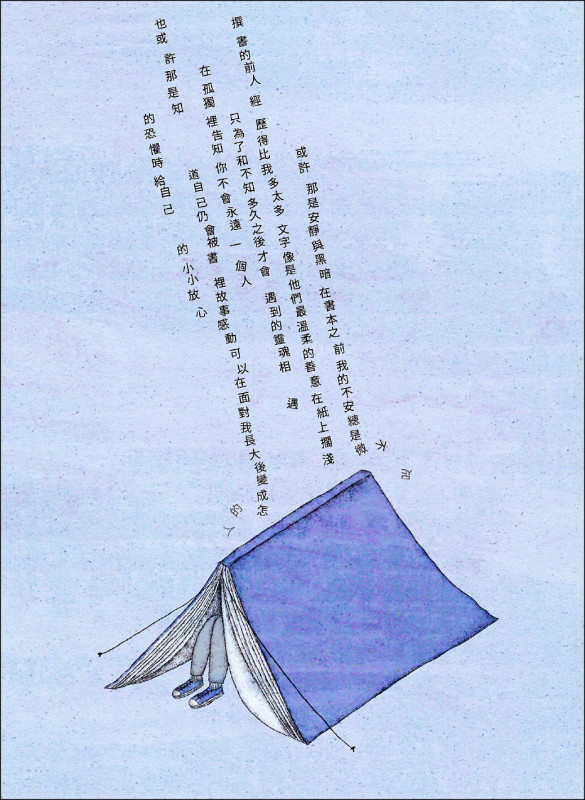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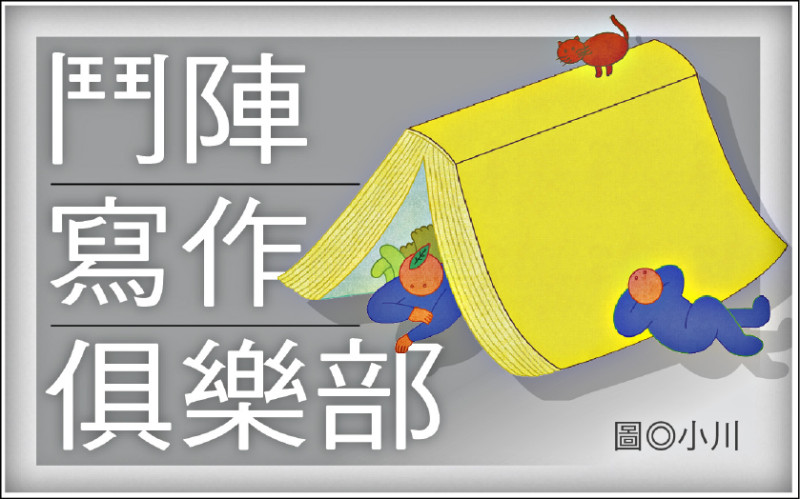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