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羅浥薇薇/【閱讀小說】3之3 - 龐城之春
 圖◎阿尼默
圖◎阿尼默
◎羅浥薇薇 圖◎阿尼默
鄰居的小船順著河水上下搖晃,一年當中近半的時間它被孤單繫綁,落葉在裡頭腐爛成毯。我清楚知道只要適當的節氣一到,有人會細細整理它,再解開它的繩順流而下,但長長的整個冬天有好幾次我都想偷偷把它放走。鄰居有兩個小男孩,年齡差距很小,時常與我的狗玩在一塊,有時我會想像擁有兄弟的感覺,只是有時。我是家裡唯一的兒子,並不覺得自己失去過什麼。
我們沒來得及去散步天便完全暗了。她起身說想去加件衣,我從屋子裡拿出幾盞燭和更多酒,等了半小時,她卻再也沒回來。我把餐桌收拾好,倚著鐵欄杆看向河對岸,龐城在十一點過後會完全熄燈,事實上住家在更早之前便幾乎全黑了。我想著玫瑰說:「孩子的誕生使我曾感覺人生又變得好長,當他死去時我乍然醒覺自己從未擁有過此生。」彷彿曾在鏡前不輟演練,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表情沒有一絲動搖。我喝完杯裡剩下的酒,熄掉燭火,輕輕走下樓開車回家。
身體漸漸好起來的時候,玫瑰開始會騎著腳踏車到鄰近的城鎮探險,這表示她不再需要我的茶葉與日用採買服務。我們白日循著各自軌道運轉,但下午六點咖啡館關門之後,她會翩然下樓,等我整理完畢,一起去散步。
我們的路線很固定,沿著龐城唯一的主要道路,過城中心,再繞到公所後面的小徑,大片的麥田看不到盡頭,放養的牛隻剛開始見到我們防衛心很強,好幾次作勢要成群衝來。她可以看牛看很久,我即興一隻一隻編造牛的名字與個性,和牠們的家族情仇,玫瑰總是很有耐心地聽;或者我們自反方向過橋,左轉進大片養木場,間隔齊整的樹拔地而起,固定命運的人生使它們顯得蒼白而挺秀。向前走二十分鐘左右會面臨野生無章法的森林,她說森林使她害怕又著迷,好像站在高樓往下看那樣,恐懼高度又被墜落所吸引,我陪她坐在樹下聽樹葉窸窸窣窣的聲音,我們重想所有在森林裡迷路與逃脫的故事。這條迂迴之路最後會回到河右岸,我領她穿越枝椏錯綜的樹叢,抵達我最喜歡的河灣,夏天極盛的時候我習慣獨自到這裡游泳,在水中會錯覺自己不在這世界上面,而在世界裡面。有時候走得太遠,回途視線已經相當黯淡,從我們身處的泥土小徑往來時路看,光線漸層遮滅,遠處深成一團漆黑,她就停止說話,顯得有些緊張。等到我們並肩,真正走進去了,再鑽出來,她才說方才心臟鼓般跳動,好像就要走進幽冥交界。
我們一起走路的時候總是相隔了一個人的距離,她再也沒有多說關於自己的事,但這並不造成我們談話的阻礙,事實上我很驚訝她依舊是個好奇心很強的人,對未知仍充滿想像力,像是沒有經歷過什麼令她傷心欲絕的事。
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她最靠近的時刻,並不依恃日暮天黑。那是可頌餐車會繞來龐城廣場為住民補貨的星期一,我們走岔了路,一口氣到了兩小時外的諾讓。雖然想著還得走兩個小時回去令人有些疲憊,但暫時離開麥田、油菜花與森林,漫步在一座新的市鎮,她看起來似乎很高興。所有店家都已關門,我們在石板路上逛著櫥窗,陽光仍在,雨忽然便下了起來。起初只是細如羽的雨絲,漸漸地雨滴愈打愈疼,我們不自覺加快腳步,她縮著肩膀皺著眉頭走,我把外套脫下來讓她披著擋雨,眼看著實在不行了,拉著她彎進路邊一間叫做喬治的酒吧。
我們狼狽地抖落身上的雨水,吧台裡的年輕女孩親切地遞來一疊紙巾。可能是雨天的緣故,酒吧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們點了熱茶與咖啡,最後在一個有著壁爐和深色地毯的房間落腳。她坐在這平空而來的我們的客廳中間的沙發角落,把手裡的糖包撕開,整個加進杯中,攪拌了好久,端起來喝一口,然後放下馬克杯,看著我:「你知道嗎?白玫瑰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花。」
這座由老舞廳改建的酒吧我曾經過無數次,但從未走進。她的真心流露使我感覺安全,也或許百年前摟抱旋轉間親密的耳畔細語分別對我們誠心開導了一次,我倒下身躺在她的腿上,她順順我被雨水打得半濕的鬈髮,手指伸進記憶縫隙撫摸如浪縐褶,我闔上眼。
玫瑰是在幾天後的一個清晨離去的。她請管家替她叫了計程車,沒有讓我知道,自己悄悄收拾所有行李,去了車站。
我上樓打開房間,她把床鋪得整整的,微濕的踏墊與手巾集中在門前的木簍,鎖匙單薄地擱在桌上,沒有留下一張字條。那支白玫瑰還插在玻璃瓶裡,浴室的窗邊,原本盛放的早已凋落,含苞的只象徵性地噘開,水還很澄清。我想像她每日不輟換水,眼神不忍將熄,空曠的房間迴盪著從未擁有機會落實的話語,它們在我胸口抓,好難受。
從那天起尚也消失了,尚與玫瑰一起消失了。我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在河邊忘我遛狗,眼前的風景都使我感覺無比悲哀,我望向窗外,確信塞納河的神已遠走,萬物殘酷。
在教堂開始整修,暫時聽不到報時鐘聲的秋天盡頭,像嘲弄著我的人生一般,女人提議我們應該同居。「我已經受夠了這種週末兩地約會的日子。巴黎和特魯瓦到龐城的距離相去無幾,你還是可以通車去咖啡館。或者你想離開龐城了,我也不介意搬離巴黎。」她不理會我試圖解釋各自保有自己的空間是多麼美妙的事,也不願思索任何折衷的選項,「我希望可以一直見到你。」她最後這樣宣示。
我提早在十月把咖啡館收起來,本來該是十一月。這是固定程序,每年冬天我們封存這棟屋子,留待來年春天把昨年的祕密融化。從前合作過的製片打電話來,說想和我談談手上的劇本,我不確定自己已準備好把故事當真,但我需要完全離開龐城、特魯瓦、巴黎,和一切優雅埋葬我的地方。而紐約並不優雅,它既瘋狂又布滿殘妝。
我沒有考慮太久地租下一間布魯克林的老公寓,距離地鐵站大約十分鐘的路程,搬著行李走上脫漆的木頭窄梯到五樓,我一直覺得整間公寓的地板是歪斜的,大概到了第二週,我才逐漸能夠適應。公寓原本的主人是個藝術家,客廳地板堆滿古怪的藏品、畫冊與攝影集,衣服凌亂地披掛在架上,我特別喜歡其中一件西裝版型的皮夾克,合身又粗獷,就像是依我的尺寸下去訂做的那樣。雖然屋子略顯灰暗潮濕,但由於位處頂樓,房子的工作桌上頭便是一面奢侈的天窗,不大不小,正好籠罩三分之二張桌子。我在這張工作桌上開始緩慢進行籌備新片的熱身作業,與一些舊識恢復聯絡,見一些新的人。有時候我也寫信,手寫的那種,給巴黎的女人,沒有收到任何回信。
十月的最後一天我和製片正式碰面,我們相談甚歡,還煞有其事地列了接下來的時程表,離開製片公司的時候,一名助理開口問我,想不想去威廉斯堡參加萬聖夜的地下倉庫舞會。「你該來的,」他以一種對我擁有極深了解的口氣接下去說:「這是一個完全美國式的節日,但你不必勉強扮裝,那裡很黑,而且音樂很吵。」
我應約隨著歡樂成鬼的人群抵達門口,接到他的來電,說舞會人太多,被警察取締斷電,叫我不必過去了,話才說到一半,沒來得及另約地點,便斷了線。我試著向裡頭張望,被驅趕的群魔漲潮那樣湧上來淹沒我。
我隨著人盲目地流,因為未經打造如此平凡,沒有人和我說話。我走進一間打著清醒日光燈的披薩店,精神奕奕的南美裔店員遞給我一張剛出爐的披薩,我坐在電鋸殺人狂與武打女明星中間迅速完食。走出開始大排長龍的店門,一名矮小的老女人上前問我是否有菸,我把口袋裡的菸草與紙掏給她,她用鼻子哼了一聲轉頭就走,周圍幾個年輕人目睹這一幕,親暱地與我招呼幾句,我索性把菸草全給了他們,其中一個男孩從懷裡拿出一瓶啤酒塞給我。
我握著已溫熱的啤酒站在傳單飛舞的人行道上,無神四顧。對街那面牆有個比人還高大的野兔塗鴉,一群高中生模樣的女孩嬉笑著拿出手機要拍照,原本靠牆站在塗鴉前的一名女子便默默走開。我看著戴上橘色長假髮與雷朋墨鏡的女子站到觀景窗之外,把背包打開來翻找,然後拿出一盒火柴。她試著點燃,卻幾次失敗,每逢失敗,她便把火柴扔開,不知是否受潮的緣故,連續扔了好幾支。我看著她俐落卻溫柔的動作,覺得真像首歌,這麼想的時候我的腦子像被閃電擊中那樣,眼前一片亮白。
那是玫瑰。
她就站在對街餐館和二手衣店舖外,終於把火柴擦亮,雙手捧護著火苗歪頭把菸點燃,抬眼把視線放遠,由右至左,沒有什麼焦點那樣,然後看見了我。
我胸口的獸凶猛衝上喉,想喊她,但人群喧囂吞沒我的聲音。我踏出步伐要往她的方向走去,像第一次見面時那樣,她淡然做了一個阻擋的手勢。我不知所措,收回腳步留在此岸,盯著她,眼睛一下也不敢眨。
她別過臉把手上的菸抽盡,蹲在地上重重捻熄,沒有看我一眼,然後像下定什麼決心那樣,低著頭穿過柏油路上三兩成群的人,走向我,到我面前,雙手輕輕扶在我胸口,用鼻頭蹭過我的臉頰而後貼著它一秒鐘,像在諦聽又像是在訴衷。那一秒之間我餘光瞥見尚從街角探頭,表情像是不意冒犯了什麼,他迅速退了回去。
玫瑰的臉正如我所想像那樣冰冷,她穿越那片微不足道的空白時光而來,在我還來不及反應時,又頭也不回地快步走回對岸。從城市角落相約掠食的千萬鬼魂飢餓地吞噬她,我目光跟不及,她便被捲入無底的黑裡。我扶著路燈,感覺身處的街道急速後退,而我穿過所有破敗的磚造建築撞上鐵網,我的身體好疼。我又失去他們一次了,我的女男主角,就復生在冷酷世界的對街,我卻怎麼也走不到。我沿著滿地的垃圾走下地鐵站,坐在月台中間的座椅上,用只有自己聽得到的聲音對著飛馳過站的列車喊玫瑰:「玫瑰玫瑰。」然而她的名字像一個失效的咒語,並未帶回死者亦無能使生者真正重聚。
我搖搖晃晃回到傾斜的公寓,攀著生鏽的鐵梯走上樓頂,整座紐約城是霧紅色的地獄,枯萎的盆栽被依舊喧鬧的漫長的夜丟棄在腳邊,我跌坐在它們中間,拿出手機,撥電話回巴黎。
電話只響了一聲,便被接了起來。我沒有說話,女人也不說話,我們的沉默占據六個小時的海洋。幾次張口徒勞,我聽著如鯨低鳴的電流,最後低低地,一個字、一個字對著話筒說:「搬來和我一起住吧,我已無法忍受知悉渴求過後的空虛。」
她沒有回應,我聽見她的呼吸在海洋上浮浮沉沉,想像她起伏猶豫的胸口。
「妳在想什麼?」我試著抓住她漂遠的軀殼。
看不見星星的夜裡飛機破空而過,一架、兩架,我躺下來數著它們閃爍的規律。不知道過了多久,從我所渴望與背離的美麗廢墟底下,傳來她被願望磨損已久、奇情沙啞的聲音:「在我眼前,你遠眺過的河道已醒,一隻天鵝正畫傷它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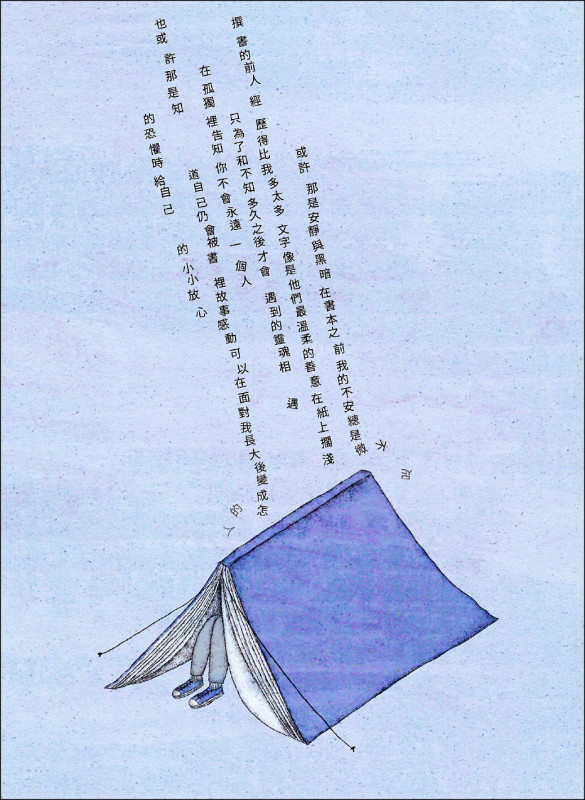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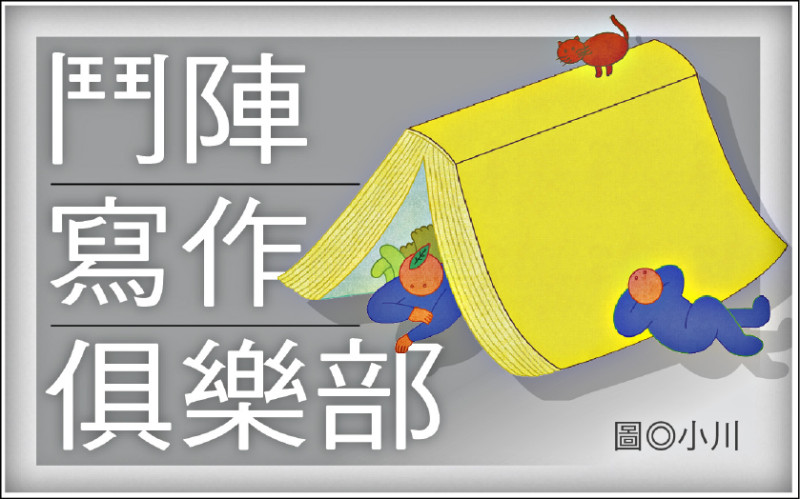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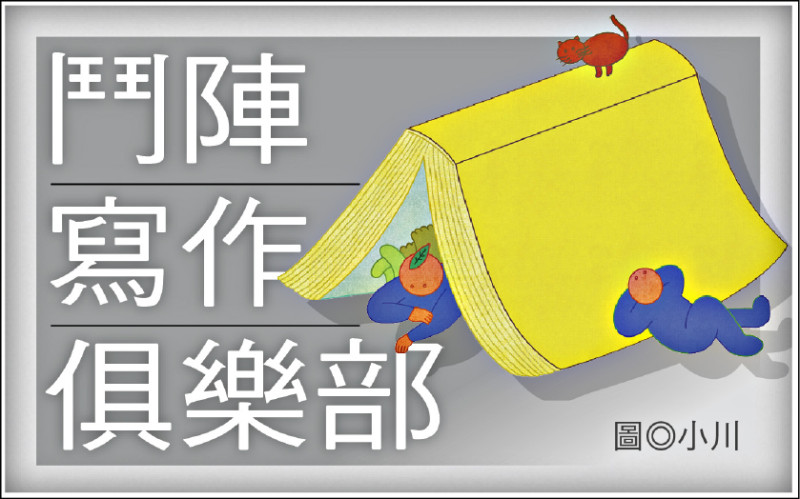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