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郭玉雯/女女相依 - 上
 圖◎王孟婷
圖◎王孟婷
◎郭玉雯 圖◎王孟婷
一些學校同事與朋友大概因為我的臉相端正富泰,個頭在女生中算高,遂認定我從小家庭環境優渥,應該是個嬌嬌女。其實,我父親(原來在中國福建保安部隊裡管財務)1948年(有可能更早在1947年年底)與母親因為逃難,由大陸來台灣,轉進桃園鄉下(怕老共轟炸台北),受訓後充當一名地方派出所的警員(好像是管出入復興鄉的許可證)。
重男輕女的年代
與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人一樣,父親抱持著重男輕女的觀念,我是家中第五個女孩,前面有四個姊姊(分別比我年長十、九、四、二歲;以出生地為準,稱為大陸大姊、二姊,台灣大姊、二姊)、一位哥哥(大我六歲,台灣出生),當時一般家庭裡這種差個一、兩歲等階式的生育排序非常普遍,孩子數目大都是六到八個。據母親說父親一定要她生兩個男孩(怕其中之一有什麼閃失,需要備胎),直到弟弟出生(小我兩歲),她才免除了生育餵哺的勞責。母親生我時,她自己恐怕也覺得滿沉重的,等於債款尚未還清;在溽暑的天候裡坐月子,母親長了一身痱子。當時經濟條件不夠,不是現在所能想像的,何況又是一個女孩?母親後來曾經委婉地透露過,只有生男孩時,父親才會準備「雞酒」給她食用,使奶水充足。
沒多少母奶吸吮的我(彼時牛奶是奢侈品),從小牙齒就不好,成年後幾乎每顆都需要修補,或者就是搖晃的;雖然經常上牙醫診所,至今仍視診療椅為畏途,不肯輕易去。舊照片看起來(從小每年照一張全家福,經由香港或新加坡的旅外親友寄回去給留在福州、來不及坐船到台灣的外婆),我小時還算壯,胖皮胖皮,可能是因為母親信了「麵粉教」――桃園鄉下的天主教堂,為了招徠信徒而定期發放麵粉,所以家中常做饅頭、麵條、窩窩頭等食物;教堂偶爾也發放一種白豆,煮熟後粉粉的,味道非常別致。
父親在派出所的同事婚後多年膝下猶虛,夫妻倆常到我們家轉悠(會不會從父親口中得到某種暗示?),據說極喜歡我,意欲領養;父親願意但母親終究捨不得,理由之一是我的大陸大姊(1946年生)與外婆一起留在福州,據父親說是趕不及搭船(我懷疑是父親來台,一切未定,一方面想著馬上可以反攻大陸?另一方面暫時無法或不願負擔大女兒與岳母的生活?),二是母親從小與外婆兩人相依為命,唯一的弟弟(我的舅舅)出生後患病一年,用掉家裡最後一角錢才離世;母親的家人不多,自然不捨將自己的骨肉送給別人。最大的理由應該是母親懷抱出生不久的大陸二姊(1947年11月生)搭機來台(母親會暈船),結果這位來不及成長的姊姊在四歲時於桃園家門口玩耍,絆到門檻跌跤,因無錢診治而夭折(父親由福州帶來的一些金條遭親戚欺騙投資煤礦,血本無歸)。
我的哥哥從小有氣喘症,每一生病,父親總是斥責母親;罵聲、喘息聲,淚雨齊飛共揚,我們其他幾個小孩總瑟縮在牆角裡。記得我四、五歲時,父親買了一隻母羊,養在大溪派出所警眷宿舍狹窄的後庭裡,因為聽說羊奶補氣潤肺,可以每天擠新鮮的給哥哥補身體。我常常看到父親下班後或週末牽著羊落到大漢溪崁底去放牧;為了羊奶能夠源源不絕,父親還牽著這頭母羊去交配受孕(如此方能奶水充足),並親自接生了兩隻小羊,但隨即賣掉;然而記憶中,哥哥的身體始終瘦弱。家裡有什麼當令或美味的東西一定是他優先;大概是胃口差或者個性細秀,哥哥常常將珍品存放在抽屜裡(他自己擁有一張書桌,其餘姊妹不是在飯桌,就是在木椅上寫功課),隔一陣子才拿出來吃,爛掉的就丟棄了。
症候其實是一種模仿
到我小學二年級時,父親嫌鄉下只有初中,水準也不夠,怕哥哥無法繼續升高中、上大學,遂自願降級調職到台北「警務處」(現已改為「警政署」)。我們離開河中捉小魚、夜間觀螢火、前庭裡有小小葡萄架、木瓜樹的半田園生活,一家子鄉巴佬到都市分租別人的屋子,擠在一間悶熱湫隘如鴿籠般公寓的後半段(前半是堂舅擔任理事長的司機工會辦公所在),其中還又隔出一間有別人租住。我小六時,父親才配得松山的警務處宿舍;十六坪大小,還包括浴廁廚房、客廳(兼飯廳)、三個房間;哥哥自己一間,弟弟與父親睡,母親則與我們三個女孩擠在一間――裡頭放著一張高大的床,上下有三層,各層可睡兩人(在大溪訂製,可拆卸,再重新組裝;第三層已靠近天花板,只能塞棉被雜物等),幾乎占滿整個房間。
台北的教堂雖不發放救濟品,母親仍繼續前往做禮拜(到她八十多歲,才透露是為了四歲夭折的大陸二姊,心靈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慰藉,但我從未聽過父親提及這個女兒),我與台灣二姊有時跟著去,尤其是耶誕節的子夜彌撒,穿得結實無比,圓團團的,深夜迎著冷冽的風,另有一種新鮮與振奮感;我還領了上主日學並受洗證書,聖名是「馬利亞」。我結婚後常到國外旅遊,進歐洲的天主教堂(譬如法國路德或聖米歇爾),見到聖母像還不自主地掉下眼淚。
小學二年級由大溪國小轉到台北的敦化國小,我老被同學欺負,自習課明明沒講話,硬是在黑板上被記了名字;挨老師打手心也不知反駁。當時功課不行,既害羞又自卑;直到五年級,遇到一位極有耐心的林老師,在他的鼓勵之下,我的成績方才有了起色;不過在同學間始終落落寡合,沒什麼朋友。課餘唯一的樂趣是走二十分鐘的路程陪母親上傳統的菜市場,一面流覽五顏六色的生鮮蔬果,另一方面幫她提菜籃。有幾次印象比較深的是母親買豬肝,我上了高中才知道她有子宮肌瘤,罹患了嚴重的貧血症(母親於1972年夏天在醫院做了全子宮切除的手術)。父親緊盯著哥哥的功課,但他的成績平平,大概身體虛弱,加上全家生活主要以他為中心,想必壓力也很大;父親只要聽見那裡有名醫,再遠都會帶他去看,往返奔波,說不定讓哥哥更加疲累。
說也奇怪,我成績一好,身體就變差,每次感冒必引發支氣管炎,也跟哥哥一樣,像風箱般氣喘著;假使生病包括某種心理因素,如此這般症候其實是一種模仿,目的或許是想引起注意。父親自然不會往這方面去想,帶去警務處醫務室看完病,到了辦公室,眾目睽睽之下即「命令」我吞藥丸,每當此時,我的喉嚨也立即緊縮變小,吞不下去而吐出來的藥也糟蹋掉了;他皺眉瞪眼,嘖有煩言。勉強幾次後,他不願再管,於是母親從原本微薄的菜錢裡勉力省下一點錢,帶我去住家附近看醫生。有一次,遇到一位免收費的中醫老先生,脾氣壞,把完脈後突然大聲訓斥:「你們父母怎麼當的,女孩子生病不好好醫,叫她以後怎麼嫁人?」母親登時滿臉通紅,其實真是冤枉她了;爾後她還發明用稀飯吞送的方式,讓我順利服用藥丸。
迢迢千里,最後告別
小學五年級學期快結束時,已聽到改制的消息――免試升學;一年後,我成為第一屆國中生。小學(六年級上學期由敦化轉永春國小)班上許多本省籍女同學,成績非常優秀,但不是準備嫁人就是到工廠生產線上做工。升國中的暑假,我依照父親的安排也到一個廠家上工,整天像機器一樣不停地將車製好的麵粉袋翻面,兩個月下來,共得一百六十九元的工資,寫在一張小紙條上,被父親領去也不敢有異議。我之所以能夠進入國中就讀,原因之一是父親所服務的公家機關有子女教育補助費。後來聽到有人批評說台灣是軍公教福利國,或者感歎本省籍青年要升學(有時是大學畢業往國外留學),家裡可能得賣掉房子或田產,還真有點心虛與尷尬!
國中期間,既叛逆又倔強,每每覺得父親偏心,對我特別不好;早餐往往沒吃完就奪門而出,一路頻頻拭淚,又怕被同學看見,愈哭愈多。第二堂下課,母親帶著自家製作的饅頭爬到三樓來了,往往什麼話都沒說,四隻淚眼相望哽咽。為了追求自己的存在價值(按現在的話是「刷存在感」),我拚成績、搶分數,結果是身體愈來愈差,氣喘還加上皮膚病,幾次在深夜中,不能平躺,靠在床邊牆上,覺得自己氣若游絲,瀕臨死滅;而「類乾癬」的病一旦發作,又癢又痛(當時不知道病名),真恨不得就此闔眼長眠。母親常在半夜裡搖醒我,餵我吃藥,然後輕輕拍著我的背,或為我抓癢,耐心地等我入眠;就在生命最為低迷之處,我徘徊踟躕,感覺自己不斷地被巨大的離心力甩開,而母親卻如一根極細卻堅韌的線將我繫住。
我考上好高中,表面上父親似無欣慰之情。從國中的寒暑假開始,我與台灣二姊就接一些編織帽子、圍巾,或在毛衣上繡花的家庭代工,賺取零用錢,主要是購買各科參考書籍,那時家庭環境好的同學可以到老師家補習或學古箏。進高中第一年,被選拔為舞蹈團,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比賽,舞鞋需自費,我就是沒有勇氣跟父親開口,一再延遲的結果是體育組長公然念出我的名字,並且大聲說沒有錢就不用繳了,至今那位老師高八度的尖銳嗓門仍令人難以忘懷。
高中離家很遠,必須轉兩趟公車,到台北火車站之後,步行至校,可以省下一段車票錢。有一回,天氣突然變冷兼下雨,我正擔心自己是否又要感冒了,結果聽到廣播說母親在學校門房等著,不知她怎麼七拐八彎地尋來(外祖父早赴南洋不歸,母親自幼即與外婆在福州的火柴盒工廠做女工,沒機會上學,後來自學認字,寫出娟秀端整的字體,更喜歡閱讀琦君的散文集,她也很想看看台北有名女中的模樣吧),手上拿著三把傘(我與二姊同校),袋子裡裝有我們姊妹兩學校的黑外套。
開放探親前的1983年,母親就勇敢地、隻身從香港轉機回福州;大陸大姊那時已結婚,生了兩個男孩(一胎化政策以前);外婆高齡七十九,患有嚴重的胃病(可能是胃癌),本來早該解脫,但為見女兒最後一面,始終硬撐。母親在村頭一下車,隨即聽見外婆叫著她的小名,兩人相擁痛哭。雖然停留的時間不很長,母親與外婆的合照張張笑容可掬、天真燦爛,我從未在她臉上見過類似的欣悅表情。母親返台不久,外婆大約覺得心願已了,撒手辭世。相片寄來,停靈於一間五、六坪的小屋裡,應該是外婆與大姊相依為命的生活所在,門旁掛有一張輓聯,上面寫著:「一生劬勞」。我從未見過外婆,乍見此照,繃不住淚流滿面。過了幾天,某晚半夜時分,我們都聽到母親淒厲地哭喊,說外婆來到夢中相見,她用力往前仆抱卻驚醒過來。母親在小小的客廳裡擺上外婆的遺照遙祭;原本不知外婆是否享用得到祭品,當時小弟已長大,平常在客廳裡睡摺疊床,剛只伴著祭桌,一晚睡夢中,聽到有人在他耳邊說紙錢燒得不夠(意思是由福州到台北的路費不足),方知真有感應。山高路遠,外婆終於從迢迢千里以外飛奔而來,倚靠著唯一的女兒,或做最後的告別?(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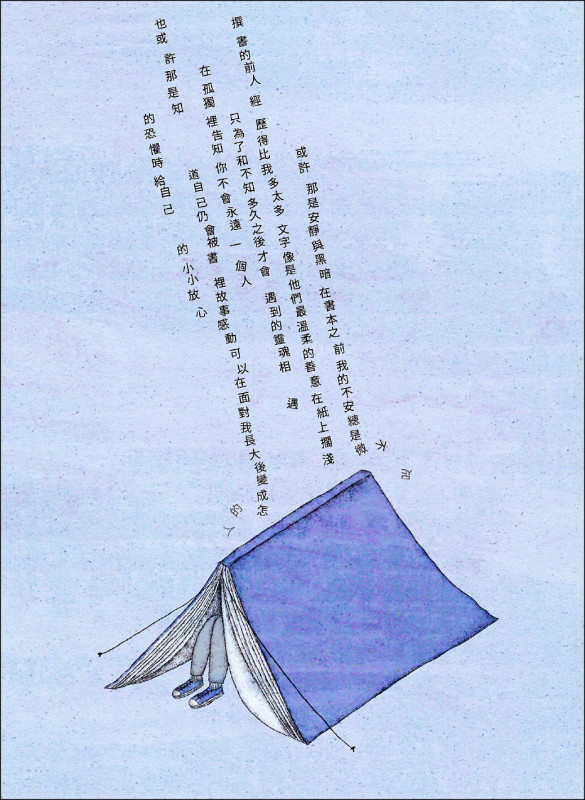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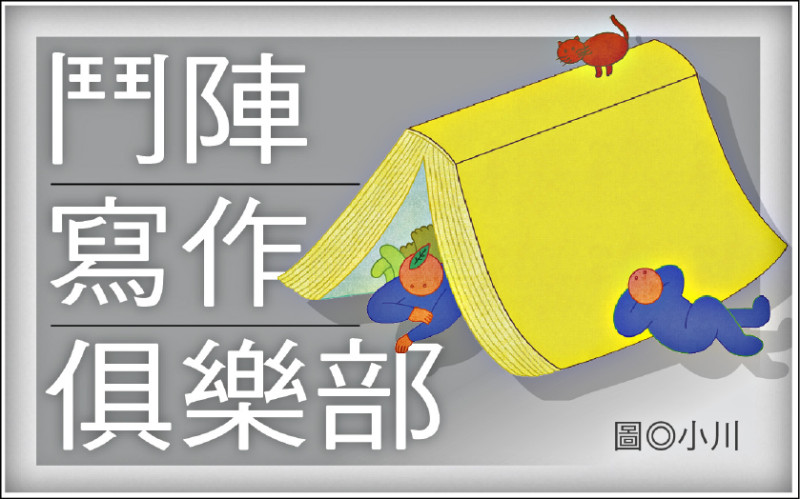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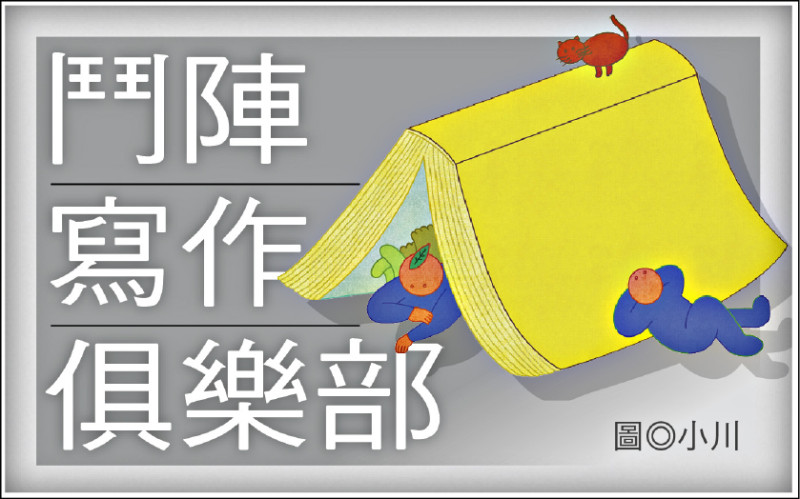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