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書與人】書寫是從棄書始 - 伍軒宏談《撕書人》
專訪◎蕭鈞毅
 新作《撕書人》。
新作《撕書人》。
 作家伍軒宏。 (伍軒宏/提供)
作家伍軒宏。 (伍軒宏/提供)
「事實上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截稿期。有一個截稿期的話,我就會好好把小說完成。」受訪時,伍軒宏(1960-)半開玩笑地這麼說。在2005年,以〈阿貝,我要回去了〉得到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之後,時至2018年的今日,伍軒宏才出版了他第一本長篇小說《撕書人》。
隔了十多年終於交出第一本小說,為何間隔如此漫長?伍軒宏從他書寫的起源開始談起:「高中的時候,被文學吸引,很想寫作,可是一直覺得自己能力不夠,所以大學才讀了文學──」可是一路走來,經歷了外文系的訓練,再到美國攻讀英美文學研究,其後回到台灣任教;伍軒宏當年想寫作的初衷,反而安靜了下來:「一個原因是,我覺得我的文學語言不夠好,還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寫;第二個原因,雖然我對周遭的環境有感覺與想法,但還沒有足夠支撐的『故事』;第三,後來上了大學,被學術研究吸引,學術與理論訓練當時非常熱鬧,所以就一路往學術方向走去。」
「但原初想要創作的想法,還是慢慢地出現了。」如同求學生涯時被學術吸引的轉向,伍軒宏的「創作生涯」從〈阿貝,我要回去了〉浮出文學創作的水面,一方面本業又在學術與教學,蠟燭兩頭,也說不清楚到底哪個才能算是「分心」了──直到退休之後,伍軒宏才明明白白地放下了大半生的本業,回過頭來處理那一個始終在精神層面不停誘惑自己的,文學書寫。
於是,恰似遠離學術等知識工作一般的隱喻,《撕書人》從書名就讓人好奇,內容更是關於「書」與「知識」之棄絕:「其實我手邊有不少長篇小說的計畫,但會選擇《撕書人》,一方面是我喜歡這個鮮明的想法,另一方面,對於『書』太多的焦慮,也是我現實中的感受。而且,寫長篇小說需要許多具體的細節,既然『棄書』是我每天都在掙扎的事,那我就有了現成可改寫的心情、細節與厚度。我想要早點發揮這個題材。」
第一本長篇小說,既是創作生涯的再開始,亦是一種書寫練習。
「書」及其象徵:人文
《撕書人》以兩條明確的故事線構成:第一條線,是再也受不了父母囤積的大量藏書的德彥,他活在一個紙本書幾已消失的近未來;德彥一面感受到書以物質層面的發霉敗壞侵占生活空間,另一面則感受到書代表的知識過於厚重累贅,於是開始規畫「棄書」的逃逸路線。
第二條線,則以20世紀90年代的台灣留美學生佐夏為主角,旅外求學與打工的生涯中發現自己有著超自然能力,碰到書本,手指彷彿有了磁力,會讓書本被吸引翻轉,甚至撕裂在空中盤旋;最後再被帶進已衰老的紐約出版公會和出版商的祕密集會世界。
兩個並不相干的世界,在小說裡藉由對「書」的遺棄與撕毀之經歷交錯。德彥身處的近未來,棄書是廢棄物清理法規中最不受歡迎的一項,是連回收都無人願意的殘餘。除了令人驚奇的霉味之外,書幾乎沒有剩餘價值可言。而佐夏的世界,雖是離我們不算太遠的過去,在《撕書人》裡,卻只是這本小說裡一篇名為「撕書人」的小說。
這樣疊套的小說結構,讓佐夏這名撕書人的故事,成了德彥所身處的書早已滅絕的世界中,一次古怪的體驗──在閱讀早已無須紙本的近未來,居然要和讀者說上一則由大量紙本、縫線、書頁與出版商所構成的故事──對於德彥世界的讀者而言,這興許是不易想像出畫面的故事了;這樣「懷舊」的故事,為何成為了《撕書人》中重要的主線?我以為這和小說家伍軒宏對書的態度有關:「書和知識的承載型態改變了,它代表的思維方式也就慢慢改變了;但像我這種訓練的人,有很多人會對紙本書、知識,和其代表的『人文』正在消失這件事,有些不捨;它也是我的一部分,可是我並不特別留戀,我想如果它留不住了,那就讓它走了吧。」
佐夏的留美經驗,及其代表的學術訓練,恰似伍軒宏知識體系構成的路徑。很難不以此聯想,小說裡的小說之所以讓佐夏成為「撕書人」,頗有在「虛構」的近未來世界中,為過往曾經喧譁熱鬧且以紙本書為知識載體的年代,打造一座讓人文得以善終的故事棺木。
若要撕書,也要讓嗜讀且無書不可的人,來當拆開書頁的那一個人。
於是在小說裡,最盛大的撕書場面竟也有了紙張紛飛,恍若死前狂歡的感覺。
《撕書人》的書及其象徵:名為「人文」的事物,即使撕成碎片、即使成為袋袋垃圾,它依然存在於選擇它的人們內裡,即使是不選擇它的德彥,在遺棄之後,仍會有人循著它丟棄的路線,將之片片拾起。
「廢除文字,當然瘋掉了。」
「寫下去的那個時刻,是瘋狂的時刻。」談到《撕書人》的寫作過程,伍軒宏侃侃而談:「有很多細節與內容,是在寫作的過程中自己冒出來的,這些讓我懷疑起『這真的是我寫的嗎?』的文字,這種意外,是最大的樂趣與驚喜。」
從寫小說的長路中發現樂趣,小說本身卻是寫了一個書不再被需要的年代。角色們討論亞陶(Antonin Artaud)的殘酷劇場時,冒出的一句對亞陶的評價,或可做為理解這本小說對「人文」之態度的線索:「廢除文字,當然瘋掉了。」說的是亞陶,說的也是小說裡,文字以更簡短、更段落式的形式,存在於書消失後的世界中,讓人們不至於「瘋掉」的存續。
就此,伍軒宏提到:「德希達有篇文章,認為亞陶的觀點看來激進,其實連通的卻是古典希臘的形上學;他認為,就算亞陶成功了,總是會有別的文字、別的Text出現。雖然我正在呈現的是這個形式的文字──以一本書為載體單位的形式──正在消解的現狀,但我還是比較Derridean一點的。」比較Derridean一點的,認為總會出現另一種文字形式,乘載著不同的意義與觀念,讓人們藉以溝通、思索、與追問。
也由此,就算小說裡頭走向了棄書與撕書之路,就算「人文」慢慢地式微,它可能也會以另外的方式,重新浮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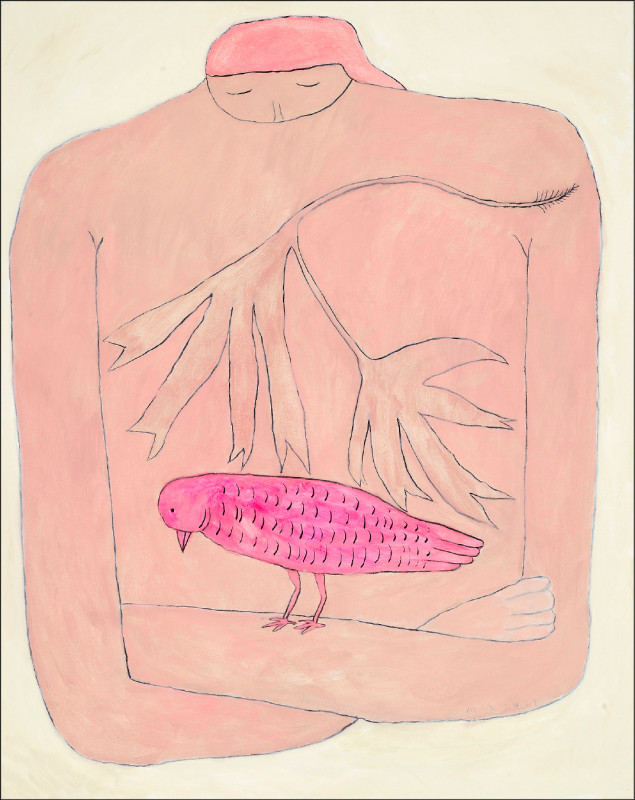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