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劉清華/一碗菜茶的航道
 圖◎吳怡欣
圖◎吳怡欣
◎劉清華 圖◎吳怡欣
搬離家裡快十年了,試過與人同居也有獨居,但還是一直逃避煮吃的事。每次被問何以如此遠庖廚,我都回答:「我媽媽做菜太好吃了。」今年春節難得回港,住在老家兩星期,終於吃到了久違的滋味。除了豐盛的團年飯,馬拉松式的春節聚餐,正月初十那天,我睡到很晚才醒來,走出客廳就被眼前一桌子賞心悅目嚇到,「今日食菜茶。」母親說。這是我們家每年都會出現一次的餐桌風景,也算得上最有特色的一幀。
菜茶是潮汕茶食,又名開燈茶。每逢新年,潮汕人家家戶戶都會炒菜茶,互相串門子,十幾人圍著大圓桌再笑數著對方吃了幾碗。登門的要帶禮,用紅紙包一條長長的白線,寓意幸福長壽。不過這些鄉里習俗,都是後來我從母親口中得知,因為我只吃過她做的菜茶,對我來說,這是屬於我家的滋味,當然也包含著她對原鄉的味覺記憶。
雖說是傳統料理,每家人菜茶的口味都不盡相同,菜肉比例,茶湯調味也是求其所好,正如每個香港家庭都有自己的番茄炒蛋。母親的菜茶用料豐盛,處理食材也是講究,用上的菜品有七種:生菜、椰菜、茼蒿、芹菜、蒜仔、西洋菜、荷蘭豆;炒一盤十多人份的菜茶,廚房瞬間變成菜園,被一籃籃綠色層層包圍,而單是洗菜也得用上半天工夫。每種菜洗淨後分盤待摘,荷蘭豆拔邊去絲、芹菜要用小刀在葉柄根上輕輕一劃,撕走菜梗的粗纖維……再將所有菜去頭去尾,切成易入口的大小。母親說炒菜技巧是這門料理的關鍵,她用的是傳統中華生鐵鑊,強調菜絕不能混炒,翻炒時菜要少,油要足,鑊要熱,而且必須快手快腳,把菜炒到出水變軟就是大忌,菜茶變菜湯。分批炒好的菜散開在大盤之上,加入已經燙過的粉絲拌勻,加速降溫以保持菜料色澤油亮,翠綠。
在鄉下,如此費工夫的料理必然是家裡的婦人合力炮製,但我家廚房裡卻從來只有母親一人。七十年代,父母在內地生活困難,在大饑荒後民生蕭條,經常三餐不繼,幾經波折終於從海豐逃難到港。從此在這邊岸上扎根成家。來港多年只吃過兩次疏堂親戚做的菜茶,是後來我弟都升上小學了,母親三十二歲那年,時間變得寛裕下才生起在港「復刻」菜茶的念頭。不能否認,母親對煮吃相當有天分,童年時只負責洗菜的她,單憑回憶當時大人在廚房裡舉動,加以揣摩就能做出了一桌有板有眼,滋味得可以宴客的家鄉料理。
至於菜茶的配料,母親喜用豬油渣,在市場買三十元肥豬肉,把雪白的大肥肉抹乾切丁,細火慢炸,原先帶有腥氣的肥肉隨著油溫持續升高變得焦香撲鼻,最後才加一撮鹽調味。花菇乾、魷魚脯、蝦米、蝦乾則浸軟後切絲,分別以紗巾包裹擠乾多餘水分,再落鑊以大火炒香,此時隱含於食材裡的鹹香鮮甜都往外噴發,最後才拌勻上盤。桌上還放著幾盤獨立的配菜:煮過的眉豆和麥米,口感香軟綿密;剁碎的香菜清香帶勁;還有負責脆口鹹香的花生,炒米。
所謂的炒米是潮汕特產,也是各式茶食的精粹。做法是先把上好的白米平鋪在竹籠裡蒸熟,再加以風乾日曬,後混入細沙,油和鹽,於大鐵鑊裡炒至米粒膨脹爆開,最後篩出細沙放涼待用。由於工序繁複,難於在家裡製作,母親每次回鄉都會補貨,但每每想到一個婦人手抱著一大袋,近乎她身長一半的炒米,長途跋涉從汕尾坐直通車到深圳,過境後從羅湖關口,慢慢坐火車搖到將軍澳老家,這長達半天的旅程,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後來疫情封關,家中的炒米快用光,母親四處打聽下,發現觀塘瑞和街街市的陳興記有入貨,她的心才安樂起來。
對味道如此堅持的母親,她的拿手小菜多得可以寫滿幾頁白紙:手打馬鮫魚丸、梅子蒸烏頭、薑蔥燜蠔,滷水豬手、生腌蟹、蠔仔海鮮粥……簡單的家常菜如香煎豆腐,豬肉炒菜心,也是外面餐廳難以做到的出色。在我長大以前,曾以為每個母親都會煮菜,愛煮菜,直到小學四年級,隔壁同學問我昨天下午茶吃了什麼,我說碗仔翅(注一)啊!母親做了碗仔翅。然後他就認定我說謊,堅持碗仔翅是買的,沒有人會親手做。我才發現母親是這個年代,這個城市裡罕見的物種,一個會自製碗仔翅,砵仔糕、煎釀三寶……一切街頭美食給家裡吃的母親。
除了味道,母親還堅持孩子要有營養,因此我們家極少外食,三十年來,一家六口的三餐都由她一手包辦。總是待在廚房的母親性格溫柔內斂,不擅辭令,每次吵架都敵不過我父與我,來港幾十年,講廣東話還帶著點潮汕口音,回鄉到市場買菜,用鶴佬話對答又被認做是外省來的,兩邊不是人。或許母親只是把精力都放在廚房裡,發展出一套完整而靈動的技藝就是她獨有語言。後來哥哥們成家立身,我則長年埋頭在工作室裡,面對子女逐個離家,母親也開始受失眠和情緒問題困擾。或許無須再打理子女的起居飲食,對她來說,也意味著失去了一直以來最擅長與我們溝通的方法。
眼前大盤小盤,翠綠的山產伴著赤紅的海幸,還有雪白豐腴的炒米,一桌美麗而富節奏的風景。此時還欠最重要的茶湯,聽說別的人家會用大骨熬湯入茶,母親卻嫌白湯濃濁,堅持只以青茶做湯,貪其幽香和淡雅。一把乾燥的茶葉撒進刻有坑紋的陶缽裡,用木棍研磨成粉,愈細愈美,再倒入熱水泡開成湯。當一切準備就緒,端碗,把菜料撈入,然後是花菇海味,再隨喜加入香菜,眉豆,撒些炒米,最後,一壺熱茶澆下去。一口接一口,食材的自然原味互相交織,油渣的焦香在熱茶的清雅中化開,蔬菜的爽脆清甜配上海幸的鹹香鮮美,那是一碗深刻而飽暖的滋味。
有時吃著母親做的菜,也會生起焦慮,焦慮她哪天離去,這些味道就會永遠消失,於是我問:「你會想我學做菜嗎?」她說不會,因為我沒有毅力,做菜煮飯的毅力。我倒是覺得她知道我志不在此,不必勉強,畢竟自有記憶而來,她都不曾強迫過我,由此至終。而現在,我還是比較熱衷埋頭創作,鮮少開火,但母親的食譜正一頁一頁記下,以防哪天心血來潮。
味道的傳承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眼前這桌料理與其說是外婆的味道,不如說它們是沿著母親生命流動的軌跡一路演變,南來北往。母親成長於物質匱乏的時代,吃過的菜茶都是湯多菜少,沒有蝦乾,零丁的豬油渣更要用搶的才吃到。她復刻的是對原鄉的味覺記憶再加上自己的心思,而那心思與她周遭的現實環環緊扣,像後來家中經濟開始寛裕,菜茶才漸漸變得豐盛,記得某年,她更自創加入鮮活,白灼了西貢買的基圍蝦入菜,滋味無比。其他傳統潮汕菜式如炊粿、菜頭粿、反沙芋都是我家的桌上餐肴,同時,她又會特意到離島,買水上人現磨的大地魚粉熬湯煮麵,仔細回想,母親的料理總是混雜著潮汕與香港的風味,而這也構成了我味覺的原點,並一直提醒著我──我是誰,我們從哪裡而來。
今日打開臉書,看到移居格拉斯哥的友人上傳了幾張照片,她用焗爐烤了一條蜜汁叉燒,白飯旁邊放上兩條菜心和一羹薑茸,說人在異地想念灣仔的再興燒臘,而她那廣東話都快忘記了的兒子也吃得津津有味。滑下去,標題「羅宋湯戰爭」的新聞出現,一個穿上圍裙的婦人指著那寶石紅色的湯水說,那就是她祖家的味道。滑下去,一則Morkovcha(紅蘿蔔泡菜,注二)食譜,那是1937年,十七萬蘇聯高麗人被史達林集體流配到中亞後創造的菜色,因為那裡的土地種不了家鄉的大白菜,只好用紅蘿蔔取替醃漬。或許從我母親的那一代,應該說更早,更早以前,當離流在人類史上展開,隨水漂流的人必然會攜著原鄉的滋味流落各地,不斷復刻,再現,演變,甚至可被視為一種微弱卻實在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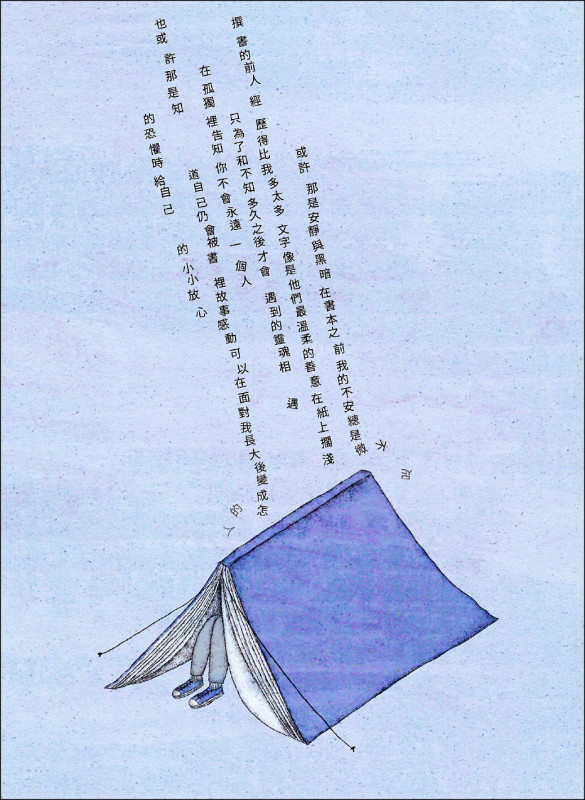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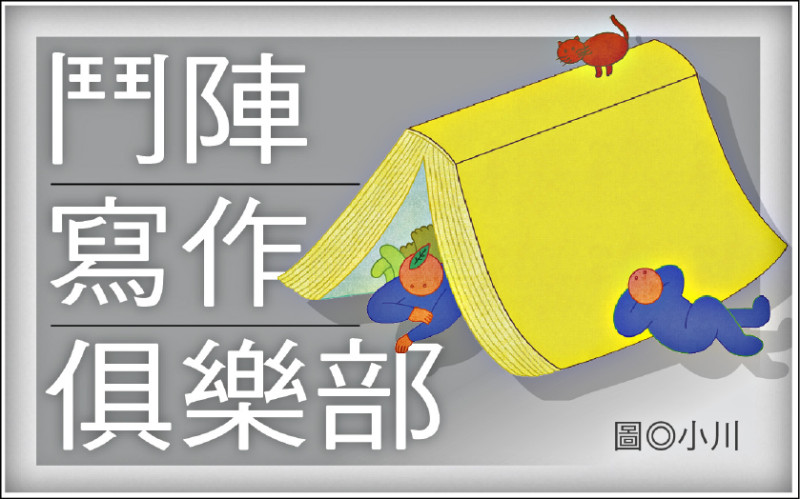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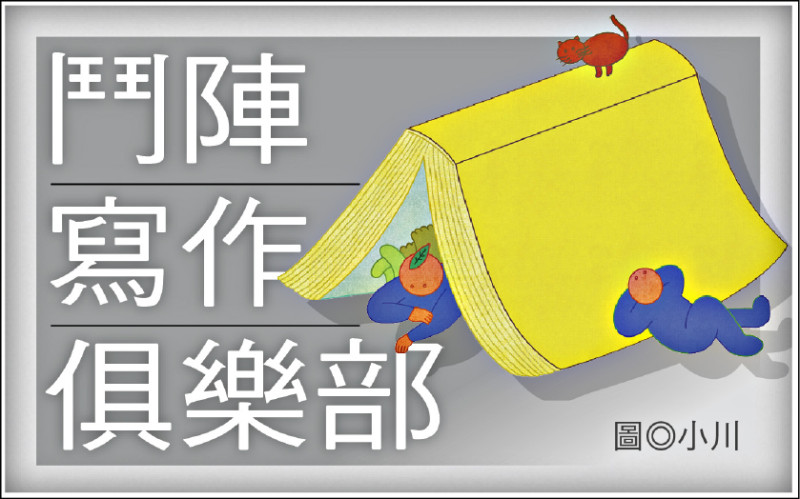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