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美麗世(負片) 〈上〉
 彌陀,1994。
彌陀,1994。
文.攝影◎吳明益
 彌陀,1994。
彌陀,1994。
偶爾會有學生在進我研究室時,問起那張照片的來歷。
我得把時間撥轉到跟他們相同年紀的時光,那時候我是那麼地著迷於偽裝孤獨與自由的漫步旅行,並且著迷於「看見」這件事。我會搭著平快車到遠方就只是坐在月台上數小時,只是看著不同人上下火車;或者從一個小站沿著鐵軌旁的小路走到另一個小站。又或者在城市、小鎮裡,專走迷宮般、不知道通往何處的小徑,試著盡可能完全避開大路,彷彿那裡有老虎。彼時陪伴我的就只是一台相機。
當時我的相簿裡頭有不少照片,裡頭的風景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再去的地方,比方說彌陀。即使台灣這麼小的一座島嶼,也存在著像彌陀這樣一個看起來在情感上渺小的、似乎不會被世界懷念的地方,小鎮的時鐘已經停了,也沒有人替它再上緊發條。
事實上我對彌陀的印象已經幾乎完全消逝了,只剩下那幾張照片。那是個天色明亮的午後,我閒晃走到一間正在搬演布袋戲的小廟前面(是什麼廟也忘了),戲的「外台」實在寒酸,就是一台發財車,側面放了一面布景,演出的師傅只有兩個人,武場則是以放錄音帶代替。布袋戲的布景上頭寫著「陳金龍木偶劇團」,並且有「彌陀」二字,顯示出它的在地身分。小發財車前的觀眾只有三個小學生大小的孩子,兩男一女。小女生跟其中那個胖胖的小男孩完全沒在看布袋戲,他們對我和我手上的相機比較好奇,發現我以後就靠過來跟我說話,不再看戲了。唯一仍面對戲台的小男生則故意忽視我,背著手,站在路邊的花台上。我把相機借給胖男孩跟小女孩,他們把頭湊到觀景窗上,露出驚奇的表情,問我能不能給他們「按一下」。
必然聽到我們對話的小男孩,仍然背著手,偶爾把頭偏過來,用眼角餘光偷看我們。而當我把相機對準他時,他就故意轉過頭去,賭氣似地繼續忽略友伴和我的相機。我拍了小女孩和胖男孩和布袋戲車的照片,也拍了假裝看戲的小男孩的背影,並且給小女孩和胖男孩各按了一次快門:他們都選擇拍別過頭去的同伴。
我並不清楚這幾張照片對我的意義,也不曉得對它們的情感標識從何而來,直到有一次,幾位來我研究室談話的學生,看到那張照片,聊起她們是多麼喜歡布袋戲。只是此時電視上流行的,已是被稱為「霹靂布袋戲」的「大仙尪仔」,聲光效果遠超過「金光戲」時代了,而布袋戲的表演也多半脫離了野台,或許可以稱為電影化的布袋戲時代吧。我曾勉強看了幾集,始終沒有辦法進入那樣的世界裡。曾經是布袋戲迷的我,被「新的布袋戲」拒絕了。
也許拒絕進入的是我。我偶爾會試著回想,那天「陳金龍木偶劇團」,演的是什麼戲碼?是正本戲、古冊戲、還是劍俠戲?卻連一點點細節都想不起來。那已經變成一把被釣起來的鬼頭刀,偶爾還會生猛地跳個幾下,迷人的色彩卻已然褪去。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對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產生過好奇的「陳金龍木偶劇團」產生了好奇,於是使用了過往的學術訓練模式,開始搜尋布袋戲的資料,看是否能找到「陳金龍木偶劇團」。終於讓我在一本《八十八年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裡,發現了一篇石光生教授寫的,題為〈高雄地區掌中戲團生態演變初探〉的文章。裡頭的附錄登載了,成立在1950年,原名「金洲園」的陳金龍劇團。團長陳金龍還有一個弟弟叫陳金雄,他的劇團則稱為「如真園」。
石教授同時比對了1960年的官方紀錄,發現當時高雄縣登錄的三十個掌中戲團,僅有七團仍持續演出,多數老戲團皆已歇業、改行、更名,或遷移了。因此在1990年代還看到陳金龍布袋戲演出的我,很可能是這個劇團最後一代的野台觀眾。更讓我覺得興奮的是,陳金龍的師承是洪文選。洪文選對台灣多數的掌中戲迷來說就不陌生了,他是台灣掌中戲的一代宗師,「五洲文化園」的創始人。陳金龍在掌中戲最盛的時代組團,他還曾經演出過「內台戲」(即是舞台設在電影院、電視攝影棚裡的演出)。「五洲」曾經是撫慰了無數台灣底層觀眾的,那麼重要的戲團,但現在記得的人卻不多了。
據「如真園」的團主陳金雄表示,他自己早期都演古戲(即傳統的故事),樂團最多時曾達九人。古戲後來慢慢被戲偶會翻滾、故事緊湊的劍俠戲所取代,樂團也變成使用唱片來伴奏。到最後劍俠戲也開始不受歡迎了,師傅幾乎都改搬演「金光戲」,劇團只剩一些酬神野台的演出機會。
突然間,我明白了這張在那個無所事事時光按下快門的照片對我的意義。那一年還年輕的我和那三個孩子,看了一場洪文選最優秀的傳人之一的陳金龍師傅,幾近沉入暮色的掌中戲。儘管那戲的口白、技巧、故事,無一留存在記憶裡。但那張照片不只是一個畫面,而是一個伏筆,它為了多年後呼喚我在尋找陳金龍布袋戲團過程中,幸運尋回記憶失物的溫暖而存在,我為人生有這麼一段插曲,而且留下這麼一張線索,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
我一直相信每一張照片都有它存在的目的,就像循著自然原則演化至今的每一種生命,無論是藍綠藻、露脊鯨或迎春花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態區位與尊嚴,只是我們一時看不出來,或毫不在乎而已。然而所有生命都有存在的意義,卻不是所有地層裡的煤炭都能成為鑽石,一張會被記得的照片得有除了物理上的存在以外,更深邃的什麼。
從腦科學家的眼光來看,攝影師在街道、森林裡注意新的事物、新的現象,也許跟人類生存的需求有隱性的關聯。人類做為一種沒有利爪、體能並不出色的動物,最強悍、靈活、充滿想像力的武器就是「大腦」。養過貓的人必定知道幼貓如何在童年時期鍛鍊牠們的狩獵武器──爪子,如何在空無一物的房間裡,彷彿在想像某個神祕敵人存在似地重複著撲抓、攫咬的動作。而人類的童年時光幾乎都花在鍛鍊大腦上。
人類活在一個無樹平原、開放林地,隨時可能遇到獵物或獵食者的環境裡,接受天擇、性擇各種情境的考驗。演化學者科思麥蒂絲(Leda Cosmides) 說為了對應這種競爭的環境,大腦得處理各種有意識無意識的心智活動,因此形成了各種處理「模組」:狩獵、採集食物糧食、追求配偶、與親屬合作、避開獵食者等等。其他生物的大腦當然也有類似的運作,只是在面對現代社會,人腦須形成的對應模組更加多元、也更離奇。人類社交時的合作、欺騙的關係是其他生物難以想像的複雜,生活內容也充滿變化。人腦約有一千億個神經元,每一個神經元平均約聯結另一千個神經元,因此人腦有一百兆個神經突觸聯結,這些輸入的資訊,統合而成我們的意識。我們大腦的神經元聯結的靈敏度與皮質層的活躍,得靠不斷刺激來面對各種新情境,並且產生對應這些情境的反應模組。
想像我們進入一個新城市,就好像我們的祖先踏入一座新的森林。充滿了各種指示路牌的街道,就彷彿殘留各種生物氣味、視覺訊息的林道。這種面對新環境的不安與興奮感,相信許多從事街頭攝影和生態攝影的人都曾經感受到。我們或許可以這麼想,對拿著相機的裸猿來說,森林是某一類攝影者的街頭,而街頭則是另一類攝影者的林道。
街頭攝影不只是拍人事物,也在拍環境。人活在浽溦細雨、太陽、風、霧、閃電、樹的影子的邊緣和黑夜之中;活在馬路標識、商店、盛著拿鐵的馬克杯和閃爍霓虹燈光線之間。有時候用相機進入充滿垃圾、髒亂老舊、猥瑣建築的裡頭,會發現彷彿情人在玻璃上呵氣留言的精緻氣息;走過路燈、空橋、修剪整齊的行道樹下,你會聞到墓石的質地。我常在城市中一走十個小時,甚至整個黑夜,有時候我會想,自己迷戀漫步的理由可能就是這種誘發大腦好奇心的毒癮,漫步成了我活著的見證與理由。
何況在漫步時我的腦中並非一片空白,它有時喚起童年抬便當聞到的氣味:那是班上五十個孩子便當混在一起的氣味,夏季的風正吹上我的前臂,一篇小說從意識底層如浮島般升起,腦中先後響起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的〈天堂之梯〉(Stairway to Heaven)和蕭邦(Chopin)的〈夜曲〉(Nocturne),經過轉角時,青春時期的一個吻則和此刻目睹的一個吻疊影在一起。如果仔細回想,就知道一張在街頭獲得的照片不會只是按快門的一瞬,它是一段插敘不斷的敘事,是意識流、蒙太奇。記憶專家會告訴你,一張照片喚起的是「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這可能是人類獨有的,涉及自我覺知與複雜經驗的記憶形式。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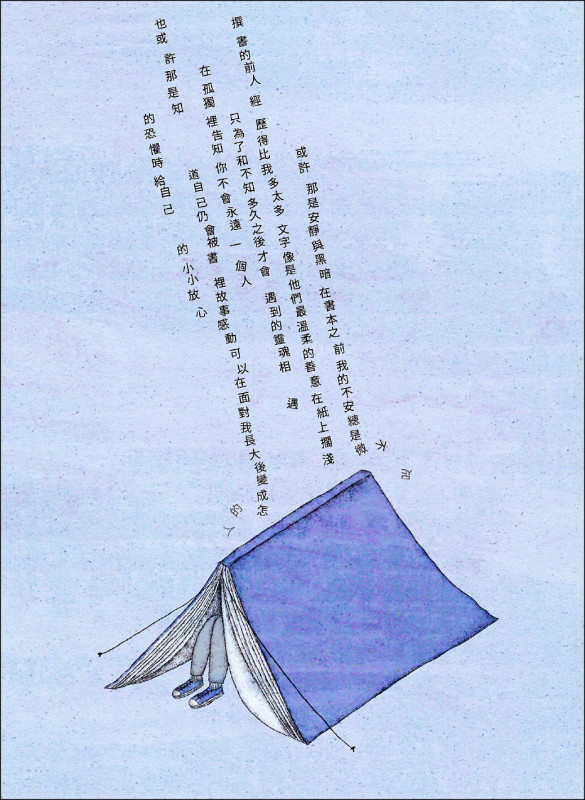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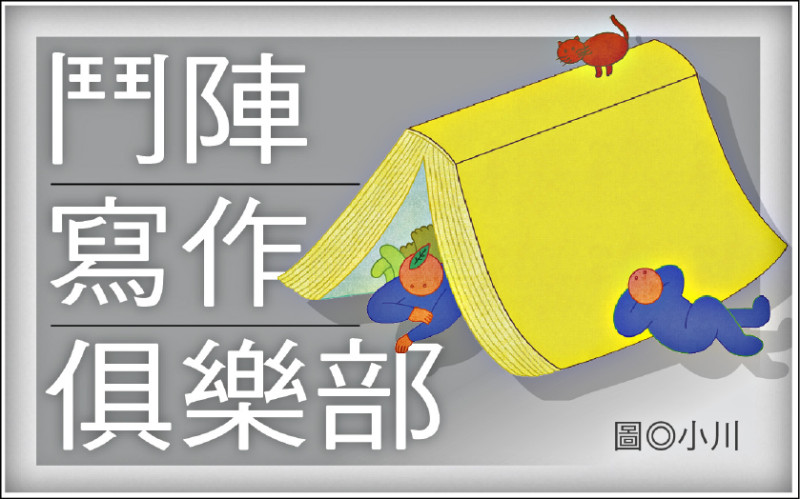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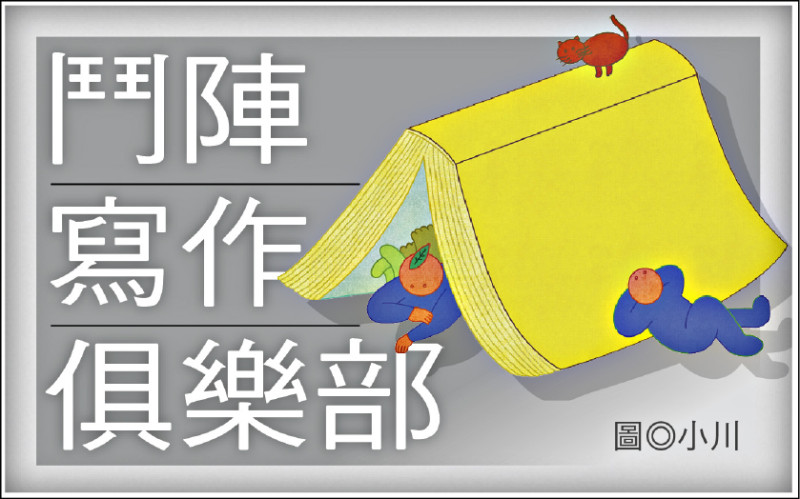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