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謝凱特/隔壁的男生
 圖◎郭鑒予
圖◎郭鑒予
◎謝凱特 圖◎郭鑒予
許多年來,哥哥一直都在我的隔壁,即便多年不說話,不見面,我還是可以感覺得到他就在身旁。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師阿燕的刻意安排,還是兩人的個性造就,男士髮廊裡好幾個座位,他總是會選中央最亮堂的位置,繫上理髮塑膠巾,那神情有一種理所當然,一種天生萬物以養我的理直氣壯。我總是坐在他的旁邊偏店內側的椅子,不想離他太遠,卻又害怕人們的目光。
在模仿和超越之間
我的頭形難看,不是一般人喜歡的渾圓頭形,從耳際往上延伸至頭頂會經過一個近九十度的直角,只要頭髮留得太長,稜角就會炸開叢生的毛髮;但剪得太短,又會蓋不掉太大的臉,這種奇怪的「頭角崢嶸」讓阿燕每次動剪時,都得花上許多時間,用細長的剪刀在直角處細心修剪成最適合的長度。
你跟你哥還真不像。阿燕說。
阿燕是個可愛的女孩,替我理了七年的髮。一次我把她的預約方式給哥哥,從此,我就會從她口中聽到自己和哥哥成為兄弟三十年間未曾聽聞的差異:像是這裡,你哥的頭形就渾圓得多,不用避開這些稜稜角角的地方。
兄弟之間從小就常被拿來比較,成績單上分門別類的項目都能像報紙製表一樣分出幾勝幾負,但是能夠比出頭形的角度和理髮的細節,這還是頭一遭。
真的嗎?原來他的頭形是好看的?
不過他不像你會花很多心思在上頭,他很懶得整理。阿燕說,她常叮囑他,早上出門前至少用水沖一下,吹乾,再抹造型品,否則頭髮壓了一夜,髮蛋白都定型了,再強的髮臘上去也就只是像抹了一層油一樣無甚效果,只是徒惹油膩。但聽到這些步驟的繁複,哥哥總會問她:有沒有更簡單的?我早上都趕時間,要上班賺錢啊。
有啊,我就幫他剪了一個只需要把額頭瀏海吹高的飛機頭,其他用水抹平就好。
設計師說這些話時,可以不必看著手中的梳剪,就能俐落地把我的側鬢削去。一直以來,我以為這些稜角就像一些長在身上的修辭,暗喻我個性上的易和人碰撞的缺陷,因此遇事寧願退卻鄉愿,卻在頭上長出代償性的稜角,害得阿燕總是得費一番工夫處理,剪刀開開合合上百次,只為了一公釐的差異。但事實上阿燕害怕的不是有稜角的頭形,反而不喜歡精心幫顧客剪的髮型卻總因為懶得整理而被糟蹋,像哥哥那樣。
「有很多客人都知道我會嘮叨什麼。只是覺得自己手拙,怎麼用心整理頭髮都像一坨搞砸的生菜,就要求我剪一個不用整理的髮型。」阿燕說,像我這種會花許多時間注意小細節的男生,大約只有兩成而已。
這些話穿過鏡子,在倒影的虛像裡重構出我的哥哥,鏡子中央浮現每天早上都會出現的光景──在我起床前一個小時,就會聽見隔壁房門的開闔,浴室裡嘩嘩的小便聲,吹風機哄哄軋響的三分鐘,而後急急關壓的水龍頭──這一連串聲響,都在我似夢非夢的晨間響起,似乎能聽見哥哥醒時的慵懶,又不得不逼著自己趕忙的動作,在鏡子前撫平鬢邊的亂髮,並將瀏海往上吹送,彷彿在一連串的壓力雲霾裡,試圖吹開一張明淨晴朗的臉,讓額上的機翼能迎空高飛而去。
我們相差四歲,每每當我在人生的上個階段,他已經到了人生的下個階段。我小學時,還不懂造型頭髮,國中生的他已經懂得用扁梳從髮中五五分開左右兩半,沾水抹出中分頭。我國中時,跟著把頭髮縷成兩半卻像書呆,他已經是半熟的高職生,從側邊八二分梳,打籃球時就能以單手帥氣地撥弄髮絲。高中時我梳旁分,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終於長大了,而他已經是大學社團要員,彼時足球金童貝克漢身兼球員和明星獨領風騷,層次短髮往中間抓型成束,他也跟著抓起洋蔥、刺蝟、飛機等等短髮的變體。
這些年之間我們不交談,不互動,只是安安靜靜地從鏡子裡觀察彼此的面孔和髮型,在模仿和超越對方之間,用頭髮進行一場永不停歇的比賽。
被玻璃分成了兩半
其實,我們小時候感情十分要好,就跟一般的兄弟一樣,是都市之中,幢幢樓房隔間裡,其中一間的大玩伴跟小玩伴。
家裡有一扇大落地窗,玻璃是常見的梅花花紋,我和他經常隔著那扇凹凸不平的落地窗玩遊戲,若不是對彼此惡作劇,把對方鎖在外面,就是兩個人隔著厚玻璃,像電影《E.T.》一樣,用手指玩連線遊戲。他頻頻出題,我就得十指並用,讓幼稚園的我那短短嫩嫩的手指,按在他的座標上,我跟上一個,他退後一個,梅花花紋像不規則的星雲,手指就像繁亮閃爍的星星,我那時以為那就是我的星圖。直到他把嘴用力吸在玻璃上,揮揮手,要玻璃另一頭的我也親上來。
我看著玻璃後,他那像小章魚吸盤的嘴唇,咯咯笑著,毫不猶豫地親了下去。
「白癡!」
他站起身來,也笑著,卻不知道為什麼像是開玩笑又像是認真地大聲罵了我白癡之後,自己跑去看電視,留下我一個人在現場。
我總猜想,我和他之間,有一些註定好的裂解,就從這面玻璃開始,把我們分成了兩半。
我開始聽得見父母和親戚對我們不同的形容:哥哥活潑,弟弟內向。哥哥長得好看,弟弟可愛(而我一直都知道可愛是醜的轉注)。後來還有了哥哥不愛念書,弟弟成績優異,哥哥幼稚,弟弟早熟等不同版本的描述。我記不得這些描述到底是我跟他之間的根本差異,還是我為了讓別人記得,努力異化自己,像從亞當身上拔下來的肋骨卻長成了對面的夏娃,而我長出的是從他身上分化出來的特性?
兄弟的分化是一種必然嗎?每當我從自己房間拿出厚厚一疊獎狀跟親戚炫耀,而他總是兩手空空地從隔壁房間出來,拿了親戚的零用錢,不屑地看著我回自己房裡,那一刻,就算只是個小學生,我也明白了這個世界僅是各種條件對比雜糅之下的殘酷,勝負也從兄與弟之間無情地分化。只是我不知道這樣的分化,居然也會延伸到性向上來。
高中的哥哥開始交女朋友了,有了自己的交友圈,在隔壁的房間裡牽了一隻新的室內電話,每個晚上都聽得見短暫的鈴聲響,他即刻接起,以為不驚動這房裡的任何一人,但他不知道嫉妒心起的我馬上隔牆附耳,想偷聽那些說給話筒裡的女孩的密語為什麼不能說給我聽。但電話裝在他房間的另一頭,聽不出那些聲線模糊而無法辨析字句的內容是什麼,就算有時聊得大聲,也都是戀人之外不產生意義的綿綿情話,最後細聽下來只剩生活瑣事,末了纏綿幾句告別的台詞,敲定週末的約會時間地點,眷眷不捨地掛上電話。
「喀……咑……」
約會當天早上我趕緊起床,身兼私家偵探和抓猴者,穿著睡衣佯裝成無甚相關的路人,若無其事地在客廳看電視吃早餐,但視線一直瞥著在廁所忙進忙出的哥哥。他換上破牛仔褲,廉價但表彰率性的襯衫,腰上一條銀鍊子不知道為什麼明明就只會按電鈴叫我開門卻也要掛著一串鑰匙,然後從清水抹髮再到動感彩珠顆粒的髮雕,沾得珠玉滿頭才夠酷炫。
去哪裡?我問。
關你屁事。他轉身出門。
隔壁的房間空了,附耳聽時只有樓上的腳步聲,或是樓下敲釘子的聲音,再不然就是空的聲音,像從耳朵裡抽出一條非常細的線頭,發出非常細小的弦音,線的另一端卻像是扯著心臟似的,有點痠,有點麻,微小的疼痛。再繼續拉著,線頭扯完了,心房就空了。
國中生的我開始練習交朋友了,有了自己的死黨玩伴,還發現自己喜歡男生,那一刻,就像被上帝扭過頭來,我和哥哥走了完全相反的路。我也開始用清水抹頭,用造型品。一次偷偷用了他的炫彩顆粒髮雕,他隔天出門約會前發現,怒不可遏的哥哥和不明就裡的弟弟兩人在落地窗前吵起架來。印象中只記得在齟齬間輕推了他一把,一個踉蹌,他跌在落地窗上,厚重的玻璃碎成了好幾塊。母親聽到動靜過來探看,說:小時候你們最喜歡坐在這裡玩的。
打開門,前往各自的人生
落地窗破了,膠帶黏不回來,母親趁著底下修理玻璃修理紗窗的小貨車經過時請工匠上來換。工匠車上只剩正方格紋的透明落地窗,換好之後,梅花星雲消失了,梅花稜鏡裡的小章魚似乎也游走了。
「你要用我的東西也要跟我講,以後自己用自己的東西吧!」他生氣地撢去身上的玻璃,關上房門,那是毫不猶疑而憤怒的「喀咑」兩個猝聲,關成了兩個世界。從此一人開門,一人關門;我高中日日通勤,他念大學外宿;我念大學和研究所住宿舍,他退伍返家。終於兄弟二人統統住進家中了,也是在房門開關之間,窺伺著彼此的動靜,趁著各種聲音數據研判廁所空無一人的時機,趕緊搶占那個能夠梳洗打扮的唯一空間──關上門,面對鏡子,或用冷水,或用熱風,在唯一可以變花樣的頭髮上用盡心思;打開門,前往各自的人生。
一次母親與哥哥在生涯上起了爭執,換不換工作的問題延燒到哥哥到底什麼時候結婚生小孩成家。哥哥自己腦子裡都沒主意,卻被逼著說個答案,著實氣不過的他從父母主臥房裡悻悻然離開,經過我房間時,他敲敲門,探頭進來,問:你是gay嗎?
我默不答聲,多年來難得的一句話,卻令我為難至不知該如何回答。
「算了。」他說,「算了,沒關係,我擔。」他回隔壁的房間,我附上耳朵,很想聽聽他的聲音,卻只是聽到冰涼安靜的聲音,像我們數年來不說話的累積,砌成一面阻擋彼此面孔的牆。多年來我只是專心地面對性向與環境之間的扞格,關上門,出去尋找自己的天空,卻同時把他關進櫃子裡,留著他處理那些我終其一生都可以還他一句關我屁事的家庭和宗族,一個人盤算著自己該如何應對婚姻與傳宗接代這樣尾大不掉的爛攤子。
我看著他的時間被工作和壓力輾平,無暇顧及造型,出社會後的幾年間,他從浴室出來的樣子完全一模一樣,停留在多層次剪的時代,落在我身後好遠好遠。幾個週末早晨,他會坐在客廳,看著我在浴廁間忙進忙出,目光不小心對上時依舊保持兄弟之間的默契,把視線自動調整成兩條平行線。此後幾天就會發現我的髮蠟少了一點,定型液輕了一點,想起他大概也是想要在鏡子裡找一個更好的自己,或者是有了新的交往對象了,就遞了阿燕名片給他,說,你可以找她剪頭髮。
再隔幾個禮拜後,當我踏進理髮店時,阿燕跟我說,欸,你哥來過囉,他到底是幾年沒換造型啦,現在的人都在用髮蠟了他還不知道。
真的嗎?
自那次開始,我和阿燕就會交換著哥哥的消息。即便我們在家裡不講話,但是每個月我都會去剪頭髮,順便更新一次他的近況:他要考證照、他最近正在念英文、他加薪了,就連他去日本玩了,也是阿燕一邊動著剪刀,一邊說的。
欸,你好歹也主動關心一下你哥,你個性真的是喔……
真是很難相處。
我接了她的話說,看著她費心處理著我頭上那塊會炸開毛的稜角,知道自己的個性就像這種奇怪的頭形,稜稜角角的,閩南語會說鋩鋩角角很多,大概就是指我這種顧著做自己,忘記自己的堅持會撞傷別人的人吧。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他在做什麼。」話點到這,設計師會心地一笑,點點頭,大概這世界的人她也看多了,就像每一個人一種頭形,每一種頭形,都有一種修剪的方法。
一個週末早上,他早上起床,敲敲我的房門,問我:為什麼要先洗頭再吹,然後再抹髮蠟?
我起床說:因為頭髮壓了一夜,髮蛋白變形了,這時候就要用水洗過,讓髮蛋白重新吸水,然後用吹風機的熱風吹出髮流,再上髮蠟。設計師不是跟你講過這些嗎?
我只是想確認一下,你是我弟,我比較相信。
他進了浴室,先後傳來洗頭和吹風機的聲音,接著把頭髮弄得英挺帥氣,對我點點頭,出了門。
視線終於交會了。
阿燕後來跟我說:你快要有新的大嫂了。
真的嗎?我在鏡中看見阿燕工作的表情,彷彿就看見她幫隔壁的哥哥細心剃去鬢角,修整瀏海,露出俊朗的五官。在剪刀開合之間,我和哥哥透過鏡子互相對視,樣貌漸漸清晰,在訊息與推剪聲音的交換之間,我們的表情也默默地改變。
我猜想有些關係就像頭髮,睡了一夜,被壓得死平,像一堵牆。但用清水洗過,恢復彈性,還有機會再次塑型。那些以為好像再也無能為力的扁平,幸好,還來得及重新抓出我們之間的線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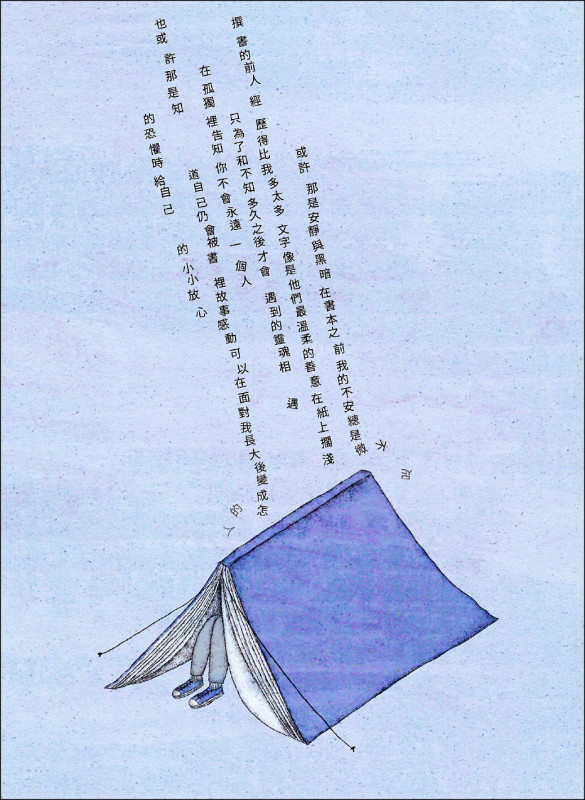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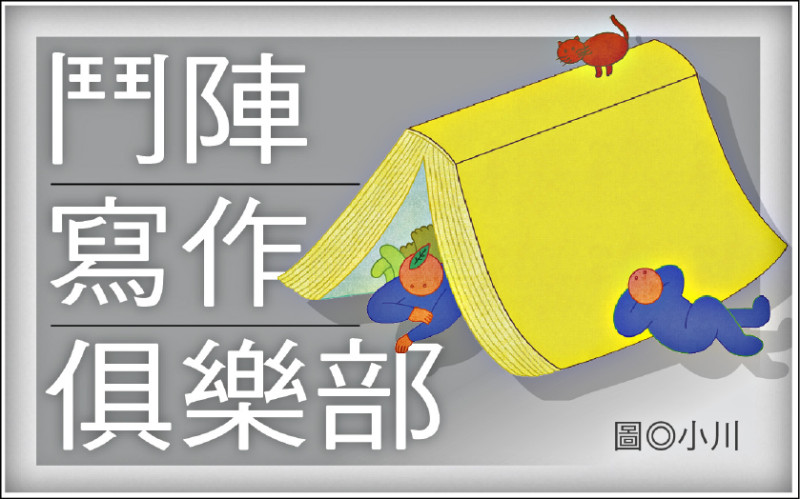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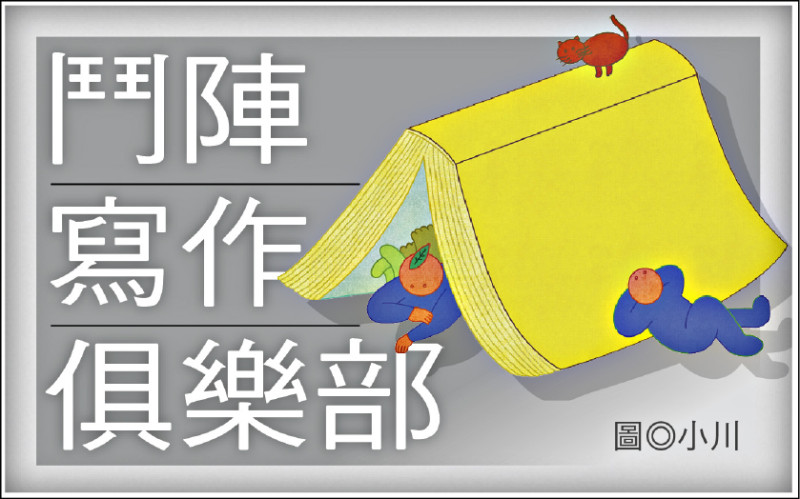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