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作家的藏所
收留疲軟身體,慰藉徒勞心靈。
黃昏的溪流
文.攝影◎吳敏顯
宜蘭人都知道有冬山河與蘭陽溪,卻不一定曉得還有一條比它們美麗千百倍的宜蘭河。
宜蘭河的美,不像冬山河那樣妖嬌,敷粉擦胭脂,還戴著俗艷的珠寶;也不像蘭陽溪那樣邋裡邋遢,一個嗜酒又不修邊幅的流浪漢。宜蘭河總是素素樸樸的,宛如常在廟口遇見的阿公阿嬤,他們面帶微笑,常會講些好聽的故事。
到宜蘭河堤防散步,幾乎和閱讀、寫作一樣,都是我的日課。春夏,我在下午六點鐘離開書房;秋冬,日頭短,我提早一個鐘頭出門。這時,夕陽將沉未沉,彷彿等著我去送行。也有一些時候,不知道它是躲進層層疊疊的群山打盹,或是噗通一聲掉進河裡,拱手讓暮色統領大地。
我散步的路線,先穿過一條門戶大都緊閉,偶有一兩個孤單老人走動的眷村巷道,再走一段田間小路,然後爬上堤防。但夏天小徑雜草叢生,不易辨識路況,我只好順著軍營圍牆,再爬上營區後方的南岸堤防,跨橋過河,沿著北岸堤防向著群山走去。
堤防下,由廣大的麻竹園和果園占據,村舍聚集在這一大片翠綠平野的遠方。
河邊高灘地,有如一本攤開的《四時果蔬大全》,專供才從市區溜出來的人閱讀。這裡那裡,點綴著萵苣和紅色或綠色的地瓜葉,花生往往結伴藏在野草地裡,幾棵香蕉樹站得老氣橫秋,鳳梨會掀起衣襟從頭頂摀蓋自己的頭臉,玉米是幼稚班裡的乖寶寶排著路隊準備去遠足,不斷擴張版圖的南瓜藤竟然試圖爬上陡峭的堤防邊坡。
北岸水湄, 有一處五、六十公尺長,四、五公尺寬,呈帶狀分布的蘆葦叢,是方圓幾公里內難得一見的鷺鷥林,許多白鷺鷥在此築巢群居,間或有幾隻灰色的夜鷺飛來做客。過了一個春天加一個夏天,原本蒼翠的蘆葦叢,顏色愈見枯黃,高度也日漸坍塌,看來已不勝負荷。但在竹圍和樹林急遽消失的情況下,這兒或許還真的是牠們適舒的家園。
我散步的時刻,大部分的白鷺鷥已經停棲在蘆葦叢頂端,卻總會有幾隻晚歸的鷺鷥,還在河面上遊蕩。牠們極力地展開翅膀,先以優美的滑翔姿勢,向著蘆葦叢飛去,看來牠已覓妥即將棲息的位置,未料牠再度搧動翅膀,掠過那些整理窩巢的伙伴,繼續貼著河面,朝落日的金光飛去,經過兩處河灣,再依依不捨地調頭,彷彿對準映著夕陽的河面攬鏡梳妝,讓金色的光芒鑲在牠每一根羽毛末梢,沿著剛剛掠過的河道上空,緩緩地回到蘆葦叢。
我的腳步常隨著這些遊蕩的鷺鷥移動,先是迎著夕陽朝前邁進,再跟著牠們調轉過身子,以倒退走的方式繼續向落日的方向走去。一面看著牠們背著金燦亮光,陸續飛回蘆葦叢,一面看著自己的影子被夕陽愈拉愈長。這種為了讓目光追隨那調頭飛翔的鷺鷥,時而倒退走的散步方式,連自己都覺得整個人也像那鳥一樣,自由自在地在河道上空迴轉盤旋,且很快成為我的隨興遊戲,樂此不疲。
鷺鷥最後一趟巡航,看來不像是為了找尋晚餐,或為黑夜來臨準備消夜。也許,牠們像我,經過一天的閱讀和寫作之後,必須要活動一下筋骨,紓解心中的鬱結或困惑吧!黃昏歸鳥,如果遇到一樹麻雀或其他的鳥類,肯定吱吱喳喳地爭論個不休,而鷺鷥畢竟是紳士,牠們只禮貌性地彼此打個招呼。
熟悉的山影,在晴空下分不出太多的層次,卻在黃昏時刻褪下一件又一件華麗的衣飾。我想,群山在此刻設下多層次的布局,定是怕落日迷路,怕那個喝得滿臉通紅、醉醺醺的太陽公公,不小心跌跤吧!氣象局說有颱風逼近台灣,那些鷺鷥和夜鷺或許知道天氣即將變化,或許並不清楚。縱算知道又能怎麼樣?牠們這樣的家,沒有門沒有窗,也沒有樑柱屋瓦和磚牆。只要山區或平原的半天豪大雨,可能就把蘆葦叢淹沒,甚至夷平。
我們所在的住居,不也如此嗎?水源能源一天天減少,氣溫一年年升高,空氣一天比一天汙濁,糧食一年比一年短缺。人們知道嗎?或許知道,或許並不清楚。而知道又能怎麼樣?大家照樣開著車四處跑,照樣全天候地開著空調,夜間無人行走的田野裡照樣燈火通明,照樣吃大餐,照樣糟蹋水源,照樣肆無忌憚地把海洋當做垃圾場。
我在北岸堤防走了一段時間,會遇到河上游另一座橋。有時我過橋,從南岸堤防往回走,但南岸堤下的水防道路車輛多,感覺不如北岸安靜,空氣也沒有北岸乾淨,所以我大半還是順著原路走回家。
這時候,天色逐漸暗下來,高灘地上的《四時果蔬大全》跟著把書頁合攏,只剩河面依舊映著些許銀亮的光。朝著我來時的市區望去,一幢一幢樓房紛紛亮起燈光,先是零零落落,很快就繁如星朵。看來,只有蘆葦叢裡的那些鳥兒,才真的跟著太陽一起作息。 ●
金恩巴的海浪
文.攝影◎夏曼.藍波安
好久以前,我靈魂先前的肉體曾告誡我說:「孩子,長大後不可在金恩巴那兒的海域潛水射魚。」當時我人還小,不知父親說這句話的意義。二十年後,父親告訴我說:「在金恩巴那兒的海底有個天然洞穴,我曾經在那兒潛海撈過溺死的族人。」當他說這則故事給我聽的時候,我已經回蘭嶼定居,開始在金恩巴的海域潛水射魚,並且逐日逐月地喜歡了金恩巴這個地方。
金恩巴是一個獨立礁岩的名字,達悟語言的字義說是:「被海浪斧削(侵蝕)的礁岩的意思。」然而從外海觀看獨立礁金恩巴,它卻像個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頂上有頭髮(羅漢松)的人頭。
連接金恩巴的陸地全是大塊的鵝卵石,面海左邊有兩個天然的海池,一道小海溝通大海,是大小魚兒進出的捷徑,於是小海池常是小魚兒棲息的天堂,父親說:「小海池常是我在凌晨夜間漁撈大鸚哥魚、大石斑魚的地方。」我回想,我兒時經常在凌晨被父親喚醒吃生魚片,那些魚兒就是從這個小海池捉來的,面海右邊也是一個天然的洞穴,夏末秋初更是海蛇浮生下一代的窩,阿爸說:「在冬末春初的朔夜漲潮時段,龍蝦便爬出礁溝,在洞穴裡的平台集體出遊,一把火炬的照明,龍蝦暗紅的眼珠如是天空的眼睛,動也不動地任你手掌捕抓。」然而金恩巴背面的坡地是一面很陡的草地,整年飽受海風的吹拂,於是草皮宛如是美拉尼西亞人綿密而蓬鬆的髮絲,腳掌踩上去感覺像是踏上雲端的舒適,然後,就在初春時分,野百合便從千孔的草皮根莖裡鑽出蒸發美麗,在二、三月裡綻放出全是面海的乳白花瓣。因此金恩巴是三面陡峭的地形,我測算走下去的坡度是七十五度到八十度左右,是人跡罕至的地方。
回蘭嶼之後我經常在這兒潛海,對於金恩巴的天然景致未曾在意過它存在的美麗,也不了解海陸生態的變換,就像我父執輩們的思維一樣,只在意潮汐潮水與魚類的關係。有一天,從我達悟人的禁忌文化而言,那一天是潛水人潛水射魚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說,過了那一天就不可以再去使用魚槍潛水射魚,因為次日就是我達悟人的飛魚招魚祭。
那一天滿潮的時段很晚,潛海上岸時太陽已入海了,陰暗的午後讓我的思路湧出,坐在礁石上抽煙,想著父親告訴我這兒的傳說故事,說是:「金恩巴是靈異的聚會所。」想著媽媽生前跟我說過的話,說:「潛海前,說出你是誰?你的家族,好讓金恩巴的遊魂認識你的靈魂,你的體味。」後來這句話成了我到現在潛海時的護身符。
前幾年, 就在媽媽眼瞎, 她眼珠的世界成為黑暗;父親的痴呆,日夜昏睡分不清早晨與黃婚後,我回到金恩巴,但不是在午後,而是凌晨的三、四點鐘。手電筒照明我的路,父親說,過去他在半夜來這兒抓魚,腳掌就是他的手電筒,我很難體會他這句話,但父親確實是如此辛勤地養育我與小妹子。
我似乎沒有預感,那一年的三月父母親同時離開了我。我凌晨三、四點鐘去金恩巴潛海,為父母親抓魚,我想的除了是回饋他們在我兒時給我的芋頭與新鮮魚外,但彼時我內心底層卻是一股想攢入最為沉靜的場域,只有天籟的原音,海風與海浪。在凌晨,我孤寂的面海,右手邊是一個深邃墨黑的洞,每一波宣洩的浪,洞裡便發出低沉「轟」聲,如是惡靈酣睡的鼻音;左邊即是一尊人頭形體,彷彿是夜夜伴著我望海星空的真情摯友。如果說,有上帝的話,金恩巴就是上帝給我的戶外教堂,於是我一絲恐懼也沒有。海裡的黑,也許比陸地更黑吧,但我一個人沉醉在她的懷裡,在墨黑的水世界用一隻手電筒在水世界胡亂掃射梭巡獵物。一個人!獨自一人!原來,孤獨是幸福內臟,發覺自我存在(自戀與自卑)的本質。黎明降臨後,我立刻奔跑回家,為他兩個老人家炊火備早餐,午夜過後,我又獨自地再訪金恩巴,夜夜在這兒傾聽金恩巴給我的原音,也藉著它洗滌文明在我外形貼的標籤: 自戀與自卑。
父母往生後,午後我依舊造訪金恩巴的海浪,我知道,我的父母親、大伯、我的五個祖父在這兒聞得出我的體味,還有我兒子的靈魂。
●
非處所
文.攝影◎黃錦樹
如果你是都市人,大概會眷戀於某間咖啡館、電影院、美食餐廳、某一條大街、某處古蹟……那可以一再重複造訪的──甚至某個知交的家。偶爾可以把生命固定在某個由具體的物構成的定點,讓精神可以獲得暫時的喘息,稍緩其生之疲憊。好像重新確認自己的存在,重新整頓彷彿即將散亂的生命形式。所以不難理解,許多人都渴望一個較穩定的空間(猶如老巢),讓精神可以留駐。彷彿可以更容易地證明自我的同一性──「我」的存在的延續性──而非處於飄搖的、斷裂的處境。然而時間的本質其實更接近後者,尤其是線性矢量、遙遙指向深淵(不再有二度降臨)的現代時間。
不是自憐,無意誇大,但遠離多年生活的地方,千里的遷移;又屢經搬家,大概不免會造成對位置的感受上的錯亂(這當然包括了地方感)。或許更深地緣於移民社會本身的時間性騷亂──總是被歸類為時間差錯的產物──錯誤時間裡錯置的生產。殖民主義廢棄物的後裔。
然而對我而言究竟有沒有那麼樣一個可以讓精神暫時休憩的場所呢?曾有。
我應該用過去式。如今我大概只能描述一個擦拭的過程。套句俗話,時間是場騙局。
許多年前,是一片膠林,不論是凌晨的漆黑,還是初晨的暖陽和沁涼的霧;一小片簡略圍起的園子,種了變葉木、指甲花、鳥椒、一株米蕉和南瓜,都營養不良地結了果實。家居不遠處的那片彷彿不曾乾涸的沼澤,有釣不完的鱧魚、抓不到的鬥魚,交響著猿啼與蛙鳴(來不及認識牠們的品系),遍布鳳梨科的熱帶植物,莎草、老黃藤、碩莪。永遠深茶色的水,丹寧酸與腐植質。年輕時寫的小說〈魚骸〉的主要背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切都消失了。發展中國家瘋狂地向它們期許中的現代發展,樹砍光了好蓋住宅,或者種植高經濟作物。於是失去棲地的獮猴、四腳蛇、雉雞只好到處流浪,淪為餐桌上的野味。
那也是我們曾有過的一切:一如時間本身,無法重回,不可逆。即使希望在夢裡重新體驗,也難以強求,夢並不能訂做或點選。每回重回那些遺址般的地方,最直接的感觸是──不是的,不是這裡。我來錯了。也許是在錯誤的時刻。
我所眷戀的我曾擁有的它的過去,被時間這塊不朽的橡皮,擦掉了。
大概每一代人的感受都近似:熟悉的世界在快速的變遷,往陌生的面貌走。
但那也是下一代人感受力最強時的世界,他們也將面對那個世界的崩落──它也許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但對於體驗者而言,最美好的一部分卻永遠隨之遠逝了。它曾經短暫地贈予生活於其間的人,但它也是有壽命的。無奈的是,認識到這一點時,往往已屬事後。或許這正是我們的世界的根本屬性,即使是最具體、真實的此刻當下、最可期盼的未來,也都帶有過去的意味。即使我們的肉身,也不免如此。這樣說來,它就如同記憶。記憶的屬性即如此。只要腦子的功能正常,它即可以發揮它驚人的延展性──重組世界、重塑時間的能力。肉身易朽,記憶的陰影是遺忘。因而我們需要額外的物質媒介,音符、色彩、影像、文字……而文字堪稱是成本最低的裝備了。當然是指寫作這回事了。追回逝去的時光,改換它的面貌(反正沒有實物可以對照),加加減減,在虛構敘事裡重新把時間展開。一如我們經由閱讀,開啟他人的意識,進入一個個似真非真的世界。在那裡,可以與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的事物相會,遇到曾經活過的亡故多年的人。也許,還可以遇見死後的自己。如果未來注定會過去,所有的過去都曾經是未來。因此,我輩的祕密基地無非是書,語詞,字;或一種行為叫寫,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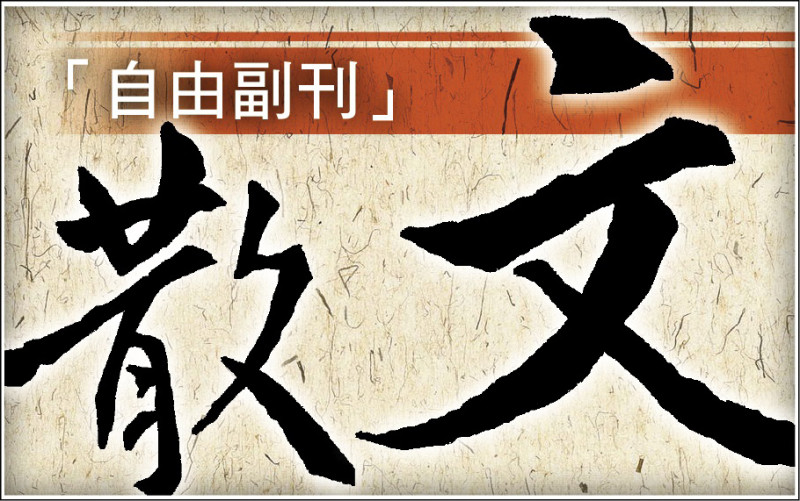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