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我常去的倫敦書店-下
文.攝影◎李有成
不只是書店而已
書籤書店還有不少第三世界作家或弱勢族裔的創作。我最早注意到帕慕克(Orhan Pamuk)、阿思藍姆(Nadeem Aslam)、馬穆德(Tariq Mehmood)等人的作品就是在這家書店。從某個意義來看,書籤不只是一家書店而已,亦且是一個資訊交換中心。這裡可以找到不少有關英國工會和工運的出版品,或者其他進步團體的活動訊息。這裡當然看不到休閒、管理、減肥、美容、賺錢的書;對書籤書店來說,寫作和賣書是很嚴肅的事,是為了改變現狀,為了追求與實現一個更理想的未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書籤書店不大的店面中央,擺了一件雕塑模型,四周或立或臥零散地置放一些新書。這是蘇聯藝術家泰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0)著名的第三國際紀念塔(the Monument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的模型。泰特林於十月革命兩年後(1919年)設計了這座紀念塔,因此也被稱為泰特林之塔(Tatlin’s Tower),設計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歌頌新社會與新時代的到來。泰特林的原意是要在古都聖彼德堡建造此紀念塔,因此他刻意尋找一種新的建築語言,企圖與聖彼德堡井然有序的建築傳統對比與對話,最後呈現的是一座雙螺旋狀幾何結構的斜塔。為了展現新蘇聯的新興與強大,這座塔原來設計高四百公尺,以鋼鐵和玻璃為建材,建成之後遠遠超過三百公尺高的巴黎艾菲爾鐵塔。塔底層是方形建築,裡面設置會議廳和會議室,方形建築旋轉一圈需時一年。
在方形建物之上——即紀念塔的中心——是一幢圓筒形建築,主要為行政大樓,旋轉一圈需時一個月。最高的地方則是一個錐形建物,屬新聞與資訊中心,旋轉一圈則需時一天。泰特林這個構思前衛、隱含無限希望與憧憬的紀念碑兼建築設計,後來淪為紙上談兵,並沒有成為實品。在瑞典首都斯德歌爾摩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有這麼一個模型,書籤書店裡頭的這個模型約有一人高,跟原來的構想當然不成比例。蘇聯與其東歐集團解體之後在書籤書店看到泰特林之塔,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天使害怕駐足的地方
談到激進或左派的書店,在倫敦東區(the East End)還有一家。一般人到倫敦旅遊,會往東區走的大概不多,最多到磚巷(Brick Lane)看看,或者周日去逛逛史畢特爾菲德市集(Spitalfields Market)。這些年來每次到倫敦,不論停留時間長短,我總會到東區走走,愈了解東區,尤其東區的人文與社會歷史,愈覺得東區神祕迷人。
這裡是另一個倫敦,曾經是大英帝國光鮮亮麗的背後最為難堪的一面——是破落、窮困、髒亂、危險、絕望所構成的人間地獄,在大英帝國揚威海外的高峰時期,這裡只住了三種人,粗分為:貧窮、很貧窮,以及非常貧窮。
1902年,傑克‧倫敦(Jack London)化裝在這裡實地探查之後,把這裡的居民稱為「深淵裡的人們」。東區固然是慈善團體如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的發源地,卻也是激進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溫床。這裡更是罪惡淵藪,不只一次發生過英國犯罪史上最令人髮指的連環兇殺案,也曾經是倫敦惡名昭彰的黑道樂園。用英國話說,這是「天使害怕駐足的地方」,也是被上帝遺忘的角落。今天的東區當然沒有這麼可怕,其主要居民除了一般勞工階級之外,就數南亞移民居多。在白教堂大街(Whitechapel High Street)上就有一座富麗堂皇的東倫敦清真寺(East London Mosque),大街上也盡是南亞人經營的各類商店,我還在清真寺附近的伊斯蘭教文物商店買過《可蘭經》的英譯本。
在白教堂大街上有一座白教堂美術館(Whitechapel Art Gallery),緊鄰美術館的是一家肯德基速食店,此速食店旁邊有一條只能容一個人走的狹窄小巷弄,叫做天使弄(Angel Alley)。巷弄很短,大概只有一、二十公尺,相當隱蔽,過去一直是娼妓出沒的地方。弄底即為速食店的後方,是一塊不算大的空地,右邊的建築其實就是白教堂美術館,從美術館樓上的咖啡廳可以清楚地俯瞰這塊空地,而且可以看到天使弄左方建築的牆壁。天使弄的這一面牆有一塊銅製看板,上頭刻著數十個人物肖像,裡頭赫然包括了巴金與喬姆斯基。
這些人物都是近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東區傳統上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重要根據地。19世紀時東區的維多利亞公園(Victoria Park)不時有各種政治聚會與演講,參加者不乏無政府主義者。英國本來就有不少本土的無政府主義者,莫禮思、王爾德都是著名的例子。19世紀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就在倫敦東區推展無政府主義運動,此後香火不斷。
位於天使弄的自由出版社(Freedom Press),就是英國歷史悠久的無政府主義出版社,創立於1886年,同時出版《自由》(Freedom)雙週刊,經營自由書店(Freedom Bookshop)。書店在天使弄的弄底,從一個狀似倉庫大門的入口處進去,上二樓即可看到書店內部。書店面積很小,約七、八坪大,可以容納的書相當有限,不難想見這些書的議題相當集中,而且都與激進主義或另類思想有關。要找無政府主義或激進思想——諸如反戰、反全球化、反法西斯主義等的書,尤其是小出版社的出版物,這裡往往會讓人有意外的發現。我就曾經在這裡買了好幾本沒有在大型書店發現的有關國際情境學派(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著作。跟書籤書店一樣,這裡也有不少有關工運或社運的報紙、手冊或宣傳品,顯然也是激進政治與社會活動的重要資訊交換中心。
我如果到東區,時間許可,都會轉到自由書店看看。書店偶備紅酒或白酒,客人不論生熟,一杯在手,可以和店員暢論天下大事或臧否天下人物。這哪裡是賣書?簡直是在清議或座談。自由書店就是這樣自由自在的地方。
東區犯罪傳奇
我喜讀偵探小說,但因為時間有限,閱讀範圍相當狹窄。福爾摩斯探案是偶爾回頭重讀的經典,除此之外,我偏好美國的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英國的詹姆絲(P.D. James),歐洲作家中我則獨鍾瑞典饒富社會意識的曼凱爾(Henning Man kell)。我對所謂的真實犯罪(truecrime)也興趣盎然,不過我比較留意的有三個案子:一個是1811年冬天在東倫敦雪德威爾(Shadwell)所發生兩家七口的命案,也被稱為瑞克利夫公路謀殺案(the Ratcliff Highway Murders)。大文豪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後來還發表系列專文討論這個案子。另一個案子則是1888年夏秋之間發生在倫敦東區白教堂一帶的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連環命案。受害者大都是年華老去的妓女,兇手身分成謎,一百多年來各種調查臆測,穿鑿附會,眾說紛紜,環繞著這些案子的各類書籍與影視產品,簡直構成了規模不小的文化產業。倫敦不只有專門追蹤開膛手傑克犯案地點的徒步導覽活動,學術界甚至有所謂開膛手學(Ripperology),當然也有開膛手學家(Ripperologist)。
我很感興趣的另一個真實犯罪,涉及1960年代橫行於倫敦東區的黑道家族柯雷兄弟(the Krays)。柯雷家族有三兄弟,其中老二列奇(Reggie)和老三隆尼(Ronnie)是雙胞胎,隆尼尤其心狠手辣。三兄弟出身貧寒,在東區起家,青少年時就經常惹事生非,後來一統東區黑道,最輝煌的時候曾經發展到倫敦西區(the West End),並且跨洋企圖與紐約黑手黨合作,甚至風光結交黨政社交名流,開酒吧、設賭場、殺人勒索、呼風喚雨,當然也造成腥風血雨。蘇格蘭警場(Scotland Yard)忍無可忍,將他們拘捕下獄,1969年3月8日,老大查理(Charlie)被判七年徒刑,列奇和隆尼則都被判終身監禁,判案的法官當庭痛斥這雙胞胎兄弟,並宣布他們的刑期不得少於30年。
隆尼後來在獄中因心臟病發作,1995年3月17日病逝。20世紀的英國曾經見證三大葬禮:一次是邱吉爾,一次是戴安娜王妃,另一次就是柯雷家的隆尼。隆尼出殯時,媒體爭相報導,各路英雄好漢齊聚送葬,東區更是萬人空巷,識或不識的鄉親沿途相送,引為世紀奇觀。列奇在獄中度過32年後,由於英國輿論不斷請願求情,終於在2000年8月獲釋就醫,六周後卻因癌症於10月1日病逝。列奇去世後,在其妻堅持之下,謝絕黑道參加葬禮,規模相對小了不少。柯雷兄弟的生平際遇如今已經成為東區的市井傳奇,他們的故事被拍成電影,直接或間接跟他們交往的人不少也趁機出書謀利,他們當年的活動照片更高掛在東區某些酒吧和咖啡屋的牆壁上。這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文化產業。
一葉知秋的「一級謀殺」
因此,除了前述幾家相當另類的獨立書店之外,我也特別喜歡市中心查令十字路上的一級謀殺(Murder One)書店。一級謀殺書店真是店如其名,是一家非常專業的與犯罪有關的書店。逛這家書店樂趣無窮,尤其是在真實犯罪方面,經常可以看到真真假假的理論和敘事。就我的興趣而言,一級謀殺書店很少讓我失望。
2005年夏天我到倫敦,幾次經過一級謀殺書店,只見大門深鎖,好像準備裝修。今年有學生到倫敦開會,我託他到一級謀殺書店幫我找詹姆絲的一本舊作,他回來時告訴我,書店搬家了,還在查令十字路上,只是搬到原店的對面,而且店面變小,原來書店還兼賣科幻和言情小說,科幻部門已經結束,但還保留言情小說部分。一葉知秋,倫敦的獨立書店可能正面臨日漸逼近的寒冬,能不能存活下去,能不能再看到春天,真是教人捏一把冷汗。
愛爾蘭小說家托爾賓(Colm Toibin)曾經這樣比較水石書店過去十年間的變化:「十年前,每一位經理可以依自己的品味和判斷選書與下訂單。後來這一切都交由中央辦公室的人來處理,這些人樣樣都行,除了選書之外。」這種情形一般不會發生在獨立書店,因為獨立書店店面不大,必須認真過濾,慎選書籍。獨立書店其實充滿了驚喜和意外。你可能在書店的某個角落找到你遍尋不著的書;你可能找到某些小出版社所印行的你正需要的書;你也可能在書店中碰到同好互相交換閱讀資訊;你也可能遇到真正懂書的店員,他不但可以完全憑記憶告訴你書的擺放角落,還可以推薦你相關主題的書籍,甚至和你討論某些書的內容。他們知書愛書,不只是賣書而已。他們是以感情甚至使命經營書店。
倫敦評論書店的經理史狄威爾說過:「我們賣『書』,不是售『貨』(products)。」言簡意賅,可以擺在書店當經營格言,自我勉勵,不過卻也一語道盡獨立書店令人驚喜和意外的原因。
賣書其實是個很特別的行業,書店貴在氣質,貴在特色,而不在規模大小,也不在店員有沒有穿制服——讓書店店員像高級餐廳或飯店的服務生那樣穿上制服,對我來說是很難想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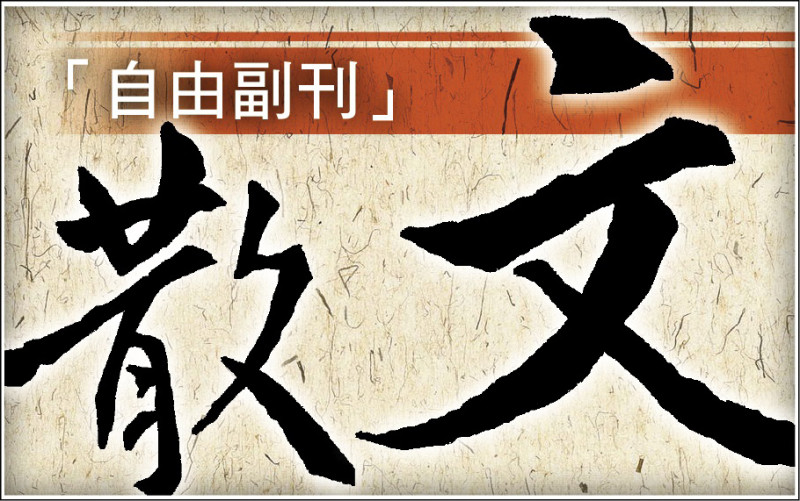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