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林文義/華麗廢墟
◎林文義
說是不經意,還不免遲疑地回眸一望。入夜後的自由廣場,存在著猶若古墓荒寒的陰惻意象──北京的天壇,強制著台北的日常視覺,符咒般祕教儀式不忘地,他從中國而來。
已不再鄙夷也直感淡然,只是覺得就留下戒嚴威權年代的歷史遺跡吧:中正紀念堂。向晚時分,儀隊踏著畫一的整齊步伐,降下那巨大的國旗。古墓般說是莊嚴實是猙獰的巨大建築,那兩扇沉重的赤銅大門,緊閉謝客,終究得以給已經坐了四十二年的蔣介石銅像,有了獨自靜思的時間;老先生在幽長的死眠中,銅像和肉身距離五十公里之遙,會彼此呼喚嗎?
我將心比心,在不經意回眸之時還是多少有種不忍。台北市中心凱達格蘭大道與桃園大溪山間的慈湖,人鬼兩殊途,何以老先生依然難以真正返鄉?漂泊的死靈魂啊,一定念念未忘海峽隔水一方的:中國浙江奉化溪口鎮。離開原鄉,七十春秋生死兩茫茫……
老先生告別的時候,正是我服役於台南府城的後勤補給單位,全軍戒備,不得休假,一整個四月份,必須配帶黑紗……彼時前輩作家文情並茂地發表〈黑紗〉,形容病逝的領袖有著「祖父般慈祥的容顏」,相信是真情流露的追思感念;1975年春夏之交,青春的野戰服少年都有鄉愁和苦戀,只是未諳老先生的生離死別比我們還要哀傷,還要深沉。
幾年以後,那時還叫做「介壽」路的總統府對面的眷村被全部遷移、拆毀,圍籬森然地阻隔在中山南路、愛國東路、信義路、杭州南路之間,巨大的土石構工開始進行了──舊時代過去,逐漸鬆動、瓦解的獨裁和威權……新時代接手的政府領袖,理所當然是老先生的長子,那個曾被當人質在俄國的左派改革者。
於是,我們終於拜讀到十年後的一首驚豔但令人不禁為作者捏一把冷汗的政治詩──
.
清明時節
雨落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
幾萬人群集佇立
是什麼樣的歲月呵
有臂膀刺青的人
他噙滿淚水
有扶手杖著中山裝的人
他默望天空
.
清明時節
雨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幾十萬人蜂湧蠕動
是什麼樣的年代呵
有熟嫻日語的人
他低頭不語
有童年生在台南的人
他凝視遠方
.
是誰的銅像啊
座落在台灣的城鎮裡
是誰的骨灰啊
灑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劉克襄(七○年代),1985
.
北京天壇形式的巨大陵墓或是紀念碑般的超級靈骨塔?方落成揭幕的紀念堂,老先生流金般同樣無比巨大的銅像,微笑地面向一千公尺外的日本殖民時代的總督府;生前他在那裡掌控戰後仍舊是被再次殖民的台灣人九千四百多個日子,死後是否依然不捨王朝地精神視事?
建築師朋友從南歐考察回來,特別指陳那白大理石構築主體是來自義大利,紫藍琉璃瓦謂之:「王」者之邑。一旁靜聽許久,向來溫文爾雅的畫家,意外冷語地插話──什麼「王」者之邑?是「亡」者之邑才對!只有我噤聲不語,只直覺紀念堂說是仿北京天壇的意涵,卻十足像一座靈骨塔般地過度龐然而猙獰。
再幾年後,劉克襄的詩,靈犀在心地回應我彼時深思的感同;自自然然的用筆,以微薄的行動參與,80年代,多麼美麗的遙遠記憶了。那是青春的義無反顧或是愚癡的自以為是呢?沒有黨,只有自由的黨外,中間偏左的理想主義,一相情願地深切祈盼島國的黎明真正降臨。
老先生,被奉座(禁錮?)在紀念堂中央的您,快樂嗎?寂寞嗎?年久月深,已然暮年之我,不再嘲謔您,歷史早已殘忍地將您定位,最大的懲罰以及悲哀是至今,不容您歸鄉。
離鄉遺事……小說家老友昔時初集命名,彷彿先知預告死亡紀實;離鄉多沉痛,遺事何榮耀和屈辱?老來靜讀百年歷史,中國與台灣其實一樣不幸,未來的孩子啊,祈盼更美好。我們這一代的悲歡離合,終將如流去的逝水,冷月無聲地悄然寂岑,猶如夜來回眸一望中正紀念堂的荒寒和落寞,想著被禁錮的死靈魂。
幸好分置自由廣場兩端的音樂廳、歌劇院的宏麗華彩,多少讓那難看的紀念堂在幽深、灰暗的氛圍中有些人味的鮮活生息,否則如入鬼域。晚安了,老先生……恍然之間,彷彿是自己在向自己致意?緊閉的銅門後面一片廢墟,我正要進場聽音樂會,華麗之心油然雀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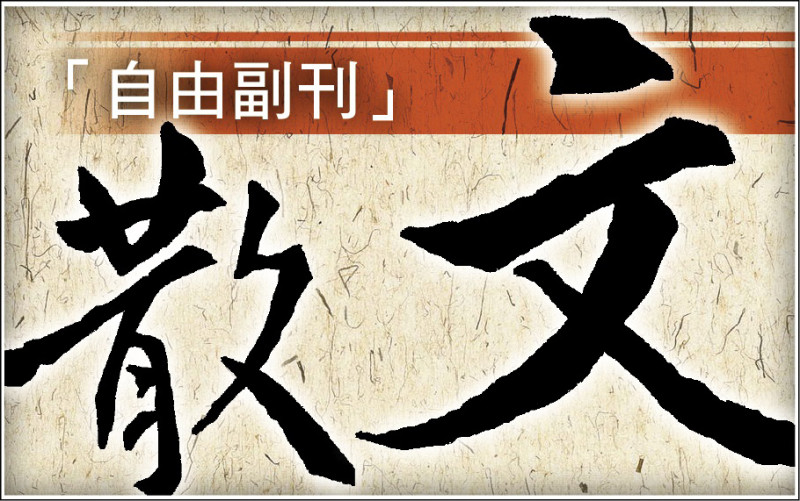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