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瘋人船上的同行者
◎董啟章
同行者:
我們大概都同樣沉迷於那種瘋人的故事。那樣的故事讓我們感到沮喪,但也同時感到安慰。彷彿,我們因此知道自己的旅程不是孤獨的,縱使同行的陪伴者都是瘋子。我們都鄙視那些瘋子, 但我們也同時感到羞愧,因為我們深知道,自己其實也是瘋子中的一員。瘋子從來也是互相鄙視的,這現象在瘋子間可謂十分正常。
你說早前常常無故被街上的一個流浪漢襲擊,給他扯頭髮,甚至拳打腳踢,而你也還以顏色。你說也許他以為你是妓女,而瘋子仇恨妓女也是時有所聞的事情。一個作家淪落到被視為妓女,這對你是個比拳頭更沉痛的重擊吧。最近你卻說,你和那流浪漢成為了朋友。這的確是個令人意外的逆轉。當然,所謂成為朋友,可能只是同病相憐,不再互相攻擊吧。原來,他當初之所以襲擊你,是因為他以為你是那種生活無憂卻跑去歐洲體驗生活的東方女子。他說他最憎恨這種人。而他,他說,他是個詩人!天啊!原來是同道中人!你遠遠跑到西班牙去學跳舞,學唱歌,學演戲。
你說你不滿寫作這種形式的局限,和作家所得到的可恥待遇。但你到最終還是會寫下去吧?特別是當你遇到這種瘋子的故事的時候。它是真相的無情撕揭,但也是嘲諷性的同舟共濟。你說你快要窮得沒錢吃飯,沒錢洗衫,蓬頭垢面,形同流浪婦。問題並不在於自討苦吃,而在於,自己是不是流浪漢眼中那種虛矯的人?如果你真的和他同坐一條船,你就是真誠的。但那是一條「瘋人船」。
在歐洲中世紀的繪畫裡,「瘋人船」或「愚人船」的意象屢見不鮮。它一方面含有宗教諷喻意味,意指人生旅程中的墮落者,犯罪者。另一方面,也反映現實上把瘋愚者標籤和區隔的情況。細看那些畫像,除了對當中的癡情醜態感到噁心和寒慄,也會隱隱然看到,當中有許多熟悉的面孔。我們都坐上了這艘瘋人船,漂泊於幻影連連的茫茫大海裡,看樣子是無法回航的了。你要小心,你的流浪漢有一天也許還是會攻擊你,縱使他知道你是他的同類。我們這種瘋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同類。
而我也不比他富有同情心。幸好我們在船上坐得不近,要不大家非但不會相濡以沫,相反大概還會互吐口水吧。
同代人
月半青春
◎周芬伶
嬰兒有嬰兒肥,青春期也有青春胖,我不能算頂胖,那時身材也很可觀,單性的生活令人肥胖,彼時期的照片都被銷毀,實在慘不忍睹。
女校裡同學不是過重,就是太瘦,少有恰到好處的,我的好朋友即是大竹竿,身高一七多,體重四十幾;另一個是大胖子,體重七十幾,那也不是減肥而成或吃出結果,而是正值發育期,麵糰還沒發好,大家奇形怪狀,也沒有時間注意外貌,反正修女般的白衣黑長裙遮住一切。
有的人還比邋遢,皮鞋不擦,灰撲撲的,故意讓它開花,有的人頭髮東翹西翹,可以看出她昨晚的睡姿,大家都長痘子,嚴重的臉爛半邊,輕微的斑斑疤疤。
極少數愛漂亮的女生,腰束緊一些,裙摺短一點,晚上跟男生開舞會,上課不斷偷照鏡子,但也不是真正漂亮的人物,記得有一個小個子,有張南瓜臉,另一個頭髮自然鬈,嘴邊有顆大黑痣,像大姨媽。
漂亮的人物不是沒有,大都是運動健將,或會畫畫唱歌的小藝術家,但也不漂亮,在這階段大家似乎重才不重貌。有一個樂隊指揮,高高瘦瘦,長得算清秀,許多人迷她,作業展覽時,我特別翻她的作文簿,天啊!字真醜,錯字也很多。
那一兩個長得不奇不怪的就是珍品了,記得有一個臉蛋紅紅的小女生,被譽為校花,大家喜歡去偷看她,幾個人擠成一團指指點點,彼此都很害羞,只敢遠觀,不敢近褻,有一次近距離看她,兩頰一大片雀斑,像美國村姑,雖然可愛,也有點小幻滅。
如果有什麼美好的事物,那就是校園裡花木特別多,每個季節有看不完的花,只有大自然景物恰到好處,花恰恰好,月也恰恰好,夢呢,無色無香無臭。我們還不懂得如何打開自己的心,如何付出,卻渴求瘋狂地被愛,然而誰會愛一個月半女子?或是大竹竿?青春的不完整性,是生命的一個過程,沒必要特別誇大或美化。那些謳歌青春的文字,大多是遠距離觀賞的美感或追憶。青春並不特別值得留戀,耽溺青春少女之美的中老年男子,最病態不過,他們真懂得什麼叫青春少女嗎?他們迷戀的是海報美女或夢中仙女?同學上了大學,過了二十,開始談戀愛,一個個變漂亮,且胖瘦適中,我也漸漸符合一般人的標準,瘦一點,美一點,然青春已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有些人還未畢業就訂婚了。青春到底有沒有來過?什麼時候來?難以察覺,這也是為什麼青春如此蒼白,蒼白即無物。
歌劇魅影
◎紀大偉
〈 眼球全球化〉這個專欄談論視覺文化的全球化,怎能不關心《歌劇魅影》呢?幾十年來,《歌劇魅影》的音樂/音樂劇獲得幾乎全球性的勝利。它的魅,大部分來自它的影──而不只是音。
當然, 沒有安德魯. 洛伊.韋伯的音樂,《魅影》不會膾炙人口至此。然而,就算沒有韋伯的音樂,《魅影》的原著小說也一再改拍為電影:在美國就可以找到至少近十種不同版本的《魅影》電影,其中包括1920年代的老片,以及張國榮主演的版本(舊上海也另拍過黑白版)。
除了韋伯配樂的那部電影之外,其他《魅影》電影根本與韋伯沒有關係。也就是說,這些版本的動力來源,在於原著小說。
原著小說是不是文學精品,見仁見智。但原著小說的一大貢獻卻不可否認:它見證了一百年前歐洲人對於「視覺文化」的執迷。一百年前,歐洲發生什麼事?照相術誕生,電影萌發,萬國博覽會興盛。老百姓的主要娛樂,就是追求「目炫」的神祕經驗,享受大開「眼界」的樂趣──於是,去照相,看電影,去看博覽會展示的異國文化等等視覺活動,就成為現代化生活的甜點。
貫穿《魅影》原著小說的主題,就是「奇觀」和「真相」的辨證(奇觀和真相,又都和視覺有關):掀開歌劇院的奇觀外貌,就是陰森森的奇觀地下湖。掀開歌劇院之鬼的面具,就是血肉模糊的真臉。劇院舉辦化妝舞會,人人戴上假面。劇院裡肖似武俠小說的機關,就是鏡子:鏡子並非映現真相,反而讓人看見另類世界──鬼住在鏡子裡,穿過鏡子就進入禁區。很多通俗文學都以善/惡對立做為主軸(好人vs.壞人),而此書則不:它倚賴的對立並非善/惡(書中「沒有」壞人),而在於真/假(以及相關的美/醜)。
在各種呈現《魅影》的版本之中,我覺得舞台表演最值得看。在電影中呈現地下湖以及下墜的水晶燈,根本不值得稱奇,因為電影本來就以奇觀取勝;但是在限制重重的舞台上呈現地下湖,在觀眾頭上裝置戲劇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水晶燈,才回歸魅影本色。搶看《魅影》歌舞劇的粉絲是為了舞台魅影而出動,而不見得是為了歌聲。 ●
中產階級的罪惡感
◎成英姝
一個人想過常軌以外的生活, 必須要有那個本錢,一則靠本事,一則靠運氣。
前兩天我問朋友A會不會去看克里夫.歐文主演的電影《玩火》,A很不屑地說外遇這種題材值得一窩蜂地拍嗎? 票房成績不錯的《偷情》也是克里夫. 歐文演的,很難不如此想。至於另外還有部新片,伍迪.艾倫的《愛情決勝點》,以這兩片的前半部劇情來看,A說的也沒錯。老實說,看這兩片前面鋪陳外遇的劇情,真是悶到令人坐立難安,但電影製片公司又不是白痴,誰會真的以為有那麼多婆婆媽媽的人想看只是一部講婚外情的故事?結果這兩片真正的主題,都不是外遇。
《愛》片描寫一個從愛爾蘭來的窮小子娶了企業家的女兒,眼看可以因此飛黃騰達,偏偏搞上一個混不開的女演員,解決這個女人的問題,他用的方法很出人意料,結局也很出人意料。(不透露結局比較道德吧!)《玩》片則是講一個有沉重的家庭負擔的男人,愛上火車上巧遇的女人,結果惹上強盜的暴力威脅,這個男人反擊的方法,也很出人意料。為什麼兩片都發生這類的情節,其實很簡單,在都會求生存的白領階級,過著安逸生活的知識份子,儘管中產階級也有中產階級生存的掙扎和困境,但大體上是被一套穩當的遊戲規則所保護著,會讓這種男人跨足到原本沒有交集的另一種遊戲規則的異次元,最簡單的發生方法,就是來自另一個女人。
這個部分我倒不關心(女人的部分),我有興趣的是一個人一開始使壞,常常沒想到後來要壞到相當的程度才能收拾。使壞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門技藝,技藝如果不是靠琢磨,就得靠運氣了。《愛》片的主題就是運氣,男主角的運氣好到戲院裡全場大笑(這就很伍迪.艾倫風了)。要緊的是,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出於不得已他們被迫要用非常的、不屬於他們原來那個安穩明亮小世界的手段解除噩夢以後,可不能吃牢飯或者改行當流氓、販毒之類的,他們必須可以回到他們原來那個安穩的明亮小世界,繼續原有的生活方式。難處在這裡。因此看完這兩部片,我不禁歎口氣,罪惡感這種東西啊,真是超中產階級的。 ●
理工學院的文人
◎新井一二三
我去年開始在大學教漢語。
明治大學是「東京六大學」之一,相當於美國的常春藤名校,歷史超過120年。
我任職的理工學院乃60年前加添的,位於東京西南邊的川崎市生田,綠油油的多摩丘陵上。眾多的畢業生當中,如今最有名的大概是電影界名導演北野武了。
雖說是理科院校,明大生田校園卻出過不少著名文人。他們是教外語或人文科目的老師們。光是純文學的芥川獎得主就有三位。戴著仿古圓形眼鏡,目前負責理工學院法語教學的堀江敏幸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散文體小說滿受讀者的歡迎。看課程簡介,堀江教授的第二年級班用的教材竟是法國菜譜;跟名作家學名菜做法,真是奢侈無比了!推介我去生田教書的管啟次郎教授則是精通英法西葡多種語言的名翻譯家,有關西印度群島Creole文化的評論集得到行家的高度讚揚。才四十多歲頭髮已經幾乎全白的管教授,看起來像個道家仙人,服裝卻相當美國化,愛穿牛仔褲和黃色的Converse皮革球鞋。夏天更著夏威夷Aloha襯衫,彈著優克李林琴(Ukulele)、哼著南太平洋歌曲進出教室,讓理科學生們目瞪口呆、大開眼界。
還有精通多種斯拉夫語言的奇才黑田龍之助副教授。他原先是NHK電視台俄語會話節目的主持人,後來到生田教世界英語。在黑田老師的課上,學生們練習聆聽帶有韓國、新加坡、印度、波蘭等各種口音的英語,為的是提高跟各國人士用英語交談溝通的能力。多麼現實的教學方式!這種課,在我大學時代是沒有的。如果有,我後來住多倫多等移民城市時候的生活品質不知會改善多少。當時,我每次去印度人開的披薩店都無法順利溝通,買張披薩好費力氣的。
這些才子屬於理工學院綜合文化教室,猶如理科大海裡的文科小島。他們從打扮、髮型到措辭,全跟理科同事們截然不一樣。
對數學、物理、化學、建築等專業的男女學生來說,跟博學多才的文人學外國的語言、文化、歷史、風俗,無疑是別有風味的經驗。至於才子們為什麼不在文學院研究教學,那恐怕各有各的故事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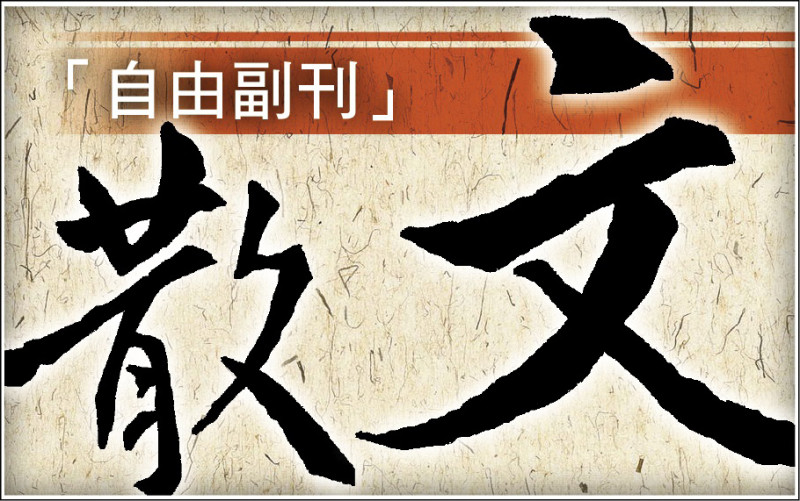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