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三獎】舊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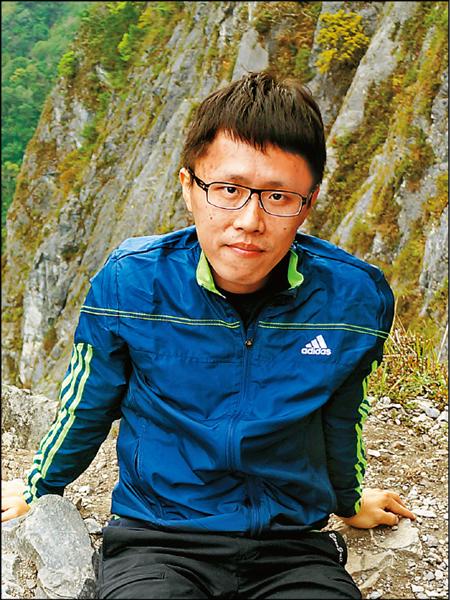 陳宗暉
陳宗暉
作者簡介:
陳宗暉,1983年生。東華大學中文系(現為華文文學系)碩士班畢業。詩作曾獲花蓮文學獎、時報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一路上願意停下來等我、載我一程的人。當初是要寫一首詩還是一篇散文,我已經忘了,結果就寫成了目前這個樣子。
★★★
舊傷 ◎陳宗暉
那時的夏天,不管什麼樣的終點,只要一直走,就可以抵達。
有些地方只有徒步才能抵達。必須
一直走。一直婉拒善心便車,避開砂石車,一直走,
直到舊傷復發。慢慢長路,長路漫漫,海風咀嚼砂石。
遠遠跋涉而來一輛彩繪巴士,遠遠跋涉而來,一艘拼板舟陸上行舟。
我想起沿途公車站牌總是生鏽模糊。
司機樂意打撈路邊擱淺的我,讓我坐進副駕駛座,「觀光客的座位!」他說。
.
成群的羊都知道要讓路給成群的機車。
這公車的二十個空位有二十種以上的等待。二十封以上的家書,沒有人在。
陸上行舟,我們在島嶼北部的強風裡沿途借過,終於進入部落。
涼台裡的老人開始騷動。車來了,像是兌現遙遠的承諾。
短褲老人駝背健步,戴帽的長裙老人懷抱包袱像是懷抱熟睡的嬰兒。
我們互不相識但仍點頭示意。我先就坐,但我是客人。
我在行進的客廳讓舊傷休息。他們繼續暢談,我繼續聽不懂他們又好像聽懂。
司機替我翻譯:老人在家坐不住,生病也要上山。
車裡音碟轉動阿美族的輕快歌謠,老人跟著哼。哼完再唱自己悠緩的達悟歌。
我看見林投樹果實飽滿誠懇,老人想起從前借用林投樹的身體曬飛魚捆小米。
.
車在監獄舊址暫停。有人在裡面種菜種水芋,有人嘗試讓珠光鳳蝶復育。
東清今晚有沒有夜市?「野銀新社區」的燒烤攤已經提前熱鬧起來,
車速慢下來,下一站是「野銀舊部落」,老人可以假裝回到少年時。
「永興農莊」的遺址現在仍有種植,日落而息時,有人燈火通明夜探角鴞。
陸上行舟,在山高路窄的後山繼續顛簸不息。海浪不打算讓舟暫停。
龍頭岩不是什麼龍,老人用母語說,那就只是沒有規則坑坑洞洞的石頭,
底下有大魚。我們的陸上行舟也是一路坑坑洞洞,
底下有撞見龍頭的抹香鯨正在下潛。小蘭嶼再過去那邊遠遠有颱風,
我們的拼板公車疑似遭遇長浪。在野生的海風裡,沒有鋼鐵可以繼續堅硬。
環島公路只有一段永保平坦,在此可以加速,生鏽的罐頭工廠無人上下車。
路邊有人整裝待發下海浮潛。路邊有抗議標語被白漆遮成啞巴。
.
路邊有偉人的半身銅像背對大海,終日看著從前的指揮部變成資源回收場。
從前從前種地瓜的土地,現在改種民宿。「民宿今年收成好嗎?」
層層抵達衛生所的時候,可能只有我一人暈船。
公車在此稍候。有人要去看病,有人要去郵局領津貼,慎重如進入森林。
準備再上路時,車外有人急拍車窗,候車亭失物招領:「誰的藥袋忘了拿?」
「丟在那裡就好了!」剛上車的失主坦承故意留下。「垃圾自己帶回家!」
想痊癒只能順其自然。有些病只能順其自然。
.
剩下的乘客都在農會超市下車。蘭嶼公車的每個站牌都是生活的入口。
我看見奇岩,他們看見漁場。有人攜帶自家農產漁獲在超市門口擺攤,
司機也跟著下車買了一袋蘭嶼花生,「最後一站,祝你鵬程萬里,音容宛在!
這樣下次我還會記得你。」我揮手道別。有些風景只有下次才能看見。
.
頂著一樹一樹的蟬聲繼續走,側背海浪繼續走,一層一層過濾我。
徒步是心的顛簸,徒步比較容易感傷,感到血肉般的受傷,感到骨折,
所有的傷口音容宛在,浸泡在過期的海水。慢性發炎是火山口,疼痛是海溝,
是廢棄國宅的窗,是簡易碼頭的裂縫,是野溪流過水泥河道,是復建堤防,
是危險的安全。這個島嶼有時憤怒是因為舊傷復發。是帶狀疱疹。
我回到島嶼北邊的「五孔洞」,他們禁忌的洞穴是我隨地休憩的地方,
岩壁裡有凝固的禱辭,在這個沒有翻譯的海蝕洞裡,可以聽見頭頂有海浪:
像大海一樣柔軟,像大海一樣堅強。
我想起老人晃動的表情,有人是沒有父親的兒子,有人是沒有兒子的父親。
我是森林與大海的孤兒。我在他們受傷的地方徒步,腳底有心臟,
愈踩愈感到衰竭,愈踩愈感到抱歉。
【評審意見】
豹眼踏查
◎蘇紹連
詩寫邊境島嶼之傷。本詩是採取「豹眼」似的地面攝影視角,而非「鷹眼」似的空中攝影視角。「鷹眼」盤旋鳥瞰大景之美,震撼視覺,而「豹眼」近距離踏查,穿梭文明的遮掩,體察住民的生活,掠取時空記憶的細節,無疑是獲得了更為真確的現實感。一直走的徒步旅行,在舊傷復發而坐進公車副駕駛後才開始,敘寫跌宕多姿,那是一輛在地景空間「移動的客廳」,也是住民聚集的生活載體,一路上,帶出地景及建物的變貌記憶。作者在「客廳」內養傷,進出的住民灑脫談話、唱歌,司機幫忙翻譯,兩種語言交錯混搭,有趣而幽默的語感,誤用華語而不忌諱。作者所見的住民,有人是無父,有人是無子,作者帶著個人的傷徒步,卻踩在他們受傷的心臟,暗喻島嶼的生命力快沒了。此詩深刻婉轉,更能在結尾對蘭嶼致上無比的歉意和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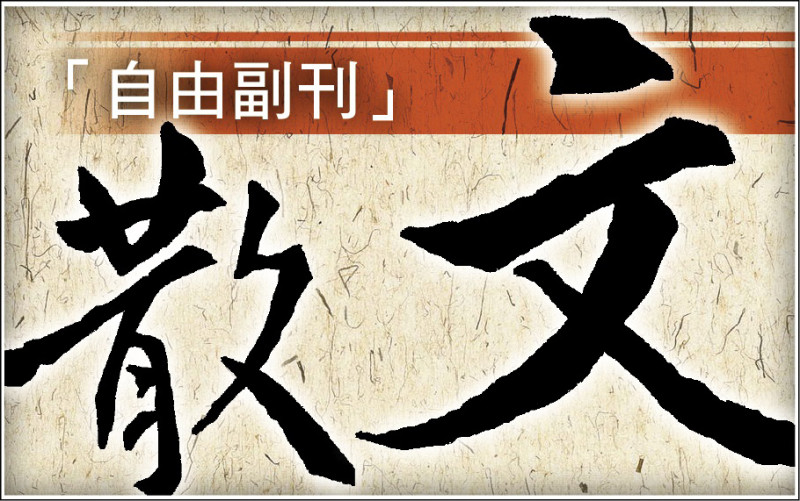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