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向陽/歲月的爪痕
 圖◎焯両黃
圖◎焯両黃
◎向陽 圖◎焯両黃
在民雄,我看到歲月的爪痕,攀爬在古建築的牆上,訴說歷史的滄桑。
在國家廣播文物館,館外兩排大王椰子樹如衛兵一般矗立在晴陽之下,一旁的鐵塔從高處俯視著這棟建築於1940年的老電台館舍,放眼望去,周邊一片濃綠,把自然和古蹟融於一體。鐵塔有兩座,巍然聳立於天際,高約二零六公尺,估計有七十幾層樓高,因為成為民雄的地標,是民雄人共同的家園象徵與記憶圖像。歲月走過這棟館舍,已有七十多個春秋,在它的建築裡外,標記著歷史的腳跡。
國家廣播文物館起建於日治時期,最早以「民雄放送所」之名啟用。那是日本發動對華戰爭的時代,負有日本殖民地國宣揚政績、遞送戰情的任務,因此電波傳送範圍遠及東南亞和中國江蘇省及南京等地區;大戰結束後,一切設備由政府移給中國廣播公司接收管理,改名為「台灣廣播電台民雄播送機室」;1980年移給國防部,成為「中央廣播電台第一發射基地」,直到1998年中央廣播電台改制為國家電台,這才褪去軍事和政治作戰的面紗,而後轉型為今天的國家廣播文物館。
站在這棟建築之前,我彷彿聽到日治末期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仍在持續,播報原以歇斯底里的聲音放送日軍在中國、在南洋的戰績,乃至於日本天皇宣布向盟軍投降的顫抖的聲音;我也彷彿聽到,戒嚴年代通過這裡播放出去對大陸心戰喊話的高亢播音,宣揚著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政績和「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話語──在這曾經播送兩個國家機器的神話的戰事電台之前,已經過去的戰爭和政治神話,如今俱已偃息在徐徐吹來的嘉南平原的風中,供人憑弔。
只留下歷史和建築,在館內駐足。廣播文物館一樓主要是辦公空間和簡報室,二樓則是主題展館,1940年代的原始建築風貌仍保留至今,日治時期由日本NEC電器製造公司設計的龐大發射機具,以灰沉之姿迎接七十年後前來參觀的訪客。大小不等的真空管,在從窗外撒進的陽光中閃著銀光,似乎仍在誇炫二次大戰期間日軍的戰力、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的政績;角落則是「中美合作」時期留下來散熱的大風扇、播音室。摻雜著軍事、政治和由國家機器控制的廣播史,就在這裡一頁頁地展開。歷史以縮影之姿,和這座文物館共存;而不同年代的聲音,或高亢、或柔美、或急促、或平和,則在二樓的堂廡之間持續流竄。
這曾是民雄最最威嚴、神祕與難以靠近的所在,在歲月的汰洗之下,如今成為開放的空間,古老的建築儘管標誌著戰爭和戒嚴的痕跡,如今洗去一切,打開門窗,迎接陽光的撒入,竟也有一種歷史遺跡的平靜之美。
相較於國家廣播文物館的歷史遺跡,在民雄,我也看到一棟老屋的蒼涼。那是被訛傳為「台灣三大鬼屋之首」的劉家古厝。
劉家古厝站在荒煙蔓草之中,整棟建築爬滿樹藤,即使是在白天,日正當中,仍然散布著某種難以言說的鬼魅氛圍。站在古厝之前,很難想像這棟三層樓半的古厝曾經也是風華絕美的屋舍。比對它初見之時的照片,以中西合璧的巴洛克式風格建成,它的主體結構宏偉華麗,門框、窗罩則以閩南建築常見的傳統圖案鑲嵌,融合了洋樓和閩南建築的雙重風格,襯以綠草如茵的前庭,典雅而溫馨。
然而,歲月卻以它的爪痕,讓這座曾是民雄首富之家的洋樓成為如今樹藤纏身的「鬼屋」,在雜草叢中,展示一個家族的沒落和不受疼愛的建築的蒼涼。
資料上說,劉家古厝乃是被稱為「打貓員外」的「阿裕舍」(劉容如)於日治時期(1929年)所建,乃是當時台灣的豪宅之一。劉容如出生於地主之家,畢業於「打貓公學校」,除了接受日本教育之外,也跟從鄉內宿儒何振猷研讀漢文,精通經史、詩詞、國畫、書法,是個典型的讀書人。後來在打貓街開設「三泰合資會杜」,經銷稻穀、肥料等民生用品,因此聚累財富。其後被日本當局派為溪口庄長,任內也受鄉民愛戴。他在人生巔峰時期起造洋樓,應該也有「三代同堂,共享天倫」的寄望吧。
滄海桑田。戰後劉容如移居到民雄市街,1949年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據說曾經借住於這棟豪宅之內,又據說有士兵因為思鄉而於宅內自殺,終於使得劉家廢棄此宅,日久草深,豪宅荒廢,樹藤蔓生,因此被訛為「鬼屋」;另有一說,則稱是因為劉家有婢女投井自殺,因成廢宅。
昔為豪樓,今成廢宅。這大概也是歲月荒涼的常見事吧。如今的劉家古厝,因為「鬼屋」傳說,已成為外來遊客必欲造訪之處。站在當年碧草如茵的前庭,看這棟昔日豪宅為樹藤纏繞、門窗盡破,屋內擺設凌亂的模樣,當年劉家的華彩、榮光,都已遁入藤蔓攀爬的陰影之下。鬼魅傳說如穿過堂廡的涼風,即使日照之處,仍有寒涼之感。
在民雄,我看到兩種歷史。國家廣播文物館,從軍事與政治用途的電台變身為供公眾接近台灣歷史的文物館舍,顯現台灣廣播史的曲折發展與教訓;劉家古宅,則從地方首富豪宅淪為荒煙蔓草叢中的「鬼屋」,昭示某種「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民間哲理。這兩棟古老建築的際遇,一如人間諸事,起落興衰之間,都殘留著歲月的爪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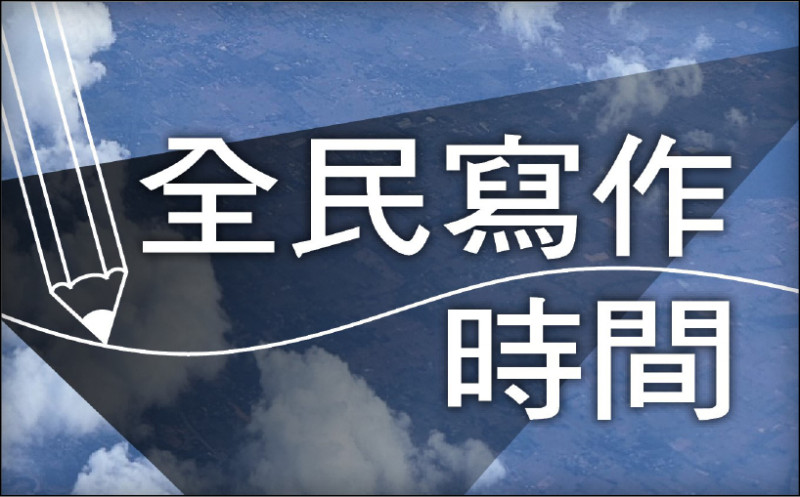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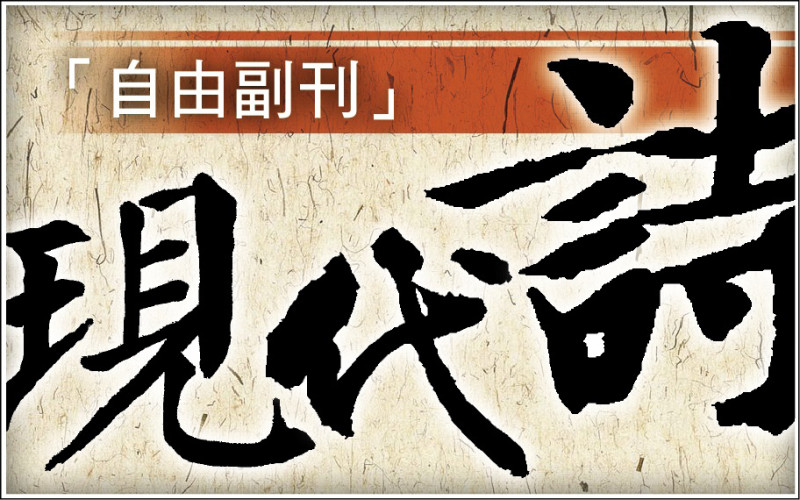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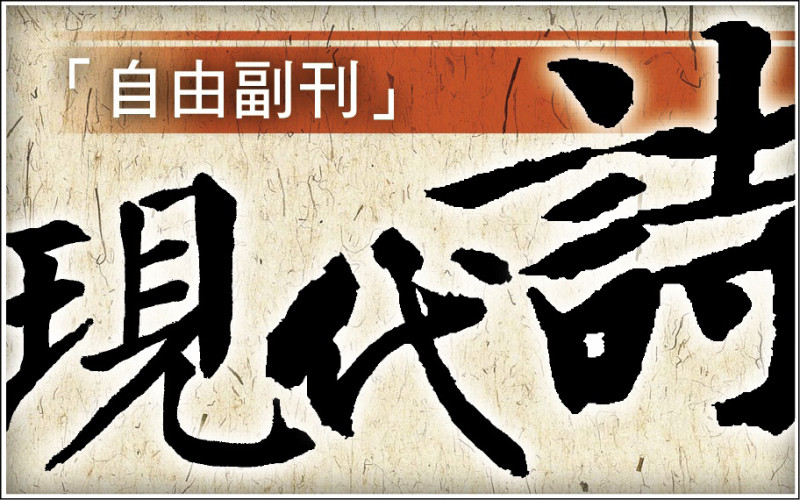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