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書與人】島嶼的未來盛夏 - 林俊頴談《猛暑》
 作家林俊頴。
(潘少棠╱攝影)
作家林俊頴。
(潘少棠╱攝影)
專訪◎蕭鈞毅
 其新作《猛暑》。
其新作《猛暑》。
《猛暑》從何而來?作者這麼說:「我對所有一切很不耐煩,就這麼一句話。」
林俊頴(1960-)總是低調,宣傳不多,公開談論也少;似乎比起身為「小說家」這份特殊的職志,他更享受於寫小說的過程。如《大暑》、《玫瑰阿修羅》、《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某某人的夢》等作,字有料峭、文又蒸溽,不只兩種極端溫度在他的小說中夾纏,連同不忍或捨離,都是小說裡矛盾的內心。意圖從這些矛盾擘畫出的小說景觀,為的正是面目逐漸模糊的人世浮生:誰愛誰、誰心恨誰、誰又認同誰,只要是和「人」有關的便沒有乾淨俐落的可能,不只批判,更有溫柔──這是我們身處的現世,是《猛暑》這本小說嘗試與讀者對質的立場。
讀完《猛暑》,我非常訝異小說家以「不耐煩」做為《猛暑》的其中一個起點,因為小說不似字面,《猛暑》反而是愈到高潮,愈顯冷靜:「像是游泳愈深,壓力愈沉,你不得不因此冷靜下來,慢下來。」到了小說中段之後,本該是暑下生機盎然的光景,全變成是遭到過度曝曬、近乎風化的斷牆殘垣。
這是「不耐煩」所造就的小說景觀嗎──又,小說家的不耐煩到底因何而來?小說家這麼回答:「社會。」
極端的未來,畸形的自由
以不久後的未來為題,《猛暑》彼時,世代政治、居住正義、所得不均、環境議題等諸種難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因新種科技而選擇沉眠的主角隔了二十年再度醒來,「我島」成了被各國角力後託管的真空地帶,早已人去樓空,有錢的都走了,留下的是自己的選擇、以及無從選擇的人們。
會有這樣的設計,小說家這麼說:「不只從冷戰,長久以來,這個國家、這個島的命運一直『被管』,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要管我們了,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萬一不是呢?」小說因此憑藉著虛構裝置,平地造樓,留下一個舉目無人、鬼影幢幢的未來。
到了那時,「我島」的生活倒帶回以物易物的生活,人人步伐緩慢、心則少憂,感受性隨著逐漸濃厚的植被愈發強烈;本來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大滅絕,林俊頴構造出的光景竟又有了些許烏托邦的況味──然而,事情沒有那麼輕易,《猛暑》的「猛」字既有生機,又有殘忍的意義:暴死的長者或老人的滅絕暗喻了世代政治的極端,在未來的「我島」,「老」不再是生命中的階段,它成了一個咒詛般的字眼。《猛暑》的政治寓言因此具體地浮現:「我自己有個很沉重的感覺,這樣子吵了十幾二十年,我覺得普遍大家心都很浮躁。不只浮躁,大家都變得很虛弱。這些年來我們的整個社會的氛圍是很緊張、很奇怪的……我在寫的時候,真的覺得兩方面很欠缺一個彼此可以心平氣和、理性對話的管道。」
多少出自無奈,小說家即使強調溝通,仍然不免在小說裡選擇「旁觀」,而以「惡謔」的角度將現有的政治議題推向極端。年老是原罪,年少者絕育,親屬關係表上的稱謂隨著惡劣的經濟環境一一消失,「家族的最後一個人」已是小說裡的常態,又或者是,為成良好公民須定時接受忠誠檢查,以享有國民福利福祉。諸如此類,小說的政治寓言因此更形尖銳:當「我島」因此而成真空三不管之地帶,無論認同為何、為人善惡,最後能離開的都是有資本者──選擇留下或被迫留下的,則將共同置身於歷史的真空,共享同一種畸形的「自由」。
自由難題與孤獨處境
熟悉林俊頴的讀者,對他的筆法絕不陌生。在《猛暑》裡寫的台灣自然,優雅依舊,幾乎是自外於一切。帶上了「崇高」(Sublime)意義的「自然」,於《猛暑》敘事者的視角,又是敬畏,又有投射,還有孤獨:無論「我島」的政治、人世如何變異,自然仍在其中茁壯生長,並適時以它們的茂盛映襯對人間的殘忍──那些在最後留下來的,不過就是意義漸被抽離的「活著」而已。
「人有必要活得這麼久嗎?活得這麼老嗎?……該讓他去就讓他去,多餘維生方式,就是在浪費家屬的情感、浪費所有的醫療資源。人到底可不可以決定自己老年之後的階段,可不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這件事卻又沒那麼簡單。」這段想法,是提示《猛暑》思考「孤獨」的關鍵,人世走上一趟,結局時不過就圖個「尊嚴」。
小說裡有這段話:「某人的意見尤佳,一到六十五歲,每個人發一顆劇毒藥丸。死亡是唯一必須長期嚴肅思考的,一如實習醫師,一如祕教法師,隨身攜帶一顆頭顱骨。」簡直孤獨到心底,也是「自由」這個概念的終極理想;這段話將人世上的熙熙攘攘,「我島」被擠壓在歷史關係與國際博弈下的居民未來,所有盤根錯節的纏繞全化約成了「可不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這樣一種個人化的,「自由」的難題。
冷靜的猛暑
儘管自稱是旁觀與不耐,林俊頴仍清楚明白自己也在「裡面」。1960年代出生的他「完全能理解年輕世代的憤怒。現在的小孩子是真的很辛苦,因為你今天無論再怎麼努力,你明天不見得可以得到相應的收穫。」亦直言「每一個世代都有他們的幸運,這是一定的。」而他最掛心的,是夾在兩造中間的「情緒」,讓雙方尋找解決方法的可能性,因此被搓消成細屑。
書裡有一句,轉引自香港小說家黃碧雲,原出自於Régis Debray的名言:「我們不與我們的時代同代。」可視為林俊頴思索「世代政治」的態度。時間感分歧,活著的目標相反,在「猛暑」下被曝曬的人們皆難倖免,退無可退。
畢竟,身處同一島上,共享同一段歷史,任何一個人談起「命運」這個沉重的詞,便難有樂觀的餘裕──時間在走,「我島」卻疲憊不堪──悲觀便由此開展另一條名為《猛暑》的未來,在那裡,有一個小說家忡忡憂心,卻又勉力從容的足跡。
或許源於憂慮──於書序,王德威言:「我們能容忍一本砲口向內的惡托邦麼?」王教授的顧慮可以理解,我對此反而樂觀;「惡托邦」惡則惡矣,仍有小說家世故的溫柔,《猛暑》批判之外留下的餘地,更像是對不同世代讀者的一份邀請:這裡提供了一種想像,無論站在座標的何方,都不妨先停下來,喘口氣,聽一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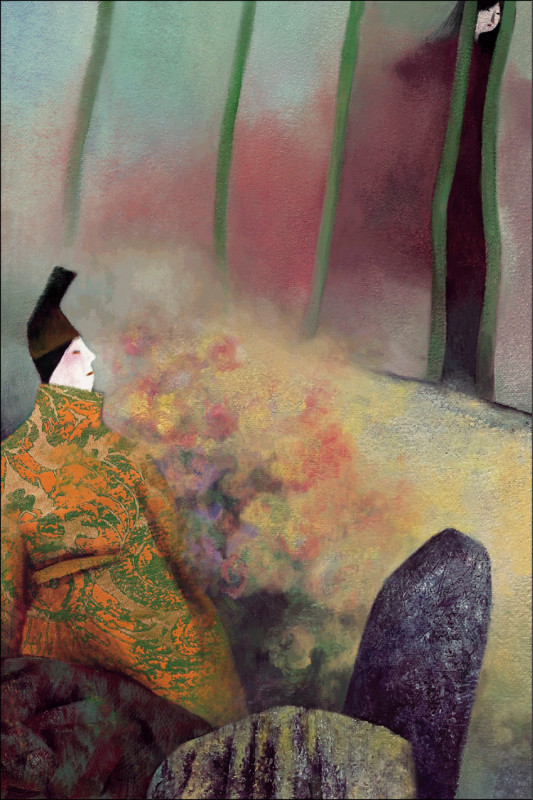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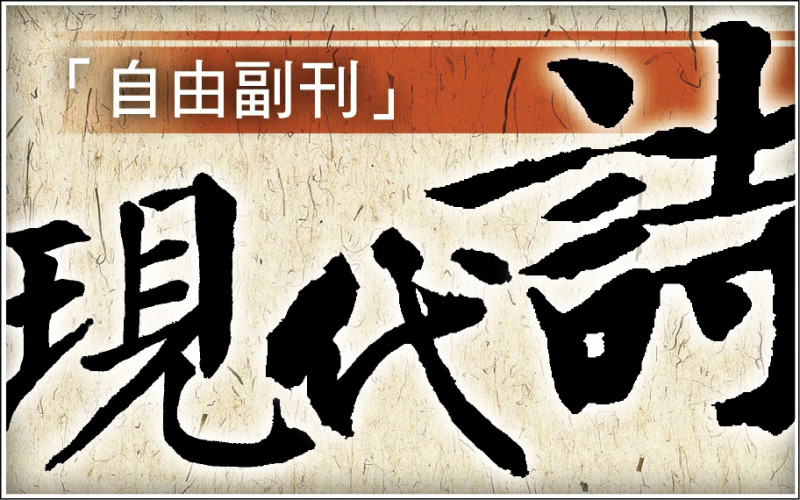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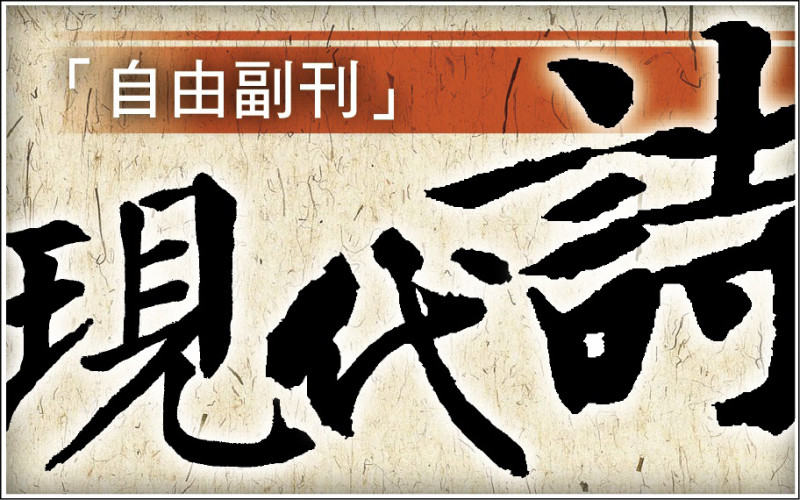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