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張讓/看不見的威尼斯
文.攝影◎張讓
 金黃石牆,高處兩條晾衣繩,浴在陽光中發亮。這動人完全不是出於設計。
金黃石牆,高處兩條晾衣繩,浴在陽光中發亮。這動人完全不是出於設計。
.
 石建築,水道相連,貢多拉舟來去穿行。水城的感覺。
石建築,水道相連,貢多拉舟來去穿行。水城的感覺。
 在小巷深處角落,嵌在古老石牆中,靛藍窄門似乎帶著神祕。
在小巷深處角落,嵌在古老石牆中,靛藍窄門似乎帶著神祕。
1
 兩個貢多拉舟子坐在橋欄上休息,黑白橫條運動衫和黑色鐵欄花樣成有趣對比。
兩個貢多拉舟子坐在橋欄上休息,黑白橫條運動衫和黑色鐵欄花樣成有趣對比。
來也好,不來也好,城市總在那裡,也總是看不見。尤其是水城威尼斯。
威尼斯一直在下沉,除非工程科技能夠挽救,最後會沉沒不見。
2
2005年,在計畫許久以後我們來到義大利。頭一站威尼斯,然後南下佛羅倫斯。
8月底,旅遊旺季,從渡船上遠遠可見驚人景象:岸上壓壓一片蠕動的人頭!
夏季不宜到威尼斯,寒季水城更美,我們知道。但為了牽就友箏上學,只能在暑假來。
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裡,勞倫斯對觀光客有一段刻薄描述:「他們要的是娛樂,簡直就像要從石頭裡榨出血來。可憐的山!可憐的風景!不斷受到壓榨,只為了給人一些刺激,一些快感。」
一下渡船我們便成為那群觀光蝗蟲的一部分,前推後擁身不由己,朝聖馬克廣場移動。幸而沒走多遠遇見一條直交小巷,我們毫不考慮拐進去。人群消失,只見一條窄小曲折石巷。我們暗自歡呼:現在可以開始玩了。也就是,開始迷路。
3
不迷路是不可能的。
在義大利十天裡不斷迷路。我們先飛到米蘭機場,租了車直奔水城。近三小時後路標出現了威尼斯, 我們遵照指示卻老在打轉(義大利路標有時像經咒密密麻麻),水城就在眼前卻進不去,在外圍繞了幾圈才摸對路,因而見識了水城邊上的工廠和核電廠,以及現代公寓住宅區(和美國城郊差不多)。後來進佛羅倫斯,也是迷得團團轉。在美國旅行從沒這樣迷路的。
威尼斯到處是人。不像碼頭上那麼可怕,但感覺置身鬧市。在美國境內旅行,我們總挑人煙稀少的地方,譬如高山或是沙漠,經常只有我們三人。這樣人群簇擁,只覺壓迫想逃。
隨意亂走,非不得已才參考地圖。有時B會面對市區詳圖說禪話:「我們好像不在我們所在的地方。」看路牌我們明明在A,地圖卻說在B。難道同一街名兩處出現?最後乾脆收了地圖,憑印象摸索。彎彎繞繞,認出了走過的街道、上過的橋、經過的教堂,甚至又再撞見先前遇見過的襤褸遊民和黑人攤販。簷角那頭雕塑生動欲飛的大鳥,布店櫥窗裡那些疋細緻的花布,多虧迷路得以再欣賞幾眼。
累了便在台階邊坐下,喝水,看人。看來看去都是像我們的觀光客,可笑到這裡除了貢多拉舟子和板著臉孔的餐館侍者,沒見一個義大利人。
常買了冰淇淋邊走邊吃,因此吃了不少冰淇淋。榛實口味最香,後來單買這一味。
4
迷路,加上蓄意挑小路,結果走了很多窄巷,看見威尼斯比較隱私的部分。像破敗的石牆磚牆、生鏽的鐵窗、朽爛的木柱木門,還有牆角隨處可見的垃圾、惡臭的狗糞――旅遊指南裡沒有的。不只眼睛旅行,鼻子也在旅行。
看了不少寫威尼斯的書,最有趣的應屬歌德的《義大利日子》。他總以地質學和地理學家的眼光來看旅遊景物,保持客觀清晰,避免掉進浪漫唯美。在威尼斯兩週沒雇嚮導,一個人隨意遊逛。走過一條又一條窄巷,有的窄到兩肘撐開便觸到牆。有的街道骯髒讓他不解,開始在腹中草擬衛生規章,然後笑自己多管閒事。
卡爾維諾小說《看不見的城市》,說的就是威尼斯,它是歷史之城、文化之城、商業之城、宗教之城、欲望之城、腐朽之城。實際上,威尼斯也是情人之城、詩人之城、小說家之城、畫家之城、夢幻之城。
經常B和友箏走遠不見了,我單人落後。
佇足巷子深處看一扇來自《天方夜譚》的靛藍窄門。
遙望暗巷前方小橋台階上坐在陽光裡的兩個人。
在窄巷交口欣賞牆上如抽象畫的各色塗鴉和海報。
以及,看到處的古老石建築。
好似我來自速成塑膠世界,從沒見過金石土木的天然材質,只能像劉姥姥大開眼界,樣樣都覺新奇。我走得慢,前後左右上下觀望,腦袋幾乎要像貓頭鷹做兩百七十度旋轉。拿手摸那清涼剝蝕的古老石牆,抬頭為歪斜到幾幾乎就要掉落卻仍危危懸在二樓的銹蝕鐵窗欄而驚訝。
但願能有大量時間,加上一隻絕好相機,讓我能在最恰當的光線和角度下從容攝取那些形狀銷蝕色彩淡去的石和磚,表現出牆面無數的疤痕坑洞、岩石本身吞吐空氣水氣的「毛孔」、腐朽木樁木門上峽谷似的深溝。無論如何,還是拿了數位相機照個不停,此外買幾本攝影集補充。
5
我所攝的水城腐朽破敗,美人遲暮加窮極潦倒,陰森如廢園鬼屋,像出自《聊齋》,不像詹姆斯、拉斯金及無數文人筆下風華絕代的威尼斯。當然我也有許多典型的「明信片威尼斯」:褪色憔悴韻味不減的拜占庭風格建築、運河上的小拱橋、形如弦月的貢多拉舟、蕩漾的水中倒影……
威尼斯人的色感絕頂,難以想像有人能把橘紅和粉紅擺在一起而不撞色不庸俗,能把對比和調和色用得那樣恰到好處。話說回來,很多非洲種族運用色彩和圖案的本事更狂野驚人。
最吸引我的是橫跨建築間一條條掛滿衣服上下輝映的晾衣繩――這可是真的,最素樸實在的生活風味,不是掛出來給遊客看的。那些衣服懸在陽光下發亮,我不由看呆了。
走不了幾步便可見這樣的晾衣繩,有的沿牆就掛在兩窗之間。不禁好奇:這些繩子不比竹竿,是怎麼拉出去的,而且能拉得那樣直?衣服又是怎麼掛上的?
照了許多晾衣繩,見到就照,從威尼斯照到聖.吉米尼亞諾。
6
後來在佛羅倫斯的烏非茲(Ufizi)美術館裡見到卡納勒托(Canaletto)畫威尼斯,很喜歡,回來後到圖書館找他的畫冊來看,見到一些畫的背景裡他甚至詳細畫了晾衣繩(沒在別的畫裡見過),更喜歡了。
卡納勒托是18世紀的威尼斯畫家,擅畫宏偉建築景觀。當時的名英國藝評家拉斯金認為他只是個畫匠,光會抄襲景物,而且畫法死板,貶得極低。但後世評家認為拉斯金所以貶卡納勒托,為的是捧本國畫家特納。特納的絕活是水景,筆下的天光水色燦爛迷離,比印象派更印象。把特納和卡納勒托放在一起,很容易便看得出拉斯金的偏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也貶卡納勒托,批評他篡改實景讓人頭暈。只有美國畫家惠斯勒欣賞他,把他和西班牙畫家法拉奎斯(Velasquez)並論。
7
一天迷路很久,頂著炎陽彎來繞去,終於走到了猶太區(Ghetto)。
Ghetto這字現在用來通稱貧民窟,其實最初指的是16到18世紀時期,威尼斯劃給猶太人居住的隔離區。當年威尼斯除了限制猶太人只能在三個猶太區居住外,並設種種職業和行動上的限制。不過比起當時大部分歐洲對猶太人極度的迫害,威尼斯人雖然也不免歧視,起碼劃地收容。
我們到的這猶太區在一座小島上,以三橋相連。空曠的廣場上幾棵樹,散布了一些在威尼斯各處難得一見的石凳。我們欣然坐下,環視四周素樸的樓房,研究對面牆上一系列的淺浮雕。
已到黃昏,斜陽拉過廣場,沒那麼熱了。角上一間窄小的猶太教堂裡,白襯衫長黑外套黑褲黑帽黑鬍鬚的學生正搖頭晃腦誦習猶太經書。附近拱橋邊,幾名男警女警聚在一起聊天。奇怪威尼斯鬧區幾乎不見警察,偏偏這裡特別多。廣場半在涼蔭裡,我們閒坐喝水,遊目觀看這一猶太生活切片。一個學生從猶太教堂出來,典型白衫黑衣黑帽黑鬍鬚,一手拿了本書,大步穿過廣場到對面大樓裡去。四樓一戶人家的窗子開著,一位老人倚在窗上看廣場上的人。一名導遊帶了一隊遊客,正在指點說明。此外,廣場上沒什麼人。
8
威尼斯由一百一十七個小島構成,一百五十條運河穿梭其間,靠四百座橋連起,像一片由水道和陸地交織而成的蕾絲。
從馬可波羅到卡薩諾瓦到莎士比亞,從歌德到湯瑪斯曼,到拉斯金到詹姆斯到阿城,早在踏足威尼斯以前,我便在書中神遊了無數次。電影更不用提了,從《威尼斯商人》到《威尼斯之死》,從《兩小無猜》到《卡薩諾瓦》到《欲望之翼》,還有更多片名早已忘記的。威尼斯大概是上電影最多的城市。
剛好那年初美國導演麥克.瑞佛德的《威尼斯商人》上映,我們到戲院看了。不很喜歡,但後來還是買了影碟,為了威尼斯。也為了那最有名的一幕, 艾爾.帕西諾演的夏洛克以沙啞充滿悲憤和嘲諷的語氣說:「……你若扎我們,難道我們就不會流血嗎?你若搔我們癢,難道我們就不會笑嗎?你若在我們身上下毒,難道我們就不會死嗎?」那一幕,不管看了多少次還是震撼。就像《簡愛》裡心碎的簡質問羅契斯特:「……你以為我是個木頭人――是架沒有感情的機器?……你以為,只因為我貧窮、卑微、長相平凡又身材矮小,就沒有靈魂也沒有心肝嗎?……」一樣讓人心痛。
夏洛克那段話說盡了內心怨憤,顯示他並不邪惡,只是創劇痛深。莎士比亞把這最精采的一段話留給夏洛克,儘管他結局還是悲慘,我相信莎士比亞內心深處不是個反猶的人。
坐在威尼斯猶太區,遙想歷史當年,很難。旅人心境如光點水,難以沉入歷史的黑暗。
只能說,猶太區大概是威尼斯最素淡冷清的地區。
9
在一座運河橋邊館子晚餐,幾乎滿座,幸而還有一張靠牆的桌子給我們。臨窗角落上一張兩人小桌的客人換了三次,都是年輕漂亮相視笑談的情侶,像電影畫面。菜色普通,但葡萄酒好,光潔微酸的滋味。館子裡人聲嘈雜,貢多拉獨木舟滑過窗外。景象如夢,卻是真的。很清楚自己在扮演觀光客,看其他觀光客圓他們的威尼斯之夢,這美景裡帶了點悲哀。
晚餐後漫步過夜色裡的水城,燈影槳聲,迷離詩意,威尼斯忽然活過來了。我們也是。
到碼頭搭渡船回麗多島的旅館――麗多便是湯瑪斯.曼小說《威尼斯之死》的背景 。
小旅館清幽舒適,房間附帶浴廁,小而乾淨。房間貼了壁紙(不管在義大利哪個城市,住的旅館房間一律貼壁紙,倒是意外),白底紫藍和黃色小花,我這討厭壁紙尤其是小花小草圖樣的人居然不嫌。浴室四牆深綠瓷磚,潔亮微帶尿騷味。每早在前院早餐(陰雨時便在室內餐廳),是一天最愉快的時刻。空氣清涼,飄著咖啡香和鳥雀吱喳聲,白衣侍者端了咖啡壺走來走去。慢慢吃,閒聊,看別桌客人,看小鳥在一旁地上和客人離去的桌上啄食,毫無懼意,看院裡的花草樹木。院子外經常有摩托車和三輪小汽車的馬達聲,有種在台灣的錯覺。到碼頭路上,經過窄窄的街道,沿街幾層樓高的公寓建築,鐵柵門,一樓小店,如大溝的小運河,車輛轟轟來去,婦女提著籃子去買菜。恍惚是在台灣,回到家了,可以無事閒蕩,而不必奔來奔去做觀光客。
誰能不喜歡威尼斯?但總覺底下有個「可是」。原籍俄國的美國詩人布洛斯基年年冬季到威尼斯,因為他本性屬水屬冷。我們在水城三天,比驚鴻一瞥長,比日夜浸淫短,免不了擦肩而過的感覺。離開後也沒心心念念要再回去,不像有些地方不絕召喚縈繞心頭。
然而這麼多年來,或者在記憶裡,或者在書籍和電影裡,威尼斯還是誘人,將我吸進去,不絕迷走窄巷上下拱橋,尋找那個似乎沒看見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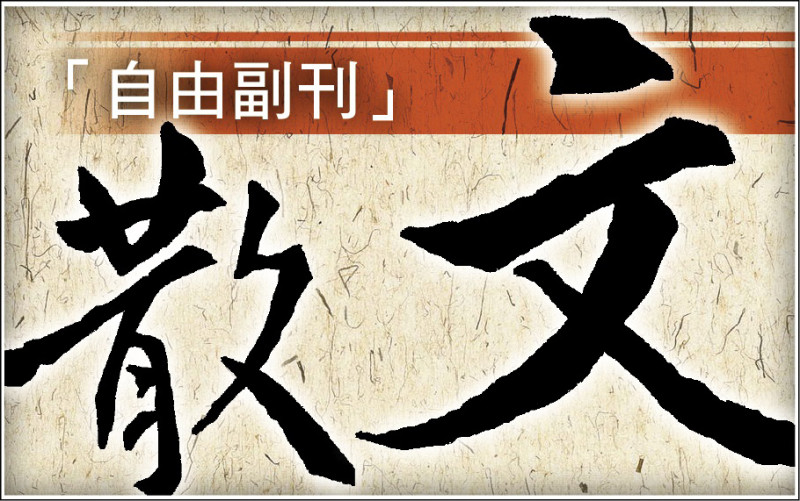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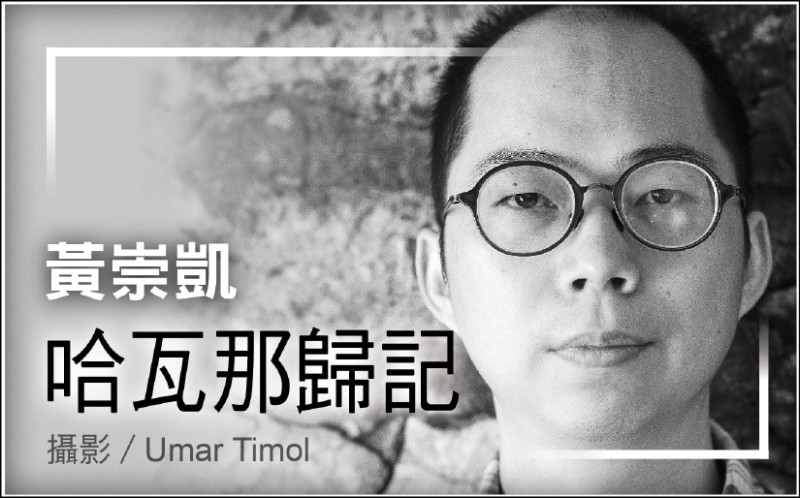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