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作家的藏所
編輯室報告:每一名創作者,除了隱身於書寫,在時空中,總也有一處不為人知的藏所──或許用來收留疲軟身體,或許用來慰藉徒勞心靈。
今日慷慨捐贈祕密藏所的是:鴻鴻、鯨向海與葉覓覓。
未來還將陸續推出其他作家的藏所,敬請期待。
聞到劇場就像聞到母狗一樣
文.攝影◎鴻鴻
巴布狄倫的回憶錄寫到年輕時他剛到紐約的情景。他是去找那些唱片上聽過的歌手的。紐約這複雜的大城他一點都不想去理解,卻可以對歌手出沒的小酒館如數家珍。
讀到這裡我忽然醒悟,我的祕密基地其實是劇場。到任何大城我第一個要找的便是劇場和歌劇院,看看有什麼戲上演。不要說柏林、巴黎、倫敦這些表演藝術勝地,就是任何不知名的小鎮,我也會跑到劇院門口張望,有什麼蛛絲馬跡便興奮起來,像我家的狗聞到母狗的味道一樣。安排行程時,也總要空一、兩個晚上,可以看場表演。即使戲不好,也可以藉此了解該地的人情與藝術關注。因而,我對許多城市的認識,往往從通往不同劇場的路開始;對一國文化的認識,往往從劇場演出的題材、演員說話的態度開始。
即使念戲劇系時,我也想不到日後會仰賴劇場如此之深。如果劇場的典範是讓人打瞌睡的BBC莎劇、或大都會歌劇院那種華麗而愚蠢的製作,我會希望這門藝術離我愈遠愈好。慶幸我生也晚──我常想,如果早二十年,我不可能會迷上劇場。
二十年前的劇場,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景象: 科隆歌劇院的《尼貝龍根指環》,伴隨華格納描述萊茵河的音樂,景觀呈現的是河底的垃圾場;柏林國立歌劇院的《茶花女》,以瑪麗蓮夢露的金髮造形,流浪在無盡的公路上;薩爾茲堡的《後宮誘逃》,把土耳其帕夏變成巴勒斯坦的解放英雄;列寧廣場劇院的《玩偶之家》,娜拉舉槍殺夫,屍體染紅了客廳裡巨大的魚缸;柏林人民劇院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一輛車在舞台上橫衝直撞;而碧娜鮑許的《巴勒摩,巴勒摩》,則是一面將舞台封死的牆,在我眼前轟然倒地,然後舞者在碎磚間開始跳舞……通過劇場,這廣大、複雜的世界,以強烈的情緒和力度呈現出來,拓展了我對現實的認知,也指引了我創作的方向。就像拉斯馮提爾讓以往的寫實電影像在扮家家酒,當今的劇場也讓已往的劇場形式成了剪紙模型。非此無以表達人們對這混亂世界的直接批評,那是時代真正的情感和聲音。
我逐漸領略到,劇場最重要的不是動人的故事、不是遊戲的趣味、也不是崇高的詩意,而是真實的「發生」,是思想和情感激烈交匯重組的地方。在任何城市的劇場看戲,舞台燈亮我便像得到許可一般開始呼吸,而所有不同的語言也都開始自行翻譯成易解的訊息。
台灣劇場常讓我沮喪的,不是形式簡陋或意念青澀,而是對劇場能量的視野短淺,好像劇場只能老這樣總這樣。不缺快感,欠奉的是對世界深刻回應的力量,有時簡直還不如口水節目或八卦報。所以,繼續勒緊褲帶出國看戲,也算一種逃避。記得薩爾茲堡藝術節期間,我在城外露營,到了傍晚,看到一對盛裝的老夫婦,從另一個帳篷鑽出,挽著手走向歌劇院。那真是我夢想的晚景。
讀巴布狄倫回憶錄的時候,我還想起西門町一家唱片行的女孩。她穿著不起眼的工作服,趴在電腦前,一副快睡著的樣子。但你一遞上要找的任何歌手,即使拼寫錯誤,她也能立刻一一道來他們的背景、專輯、代理、進貨情形,並告訴你多久可以訂到以及單價多少。我可以感受到她在這個領域裡的無上樂趣。對我來說,劇場也不過就是一間這樣的唱片行。 ●
可以相擁死去的地方
文◎鯨向海
我們相戀四年了。猶記得第一次,躡手躡腳,低聲交談,燈光微暗中,摸著樓梯的欄杆前進。開門之後,我們都不自覺鬆了一口氣,就是這裡了。這是一個可以隨意脫下衣物,光身走來走去的地方;可以認真悲傷,慢慢恢復體力的地方。在這裡不會犯錯,也沒有人會對我們指指點點。
這裡又像是童年那些用來逃避成人世界的祕密基地;我們變身為王子和公主,埋下寶藏。忽然之間,又回到了騎馬打仗的年紀,於房間裡搔癢對方的身體,於沙發上互毆,在地板上對掐彼此的脖子,然後又在床底扭成一團。這是不能讓狗仔隊拍到的地方,卻可以盡情裸露自拍。這裡正是《斷背山》,是《鐵達尼號》,是金基德電影裡,情人們靈魂安頓的「空屋」。
一位編輯朋友曾說:「我早就不期待作家本人會和他的文字一致了,這樣才能夠去承受那必然的落差。」你也早就發現,沒有人可以永遠保持神思飛馳的狀態,當我愈是遠離了美好的靈感,降落在你的床上,坐在你的對面時,愈是不堪一擊。但你包容了我粗魯的吃相與睡姿,我不寫詩時的脆弱,我身體的氣味一不小心就殘留在你的被褥裡。一如你的房間也以其特殊的味道,終年薰繞在我的衣服上。你曾緊張地問:「我有體味?是怎樣的味道?」我得意地說認識你多年,從一開始我就認得了你的味道。無論夏季冬日,你的氣味總能夠穿透那些物質性的世界,滲入我的精神狀態,使我驚醒,使我惚恍。
市川隼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的電影《東尼瀧谷》裡,東尼愛過的人過世之後,都留下了他們生前的人格所凝聚而成的物質:滿屋的華衣、舊唱片。一直要到將它們全部清空了,才能夠與他們告別,他也就真正孤獨了……你的房間幾乎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物質,你的蒐藏都是純粹精神上的,連我也是。你是一個鋼琴手,常為此無聲的世界做各種美好的彈奏。你既無大肆宣傳,也不收費;你只是靜靜坐在公寓裡,日復一日,巴哈貝多芬李斯特拉威爾史克里亞賓……有時興致一起,連我的胸膛、大肚腩還是闊背肌都可以被你觸擊成鋼琴。在房間裡,當你一言不語踩著鋼琴踏瓣獨自往前走了,我只能遠遠跟在後頭,無法辨識你坐在哪一個時代裡,正依附著哪一個樂派的魂魄。
這時,我往往像是被你放逐到一個荒島,有最寧靜的海和最悠長的夏天可以揮霍。北野武的《奏鳴曲》描寫一群幫派火拚後,躲避至某僻靜沙灘的黑社會分子;卻在沙灘上玩起了相撲、煙火大戰、挖陷阱、跳能劇、俄羅斯輪盤遊戲。而我也喜歡躺在你的床上安心地寫作、閱讀、看電影、打瞌睡,像是一個萬事具備,等待再次犯案的盜賊。
最後我們總一起躲到了被窩裡,像是挖地道躲進防空洞一樣。李宗榮的〈冬日〉:「整個冬季我們無所事事/伏案寫詩,占星、飲酒、做愛。/唉,雨季困我們這麼深/霉味比濕氣還重/我們為什麼不相擁而死去呢?」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不那麼適合聚會的那種族類,不是鄙視他人,就是遭人鄙視。雖然人都到齊了,噓寒問暖看似熱絡,卻無法認真地與某個心靈對話,注意力被分散了,於是得更用力去笑,去聆聽,稍微怠惰歇息一下,就會有人關心地詢問:「還好嗎?你看起來很冷。」同桌共食,像是散落在銀河系四處,雖然清楚地看見彼此的光亮,事實上距離卻如此遙遠。
沙特說:「我們注定是自由的。」那種自由是徹底的孤寂,是整個世界只透過我們的肉體和精神感知而存在的「虛無」;意味著除了自身,我們其實無所依憑。而這裡就是「自由的深淵」,是公元2006年,傳說那座落在此城千門萬戶之中,戀人的房間。世界被隔絕在外,我們僅有的是彼此的體溫和愛。梳洗完畢,穿好衣服,我倚窗看著樓下撿垃圾的大嬸,以及隔壁賣香腸的阿伯,或者騎腳踏車經過的小弟弟,不免也感歎,他們必然沒想到有人的伊甸園竟然潛藏在他們的日常瑣事之間,人生總是始料未及。 ●
牛頭山的祕密
文◎葉覓覓
去年夏天,我帶著十二口箱子離開花蓮,來到這座綠色小島,練習在黑板寫字、打勾以及和島上的孩子們說話。
每天頂著太陽散步,頂著頂著,常常覺得身體太甜,於是就伸手握一把風裡的鹽;有時覺得渴了,就把寶藍色的海當作奇異果汁,用眼睛喝。
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變電變壓或變形,我立刻就愛上小島生活。
綠島的夏天, 是整個租借給觀光客的。環島公路就像一架不停旋轉的銀色摩天輪,塞滿了成群結隊的機車和沸騰的叫喊,觸目所及的風景裡,都黏著一疊疊手舞足蹈的人影。
我一向喜歡安靜地發呆,不大能忍受這種輕易被拓印在人群裡的感覺,於是,來到島上的第三天,我就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祕密基地。
牛頭山。
沒有明確的標示、沒有華麗的入口、沒有涼亭、沒有石階──若是沒有導遊帶路,一般的觀光客並不會到這裡來。
我很慶幸它可以這樣被忽略。
從牛背走到濱海的牛頭需要花費一些時間,細長的紅土小路不時端出一些新鮮的牛糞和羊糞,我喜歡跨過它們,像跨過一粒粒剛捏好的泥偶。
上了小斜坡之後,回頭俯視,可以看見大半個綠島,一排排深綠的樹林交織著淺黃的草原,彷彿一條質地綿密、色澤溫暖的頭巾,包覆著海洋的頭顱。
寬闊的視野都拉拔起來。
然後你會看見一個斑駁老舊的碉堡、一個尖尖的山丘,然後下降,來到一大片青青草原。
無數次,我在草原上遇見一群野生的山羊,牠們總是無聲地埋頭吃草,一旦我慢慢向前靠近,牠們便會驚慌地斜著眼睛注視我,接著在老山羊的一聲吆喝下,集體逃跑,逃到下面的懸崖陡壁,用奇特的四十五度站姿,繼續吃草。
做為一個外來者,我經常感到歉疚,多希望自己也能化身為一頭羊,和牠們共享這片美麗的草原。
我通常在傍晚四點的時候出發,那是整座島嶼傾向冷卻的時刻。上山之後,我會直奔兩隻牛角中間,望著薄荷糖般的海水和鄰近的樓門岩,聆聽礁岩上數以百計的海鳥發出脆笛酥式的吶喊。
等到被灼熱的陽光咬到受不了,就退到右牛角的草坡上,找個陰涼的位置坐下。坐著坐著,我漸漸以為自己在荒島上了,除了多層次的藍和簡單的綠,除了遠方狀似幽浮的船艦,其餘東西都好遙遠,有一股幸福感從我的體內湧出,像一面沿著玻璃試管不斷上升的旗幟。
我可以在那裡發很久很久的呆,直到腦袋裡浸滿輕盈的詩句。
大約在五點半之後,就陸續會有大批的遊客上山來,為的是一睹夕陽的亮麗丰采。不止一次,我聽見有人興奮地指著懸崖上的羊群, 大叫: 「梅花鹿耶!」於是開始和同伴爭論起是鹿、是羊或是牛的問題,整個牛頭上鬧哄哄的,把小寐般的靜謐給打亂了。這時,我只得收回思緒的釣線,戴起帽子,逃離現場。
後來,為了能夠不被打擾不被發現,我在林投樹叢裡找到一個適合躲藏的地點,雖然無法看見珍貴的夕陽,卻可以觀賞瞬間浮昇在海上的月亮,以及一片杳無人跡的米黃沙灘。
每當腳下的海伸出白色舌頭,敲出冰涼的聲響時,我心裡就會產生一種莫名的震動,想要墜落,墜落到山塊底部,和島嶼的記憶與古老的熔岩合而為一。
就這樣,我在盛夏的黃昏裡,跟青春支領時間,坐在突出的斷崖上,度過許多夢幻的空白頁。
九月的某一天,我如常來到牛頭山,草原上既沒有人也沒有半隻羊,天空灰灰暗暗的,我走到牛角後方的缺口,眺望遠處的公館村和三峰岩。約莫六點鐘的時候,一個朋友打電話來,講了幾句話,我猛一回頭,赫然發現一群水牛正大搖大擺地走到我後方的草原,我惶恐地跟朋友說:「牛來了!」隨即掛掉電話,愣愣地與牛群對視。大概有十來隻牛吧,數量非常壯觀,我捨不得離開,掏出相機就開始拚命拍,兩隻公牛先是盯著我看,接著朝我快步走來……最後我當然跑了,顫抖著用一種盪鞦韆的姿勢。
我一邊跑下山, 一邊在心裡吼著:「這是我的祕密基地!」不久,天就黑了。
像是一塊鬆鬆垮垮的餅乾,我溶進夜晚的唾液。
然後是冬天和春天,我的小島生活還要持續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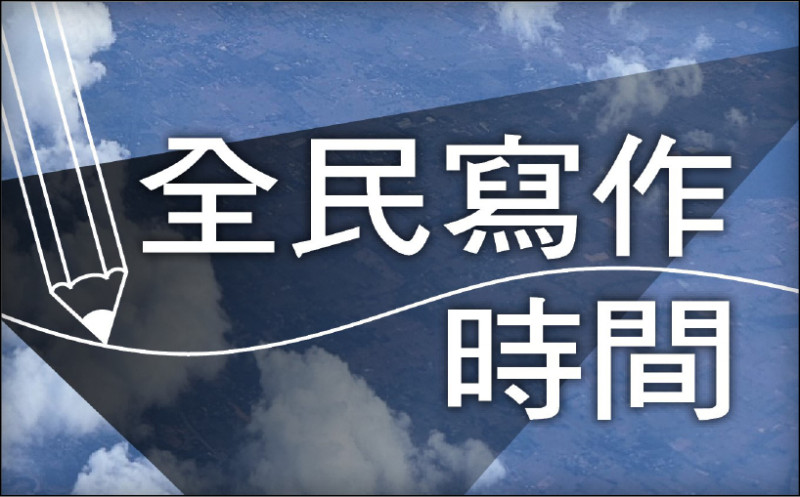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