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六四」是一道扛在肩上的閘門 - 讀《王丹回憶錄》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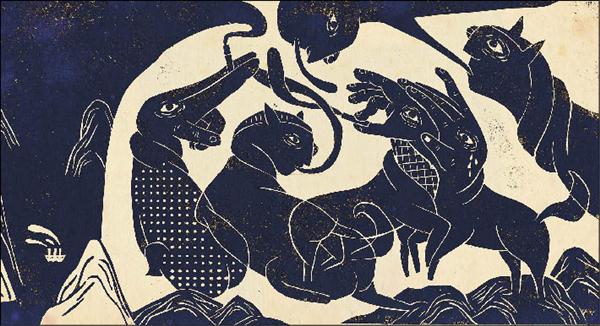 圖◎阿尼默
圖◎阿尼默
◎余杰 圖◎阿尼默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剛上北大不久,讀的第一本所謂的「禁書」就是《王丹獄中回憶錄》。那時,我認識了一位原參加過80年代韓國學運的韓國留學生,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到留學生宿舍,神祕兮兮地拿出一本包著褐色封皮的書借給我讀。當我發現書名是《王丹獄中回憶錄》時,立刻被深深吸引住。那天晚上,我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一口氣讀到東方之既白。我用自己青澀的青春呼應著王丹青澀的青春,似乎漆黑的窗外響起了昔日的細雨與呼喊──直到天亮之後,我才回到庸碌的現實之中:跟充滿理想主義的80年代相比,北大的校園早已物是人非。
與王丹的第一次相見,則是在十年以後哈佛大學的校園。那是2003年,王丹還是那張略帶羞澀的娃娃臉,雖然比我長四歲,看上去似乎比我還要年輕。又過了十年,王丹從哈佛大學畢業,輾轉到台灣的大學任教,展開了歷史研究和人權活動之兩翼,深受學生及台灣年輕人的喜愛。歲月滄桑,海外民主運動潮起潮落,中國國內情勢日新月異,這一切都沒有洗去王丹身上濃得化不開的理想主義氣質。從這本《王丹回憶錄》中就可發現,王丹一輩子都變不成老謀深算的政客──當年,他放出的「最大的願望是當北大校長」的「狂言」,確實是他的真心話。
惟有「恆久抗爭」才能走向勝利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寫道:「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這裡的「肩住黑暗的閘門」的比喻是有典故的:在關於隋朝末年好漢們逐鹿中原、問鼎天下的歷史小說《隋唐演義》中,陰險狡詐的隋煬帝設置了一個巨大的演武廳,讓英雄豪傑們為爭奪天下第一的名號自相殘殺。然後,隋煬帝在大門上安裝了一道千斤閘,企圖將眾人一網打盡。出乎其意料的是,一名像《聖經》中的參孫的大力士、號稱「天下第四條好漢」的雄闊海,在閘門落下的一瞬間,發出神力將其扛住,從而將身處險境的英雄們全都放走。但是,由於沒有人來替換他,最後他殉難於此。魯迅自我期許的這個肩起黑暗的閘門的英雄,可以與西方文學經典中推著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衝向風車的唐.吉訶德並稱為「理想主義三傑」,其悲劇性甚至有過之。似乎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驅者們最為經典的形象:肩起閘門,步履蹣跚,向著光明的方向決然前行。
若以1989年被中共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在此後二十多年裡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而論,堪稱中國在驚濤駭浪的「出三峽」過程中的一個縮影。當年,槍響之後,這群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學子,如蔓藤一樣被連根拔起,扔到大洋彼岸。「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統統只能在夢中重現。然後,從舉世矚目、萬千寵愛集於一身的頂峰,跌落到毀謗鋪天蓋地的低谷,人生宛如過山車,個中甘苦不為外人所知。在他們當中,有的淡出了愈走愈窄的民主之路,有的華麗轉身成為腰纏萬貫的商賈,有的甚至背叛當年的理想與熱血而與強權共舞。我曾經想,如果能訪談到這二十一人,寫成一本訪談錄,寫他們二十多年來的變與不變,一定是一本很有趣的書。當然,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計畫,因為其中的某些人之間早有「不圖老子與韓非同傳」之心結。不過,在尚未梳理出當年學生領袖的群體形象之前,從王丹的這本回憶錄中,讀者自可欣慰地發現,還是有人在繼續走那條「少有人走的路」。
王丹將「六四」當做一道不可放下的閘門,二十多年如一日扛在肩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些年來,我到處奔波,凡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會涉及『六四』這個主題……我感受到的溫暖和支援遠遠大於冷漠和攻擊不止十倍。」王丹面對的對手是一個不可一世的巨人──荷包鼓鼓的中共就像英國作家路易斯在《納尼亞傳奇》中塑造的那個冷酷凶狠的白女巫,其手指揮舞之處,一切生機勃勃的花草蟲魚都凝固成冰天雪地。而「六四」被冰封在「大國崛起」的幻想的最底層。
從表面上看,中共在這場「輿論戰」中取得了暫時的成功,而王丹的抗爭則走進了漆黑得看不到盡頭的隧道。二十多年以來,「六四」屠殺在中國當代史上成為一面碩大的天窗,成為溫家寶口中實現經濟繁榮必須付出的代價。天安門母親淪為不可接觸的「賤民」,天安門母親最親密的朋友劉曉波身陷牢獄,王丹甚至連累溫柔堅韌的母親成為無辜的囚徒。但是,如林肯所說,謊言可以暫時欺騙所有人,謊言可以永遠欺騙部分人,但謊言不能永遠欺騙所有人。當「六四」的真相從冰層之下脫穎而出的那一刻,必定是中共刻意營造的「復興之夢」徹底灰飛煙滅之際。在這個意義上,王丹的恆久抗爭,王丹的著述與演講,王丹在台灣給那些在和平與富裕的年代裡長大的學生所上的每一堂課,都是推倒「中國的柏林牆」的努力的一部分。
「北大人」還不是真正的「知識人」
80年代末,王丹就讀的北大,尚有「五四」遺風的存留;90年代初,我就讀的北大,則在政治高壓和商業誘惑中連一張書桌都擺不下了。在王丹的回憶錄中,我從很多蛛絲馬跡裡可以發現,「八九」民主運動絕非偶然發生,那是80年代一波三折的思想解放運動或啟蒙運動所催生的必然結果。
近代以來,面對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地轉化為現代「知識人」。在此一過程中,國族的轉型與個體的蛻變,撕心裂肺,鳳凰涅槃,讓人不由不悲欣交集。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從京師大學堂到國立北京大學,從嚴復到蔡元培,「北大人」堪稱這一群體在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生命模式方面轉換的先鋒。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在北大當過臨時工的毛澤東,在教育界首先就拿北大開刀,幾番血雨腥風的政治運動,使得北大「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受到殘酷摧抑。不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80年代的北大部分地恢復了當年的榮光,從王丹的經歷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他,可以組織社團、編輯刊物、聯絡知識界名流,生活斑斕多姿,青春如光閃爍。由此,也奠定了王丹一生都執著的「北大情結」。
但是,「北大人」還不是真正的「知識人」。其實,王丹對「北大人」這一身分亦有所警惕,對這一名稱背後的傲慢和虛驕也有所認識。何謂「知識人」?歷史學家余英時倡導用「知識人」的說法取代「知識分子」。他認為,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知識分子」用了幾十年,從前是一個中性的詞,後來就變質了。所以,余英時不想再用。他強調說:「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人」,必須具備精神上的超越性、經濟上的獨立性和價值上的恆定性,而在「北大人」的傳統中,卻滲透了「學而優則仕」、「天下興亡,唯我有責」的士大夫的優越感以及對權力的依附性。在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重現了帝國時代公車上書的模式,比如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外面的台階上,雙手高舉請願書,悲情固然有餘,卻自我放棄了在政府面前的平等與獨立。而在很多與軍隊對峙的場景中,學生、市民與軍隊唱的居然是同一首革命歌曲。這種反抗者與反抗物件之間的「精神同構性」決定了運動必然走向失敗。
在探討八九民運失敗原因時,王丹首先提出「思想基礎」的薄弱。他指出:「整個運動的過程中,理論旗幟上大書特書的始終是『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這些民主的基本操作方式;只有在6月初的劉曉波等四人絕食中,才提到了深層次的問題:民主運動的非暴力原則和知識分子的參與使命。參與運動的絕大多數人,並未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這次運動的深遠意義,而只是把它當做十年來又一次針對某一具體社會問題的不滿爆發,這就削弱了運動在理論上的號召力,沒有能切實地激發出廣大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對於廣大的參加運動的基層人民來說,由於缺乏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上的訓練,在關鍵時刻也出現了迷茫、混亂、非程式化和非理性化的做法。」這個分析敏銳而中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獨大的「國」和封閉的「家」的二元結構,而缺少具有自治精神和自足力量的民間社會。用王丹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政治文化,過於強調倚靠『清明政治』,也就是說,個人過分倚賴國家,不是把自己當做國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本來應當是為個人服務的國家身上。」對比韓國的學生運動及台灣的學生運動中對公民社會的自覺追求,仍然將改革的動力寄託於中共高層的「八九」民運,可謂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直到今天,「北大人」離「知識人」依然距離遙遠。在北大教授中出現了林毅夫、朱蘇力、孫東東等為黨國體制塗脂抹粉的御用文人,也出現了孔慶東、韓毓海等為「文革」和北韓金家王朝辯護的極左派乃至毛派,北大的聲譽一次次在「腐敗門」和「淫亂門」中遭受重創。在中國社會劇烈轉型、貧富懸殊、腐敗肆虐的今天,民眾很少聽到「北大人」發出堅定、獨立而清晰的聲音。也許,真的要等到有一天,王丹歸去來兮,當上北大校長,北大才能重振雄風,「北大人」才能提升為美國學者羅素.雅柯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所說的「以大學為根據地,充實滋養政治與文化生活的公共知識分子」。(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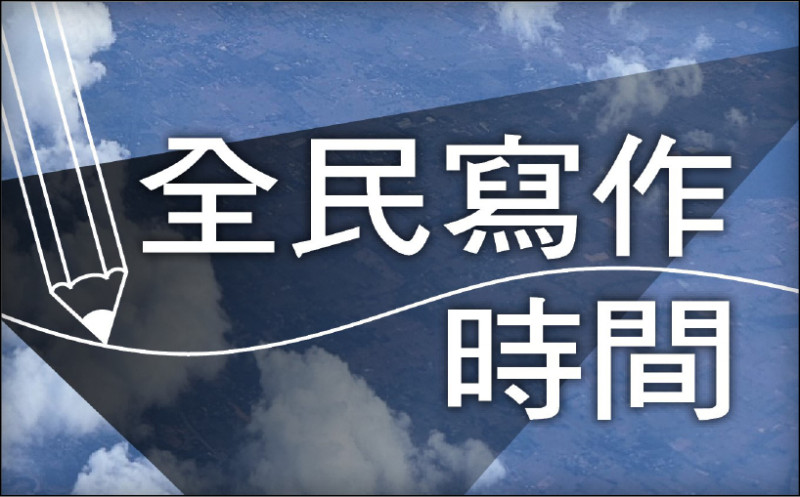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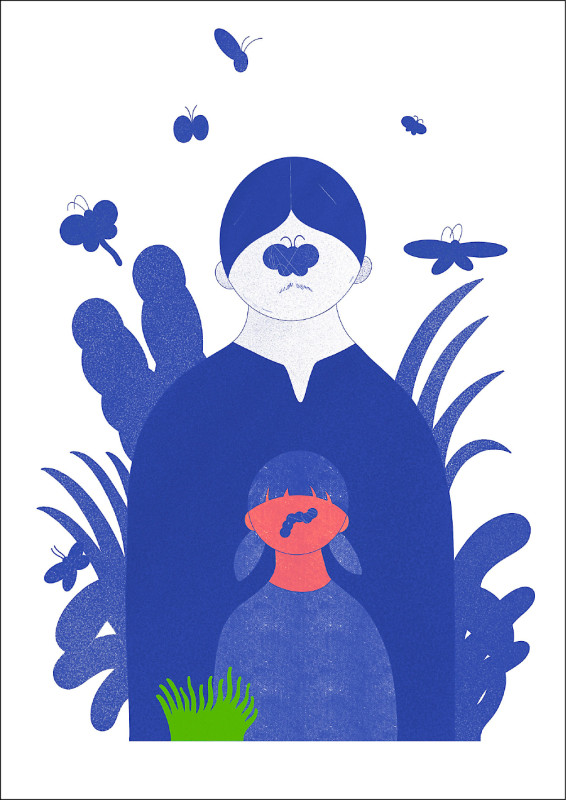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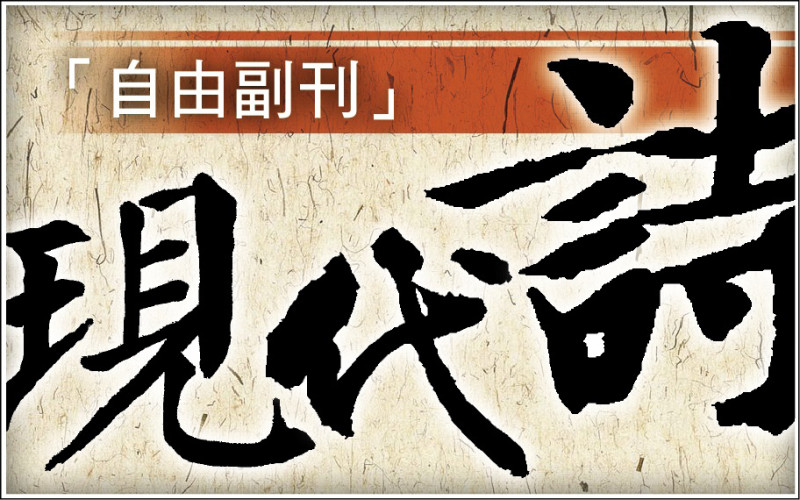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