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夏哨
◎李振豪 圖◎太陽臉
站哨的時候,很容易就能進入一種相當的沉思,靜默地以軍人的身分,與原先的自己和整個環圍的周遭,進行一種各執主觀的三方對話,這些對話,有時平淡間又具有深味,有時則令自己驚奇。
在對話的其中,很多在平時料想不到自己也能稍微靠攏往「哲學性」的思想,出奇不意地都會出現。那些關於青春,關於服役,關於日子,關於季節的……像是季節這種事情,該怎麼講所謂的因緣巧合?它的循環偶爾弔詭,但終究也是要走往規律的道途之上,或許無奈是有,感覺上像是因為某種箝制而受了虧待,然而也確實如此。往往,今年和去年的某單一季節的氣溫平均值,不過是攝氏之度間的差異。但是,比較起人類文明中的時移事遷,那種時間將其本質的奸險驗證成人類世界裡的情節,迸發火花又有衝突、柳暗花明卻又轉折的費解,大自然實在是顯得單純,且又單純得偉大,太多太多了。
是以,在哪一個時節進入了人生中的哪一個階段,其實都是自然。這種自然溫順而有理,但又不容爭辯與質疑。說成是宇宙間因天體運行而產生的,巨大而繁複的系統,難免因為一種難以觸及的遙遠而顯得無關緊要,但若是扯到天氣,就日常得平易近人許多。
我依然記得,那天下雨。
或許永遠也忘不了。
我因為一張兵單,被迫綁在春天的尾巴上,匆匆地加入這龐大體制中一列小小的,新兵的隊伍,入伍服役。火車車廂裡上演著好幾種質地不同的沉默,或許再沒有一種旅程,能使這樣一群血氣方剛的不管是男孩還是男人,對它是熟悉的,也明知它總會到來,卻又同時無法控制地,產生大量的不安與未知。當兵這檔事,從一開始,就是充滿了無奈。它蠻橫地驅使與介入我們的生活,又同時受到法律的保護,使我們的無辜顯得如此無力。
就像天氣。只是不那麼具有說服力。
那天下雨,營區裡一片混亂。到處是缺乏秩序的隊伍在雨中四處奔走,一會兒去哪裡剪頭髮,一會兒又到哪裡去體檢。所有人的神色都帶著些許的緊張,哪怕有些還能談笑風生,肢體的動作也總在所謂「班長」終於耐不住性子開口罵人的時候,而瞬間因驚懼而產生不協調。雨依然下著。墨綠色的雨衣發下來,著裝不易,又引發一陣混亂。不斷的混亂與無所適從,讓我們深深體認到自己「菜鳥」的身分。雨繼續下著,非常自然地。
等到我結束新訓的課程,下了部隊,夏天已經像握捏著流水號碼牌,終於輪到自己了那樣,完成了銜接與報到的手續,全面占領了晴朗的天空。一切依然是那樣地自然。
那些令人無論在心理還是生理上,都感到無比虛脫的訓練過程,無條件地被時間收服,進而打包,成為回憶。然而我們都清楚,回憶通常只能支撐起不甚客觀的印象,即便它是如此的雄據於身體的一方,分分秒秒都在影響著我們的情緒,而我們跟隨情緒的號誌前進,一段時間之後,便轉變了心態。
人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便有了回憶,產生了改變。
然後我開始站哨。
我們的哨所,同一時段需要兩人服勤。老實說這樣的需要也不知是於何時訂定,總之軍中是這樣的一個體制,它所沿革下來的傳統鮮少有好壞之分,唯有服從是保全自己的不二法門,就好比下級服從上級,副哨聽從正哨,對與錯唯一的分野不是有理是級職,而這樣的制度天經地義,一切因為如果敵人來了,我們會知道閉上嘴巴只管聽令,當上級叫我們衝鋒陷陣時,我們就絕對不會臨陣退縮。
真是這樣?我在站哨的時候,偶爾思考這樣的一個疑問,而答案總是迅即而生,辯駁都免了。
我所服勤的哨所,位於營區中一個小小的側門,正副哨兵分立門的兩側,磚塊水泥砌成了兩個約莫兩尺見方的哨台,三層階梯的高度。電擊棒交接,口令與準則交接後,上下哨衛兵以蝴蝶步互換位置。敬禮,禮畢,向左向右轉之後,帶哨官向還有一小時哨勤的哨兵下撤警戒的口令,下哨哨兵便隨著帶哨官回到連下卸裝休息,上哨衛兵則踩過哨台的三層階梯,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正式擔起哨所安全的責任,進進出出的人員管制,突發狀況的應變與確實回報……每一個重點都相關著自己的假期,所以有格外慎重的必要。
因為資歷淺,關於哨勤,毫無意外我站的全是副哨。第一次站哨,就是夜哨。夜半裡,好不容易克服了滿身奔竄而出的汗水黏膩,漸漸進入沉睡的狀態,卻被二十四小時輪流不打烊在連上負責相關勤務的安全士官喚醒,絕對稱不上是一件快樂的事。
多半的時候,他們會用手電筒的光掃射你的臉,如果你還不知好歹繼續沉睡,他們會輕拍你的床,叫你的名字,說一聲:「上哨了!」然後看著你睜開惺忪的睡眼,微微地挪動頸子避開那快把人刺瞎的光,然後一聲不響地離開。
從墨綠色的蚊帳探頭而出,然後下床,開始著裝。在黑暗的寢室裡,只有幾只電風扇無力地吹送著溫熱的風,它機械式的反覆運作其實也多少象徵了一種軍隊裡的生活模式,看似無意義,卻又有所貢獻。或許並不如《莒光園地》電視教學裡,用著極其華麗與浮誇的詞藻形容的那樣,非凡而篤實,但就維持這樣一個巨大得難以全面振作的體系而言,確實是有一定實質的意義。再怎麼說,沒有軍人,就沒有軍隊,沒有軍隊,也就沒有所謂的軍備與國防。有時我們需要這樣努力地說服自己,才能繼續保有一種最起碼對自身身分的尊重。雖然大多數,我們比較在乎的是,沒有電風扇,我們軍人要多艱辛,才得以在窒悶的夏夜裡攀進夢境的邊陲,暫時將自己拋除於迷彩的身分之外?然而,儘管我們一點也不介意在夢境裡恣意地腐敗,卻依然像自安穩的土壤裡被拔起的蘿蔔那樣,回到了現實。寢室裡,安靜裡隱約有一些細碎的聲響,諸如窗外樹枝葉片因風飄磨的聲音、鼾聲、情節模糊的夢囈……在這樣的時刻裡,沒有什麼是特別趕忙或者從容,只消在活動間不經意地接收這獨特氛圍的聲息,像是環境音反而給你寧靜的感受,要更勝過全然的無聲。我安靜而仔細地換上整齊的迷彩服、紮上S腰帶,戴上鋼盔……然後離開寢室,準備上哨。
夏天有個好處,半夜被迫醒來,迎接我的第一道空氣,不會是冷冽而割人的。但實際到了哨所,站上哨台,我才知道,夏天站哨,全然不是一件那樣相對美好的事。防彈背心厚重而緊繃,沒有多久,我便已流了滿身的汗,由裡而外一吋吋地浸濕了我的迷彩衣。幾班哨站下來,濕疹也開始從我的背和胸口冒出來,絲毫無計可施。夜哨還算是好的,站正午的哨,那折磨才是嚇人,如果沒有藉以轉移注意力的事情,真會活活曬成人乾。
然後我發現,在軍中,似乎再沒有什麼,會比當一名哨兵,更有機會觀察一日的種種發生。夏天,清晨五點半,部隊起床。遠方開始傳來一些部隊行進間答數的聲響,隨後是唱〈國歌〉的聲音,然後是早點名……部隊如此規律地在艷陽的監督下展開每日行程,哨兵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可以名正言順地「脫離部隊掌握」。當過兵的人常說當兵最大的麻煩,就是缺乏自由,入伍之後,我才深刻地體認到這一點。一直到正式地站了哨,我才發現,哨勤最大的功用,其實不見得是一種「看守」的作用,讓人可以暫時從一種緊湊的步調中脫離,往往才是它最大的恩惠。下午,睡過午覺之後,部隊又繼續操課,還沒有乾的衣服又完全汗濕了,就在這一來一往間,軍中的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以一種倒數的姿態被數算過去。
夜哨,整個營區在跨過一個時間點後,進入休眠,只剩下哨兵還努力維持著清醒,運作著,像是入夜後的小屋外頭,還亮著的一盞微弱的燈光。偶爾幾輛快車在營區鐵門外頭的路上急駛而過,我想像著那是一種怎樣的焦急,讓他們忘了白天黑夜的作息慣例?抑或只是青少年單純的瘋狂行徑?不曉得駕車的人當過兵沒?偶爾,有人從車窗探頭出來,向我們嘲揶似地揮手招呼,喊著:「阿兵哥!加油!」我們也只是哭笑不得,有時便索性跟著揮手,回應對方無論用意何在的熱情。
偶爾,幾隻或許是夏夜裡同樣也燥熱得睡不著覺,便到路上蹓躂地遊玩的野狗,無故地對著夜空吠叫,令人心裡一陣發寒。牠看見了什麼嗎?我想是敵人的機會應該不高。身為一名軍人,我們真正應該感到害怕的,究竟是什麼?體能操練?濕疹?還是不知不覺間被體制化?在軍中,荒謬的感觸是隨時隨地可以油然而生的。只要腦袋能偷到一點為個人思緒運轉的時間,感慨的對話就出現了。這些對話,通常出現在部隊起床的時刻,然後又在慌忙的著裝和催促的集合聲中,漸漸淡去,一直到站哨的時候,才又浮現它頹喪的臉孔,與你四目相對,相看而歎。而因為國軍就是這樣一個,用著一貫的機制程序,吞吐著一個又一個梯次的「不願役」役男,所以在恍然之間,也許那張想像中頹喪的臉,就實際地貼合成另一個哨兵的表情。正副哨間,原先極可能是毫無關係的兩人,在當下,卻有了一致的心情。
夜間,正副哨往往能聊上幾句,或者更多。我在不同的時段,聽著不同的正哨談著當兵以來的心得,也算是一種預習。其中,最令我感動的一次,是正哨提到幾種特別時段的哨勤,像是平安夜哨,或是跨年哨。曾經,一名已退伍的學長,在站跨年哨時,和當時的副哨聊起曾經和已成為過去式的女友一同到台北市政府參與跨年活動的事,他先是興奮地談起那時的熱鬧與擁擠,然後聚焦到兩人間的感情。後來他入伍,女友變心,他繼續待在營區裡盡國民義務,剛開始的時候很辛苦,後來漸漸平撫了心情,倒也能繼續倒數著服役的日子。聊著聊著,他開始哽咽,副哨看不見他落下的眼淚,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兩個人開始沉默,年就這麼跨過去了。
一切是那麼地自然。
我也沉默。
天空開始有了微小的亮度,但還不夠照明一切。
建築和樹影,都是相同程度的黑,看上去也是同樣的距離。眼前呈現出一種高度的反差,顏色空間都不存在了。世界只是一幀平面,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美。
漸漸清晨,一些老人出來到路上漫步健身。聽正哨說,這些老人不分四季,都在一個時間裡出來,其看破四季差異的程度,彷彿心中真沒有了地球軸心傾斜的事實。我想,有些體會,確實會因為經過多了,而漸漸看淡了。傷痕也是。
一日下午,我又服哨勤。沒有預警地便雷聲大作,豪雨隨即降下,典型的夏季氣候。那時,我已站過了颱風哨,大風大雨都嚇不倒了。反正,遲早是會下哨的,然後也會再上哨。也許,下哨之後,雨便停了,也許不會。也許,大雨過後,便一雨成秋。
一切都是那麼地自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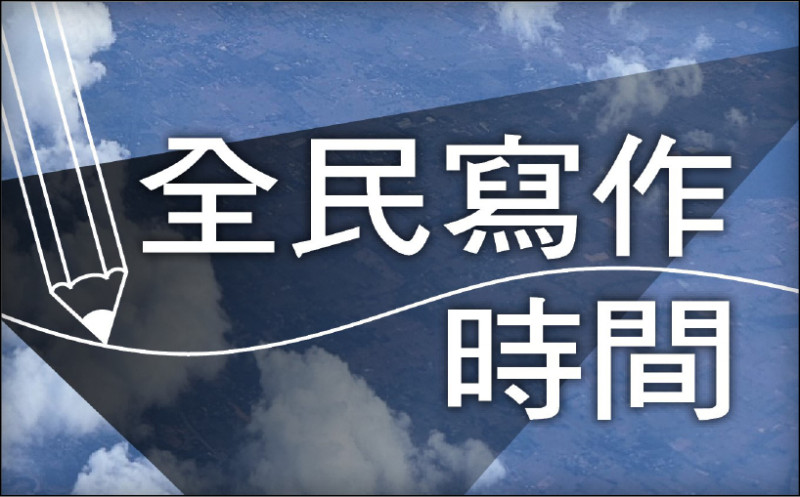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