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霧中風景
◎林文義 圖◎陳裕堂
我們所置身的島國,這狹長若蕉葉之土地,猶如一幅霧中風景。
永遠像鮭魚溯源般性格的人民,不渝地一再追尋關於原鄉最初之記憶。那麼,我們所愛戀的島國歷史又是什麼?什麼才是這生死以之的土地純淨、無偽的誕生風貌,什麼才是?子夜孤燈下,我一再試圖苦思尋索,堆積累疊的各式文獻、歷史典範,眾說紛云,似真亦假,目不暇給令人慌亂;是虛擬揣測,是藉之百年以降的外人筆記,諸如西洋傳教士、冒險家、殖民政權,甚至是未曾抵此僅流於異想的虛幻小說……四百年來,島國的歷史被一再地變造、虛構,也許昔之賢者曾奮力試圖還之本源,卻迷路於懵然茫惑的濃霧中,往更深暗的歧途前行,漸行漸遠。
史家們慣於宣稱:台灣歷史四百年。那麼試問:四百年前的台灣就不存在歷史記載了嗎?這是何等粗暴之妄言。十足漢民族本位主義的夜郎自大。或有人反詰:那麼,請教,四百年前的台灣誰可詮釋?莫非就是分住在島國山間海湄的原住民族嗎?草莽未啟,沒有文字。難道是以口傳、結繩、圖繪甚至神話呈現歷史延續?作家,你未免太過苛求了吧?不然你告訴我,四百年前,台灣又是如何面相?大哉問!我亦是迷霧中人,自是困惑於心。但就因為長年來的霧中行走,所以不懈地勤讀前人撰述之歷史典籍,比對、推敲、尋索……各家之言,莫衷一是;誰才是最接近真相的啟鑰,得以打開歷史緊掩的門禁,撥開迷霧,還以本質?
◆
史家慣於以四百年推演島國身世,約為明末遺臣鄭成功抵台前後起始,之前已是大航海時代最豐盛、壯闊的貿易往來、殖民地占領、天主教傳播、航路探測等等……而孤懸於亞細亞洲東岸邊陲的蕉葉小島,千年來居住的南島語系之原住民族,對外所見,想是濛霧中如天使羽翼般降臨的三枙帆船,來自遙遠異邦──真的所謂「文明初啟」嗎?究竟是傳遞神之意旨的善意,抑或是掠奪的終極惡念?我嘗以明末之鄭氏王朝對照民國之蔣介石政權相比擬,這毋寧是個極好的長篇小說體裁。曾經自許有此文學書寫大願,卻因自己學養不精,未敢貿然行之而流於抱憾;卻也不揣淺薄地試以三百年前西班牙海盜為題,時空穿越,襯之三百年後的現代,分別誕生於台灣、日本兩地,兩個眼眸若海色的女子,異想一部關於「隔代遺傳」的長篇小說,名之《藍眼睛》。
意義在於提示,千萬不要簡化了台灣住民的血統、身世。這十二萬字小說,僅是自我對我們所生長的美麗島國提出探問,拋磚引玉地祈求更多賢者得以回應更深邃之歷史還原;私心卻是自我叩問人生「幸福」最終極的情愛反思。是故在這小說卷首寫下如歌謠般詩句──
假如,記憶是古代深海的沉船
我們,應該學習相互遺忘。
泛黃的海圖,永遠朦朧航行的方向
迷航的三桅船啊,百年尋不到出路彷彿祈問上帝:究竟天涯在何方?
時間停歇,我們傾聽眾鯨歌唱美麗的眸啊,深海般之純藍……
這浪漫的小說想像,自有某種悲壯淒美的歷史意涵,本質是試圖呈露被殖民的島國宿命;在書寫過程中,遙想三百年前的西班牙無敵艦隊二副紀梵希面對蠻橫壓迫,義憤填膺地奪船「聖馬丁號」叛逃淪為海盜。從地中海出直布陀羅,越非洲南岸,航向命運未知的茫茫汪洋,抵達印度到中南半島,上溯中國澳門,繼而北上琉球,最後因與鄭芝龍海戰,船體受損,退至福爾摩沙北島的淡水聖地牙哥城堡(今之紅毛城)暫泊,得以邂逅凱達格蘭族女成婚,再返回海上,流亡以終,後代卻留了下來。
小說《藍眼睛》的結尾,作者沒有給予答案。盼望讀者在閱畢掩卷後,各有各的揣臆,正顯示我們所置身的島國歷史就是如此迷惑,彷彿霧中風景般地不確定,不就說明了而今台灣的百年宿命及其妾身不明的未來處境?
◆
歷史仍在迷霧中,何人能解?連雅堂先生慨歎:「台灣固無史也!」突顯出歷史真貌尋索之難。亦呈露彼時在日治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心境的無奈荒涼,更是上承下繼的留其天問。
清代旅人郁永河《稗海紀遊》形之文學,僅是歷史一景,因是採硫暫駐,浮光掠影在所難免。再者如藍鼎元、沈光文等拓台先人,亦是僅記載其經略之舉。更早期的荷蘭、西班牙文獻多的是貿易時程、要塞記事。極少真正見及原住民族觀點的歷史詮釋,才是最大缺憾。
日本殖民時代與國民政府分占台灣百年。前者視之永遠的南方疆土,後者則以蔣家政權做為禁臠,根本不是站在人民立場對待歷史本源,而是誤導及愚民;毋寧是對台灣人民最惡質的侮辱及對歷史的戕害,使得如今有心的後來者對還原歷史的奮力感受到更大的艱難。
尤其是在國民政府宰制的黑暗戒嚴年代,被放逐或自我流亡的先賢者,遠在日本、美國等地的知識分子,竟其一生夙願,埋首資料,斷簡殘篇,苦思尋索,盼求統合成理,連貫歷史被篡改、湮沒、失散的軌跡,串之形塑為較完整的原貌。這是嚴酷統治下的國府當局所不允許的,在那風聲鶴唳、險峻無明的蕭索時刻,那種堅執的勇健意志,值得致予無上敬意。如同眾所周知,史明先生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王育德先生的《苦悶的台灣》、黃昭堂先生的《台灣總督府》等等……在台灣的曹永和教授一生默默耕耘,身為學界之扛鼎已早有公認。近者猶值得感佩的如學者翁佳音,遠赴荷蘭阿姆斯特丹苦修古荷蘭文,嘗試以此深研四百年前,東印度公司在台灣三十八年的種種事略。民間學者長期以庶民形象、時代顯影著手,窮盡一生之力,莊永明先生當是第一人。
◆
及至現今,雖說言論自由,民主盛行,眾聲喧譁之間,卻亦有吊詭的陷阱及隱藏的某種誤認的危機存在。
政權更替前後的歷史還原過程,正是審視史學家沉淪或提升的重大轉折,不可不慎。若以政治力介入或意識形態重整歷史,就怕陷入符咒、民粹口號般地一相情願之偏執,這是最令人憂心之事。
譬如歷經六十年,讓三代台灣人噤聲驚懼的「二二八事變」,史學作家陳芳明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以「兩種不同的文化差異所接觸、撞擊所引發的衝突。」明示,這種澈晰識見,已導言出往後得以追索悲劇的準確指向。近見官方歷史調查出爐,爭論再起,又陷入迷霧般紛擾糾葛;少見正面的純粹學術之辯證,卻成為黨派及意識形態之爭;執政、在野各自說法流於某種意氣及責怨,迷霧未散卻見深濃。
史家撰史,當以人民立場及觀點為思考本位,還原歷史必得排除黨派考量、淪於意識形態之盲點;相信二二八事變的最後真相,會在理性的、純歷史學術的辯證,讓當年的原始文件說話,自能撥開迷霧,雲淡風清見其原貌。反之各執一言,求其利於己見,故意隱晦、欺瞞某些在當時大環境中的動亂、不安因素,誤解或蓄意的報復、私心皆為不宜。歷史之偶然成為必然,那是人民最不樂見的撕裂與傷痛。
對於文學作者而言,歷史是最珍貴可感的養分,但若沒有真相,甚至是經過篡改、刪減虛增的失真史料,藉之歷史做題反而是將文學本質誤陷於更迷茫未明的濛霧深處;向歷史借題,文學作者是另類的走索人,如履薄冰。
是以,我所書寫的小說,僅可歸之於異想虛擬,揣摩歷史的某個時刻,十足地漫行於迷霧中,自尋一種生命情境的風景看待;但多少亦是對歷史真相盼求最後的明澈理解。
前人說過──有時,小說比歷史還要真實。冷靜睿智如你,如何看待迷霧中的台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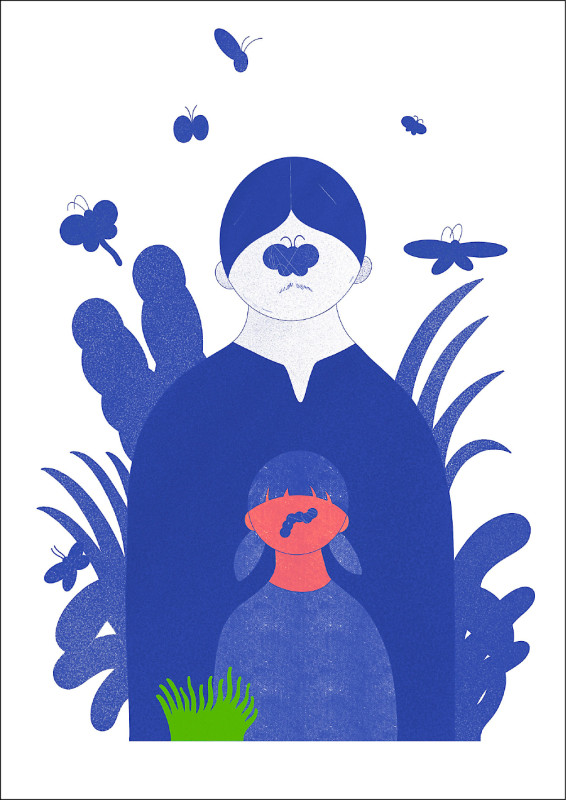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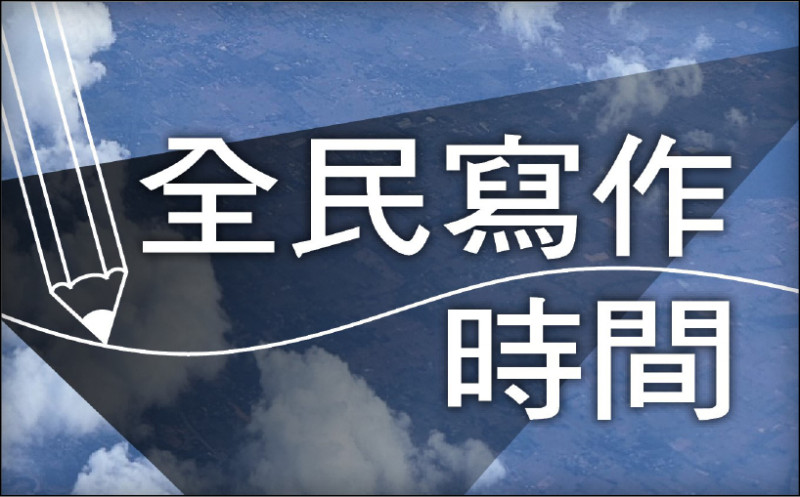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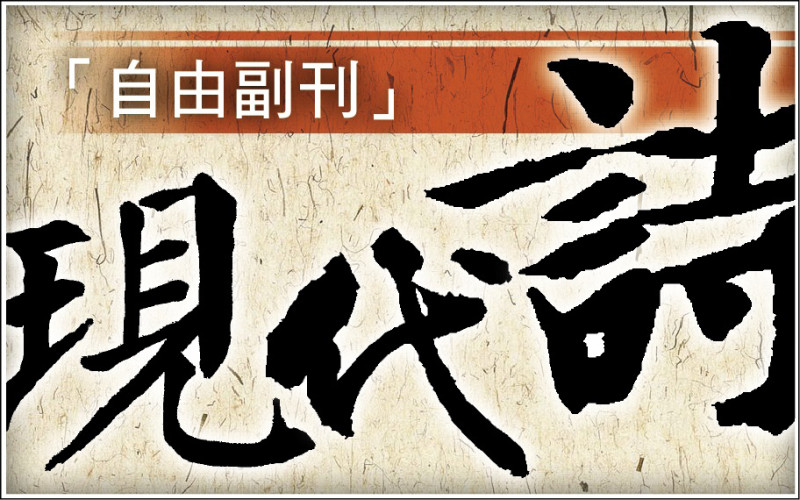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