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巫師之死
文.攝影◎林怡翠
看守整個部落安危的男孩,站立在地勢最高的岩石上,驕傲地望向遠方。那代表他長得夠大了,通過了嚴酷的成年考驗,終於可以看一看敵人的樣子。
他拿起用鐵箱子做成的弦琴,演奏那種使人頓時垂老的音樂,樂音在谷地裡轉著,像冬天時寒風刷過枯葉的聲音。
成人的世界原來是這樣孤單的,他想。畢竟,戰鬥不是隨時出現的。
他渴望戰鬥,部落裡的老人說,戰鬥才是男人的背骨、發亮的肩胛。
石洞裡,酋長和長老們正在議事,他們並肩坐著,然後捧起一碗酒輪流喝著,表示彼此關係的忠誠。那酒是用小黃豆製成的,酸酸澀澀的,像酒後的嘔吐。
彷彿誰說過,那是成人世界的威嚴和權力的味道。
1
我在一個叫巴索圖文化村的地方遇見了這個半熟男孩。與其說他像個英勇的獵人,他卻更像一個旅人。他的音樂使我想起童話中的吹笛人,把所有的孩童都帶走了的,應該就是這樣祥和卻帶著憤世的歌曲吧。
他站在陡高處,第一個看見敵人,卻也第一個被敵人看見。
然而他卻不是真的。他只是在這個後種族隔離和後部落社會裡,一個需要工作,而不得不在文化村裡角色扮演的現代男孩。還有酋長、長老們,以及那個坐在茅草房屋前的石凳上,為人占卜的巫師,他們都不是真的。那種嚴肅和煞有其事的模擬,似乎有些可笑,但捧著殘存的文化記憶的精神,卻又是可敬的。
問題是,戰場早已不再,沒有誰再可以用長矛,刺穿敵人的胸膛。這個年代既不流行用血來廝殺,誰還會關心什麼英雄?誰用什麼手段贏得了勝利?無論是男孩、老人,真的或假扮的,卻總都是孤獨的。
從文化村離開時,我忍不住推想剛剛受酋長之邀,而喝下的那一口酸啤酒,也許是巴索圖婦女將黃豆放在口中咀嚼,再吐出來使其發酵而成的,胃開始有些難受。
車子穿行過偌大的自然保育區,在高低起伏的人工道路上搖晃,周遭的草地和岩石炎熱得像要融出淚來。沒有任何一隻動物在這樣的午後出沒,這大地無邊,無聲息,竟像一座深遠而寂寥的枯城。
而這無伴無侶的古老文明,或許會到死都這樣安靜無語。
漸漸地,我的眼前被熾烈的陽光照成一大片的白,就像是從巫師手中幾個咚咚跌落的貝殼裡反射出來的。會不會那巫師其實是真的,就像男孩的音樂一樣,擁有進入人心的力量?畢竟,這天氣啊,猛爆得像一句巫師的詛咒。
2
從此之後,我對巫師這種身分產生了一種浪漫的情懷,他們結合了傳統醫療、心理諮詢甚至是社會溝通的功能,在一個與自然共生卻危險的生活方式裡,代表了人類這一方與萬物進行角力時,最靈妙的兵法。
而他們更是代表著部落時代的舊情感,和殘存的溫度。
我住的小鎮裡,就有一個婦人以巫師的技能,開設草藥、靈療的醫館,她聲稱可以為人們去除衰運、帶來幸福和財富、驅趕惡疾、保持青春,甚至還可以求子,或者使男人的生殖器增大、使性愛時間增長。
巫師們幾乎包辦了人類的所有欲望和所有的希望。
然而,從二十世紀末到這個世紀初,整個南部非洲卻陷入了滅殺巫師的恐怖和瘋狂裡。
據說在二十世紀末的短短十年裡,至少有兩萬人背負著巫師的名字,遭到激憤的群眾折磨至死。這些激進的青年開始成群結隊地指控他們的鄰居,或村子的老人使用巫術引來閃電,或者用咒語殺死他們的牛羊和嬰兒,人們把這些巫師嫌疑人,拖出來毆打、丟砸石塊、用刀子砍殺得支離破碎,或者放火燒死他們。
人們甚至發展出如何辨識巫師的方法,諸如眼睛的顏色、煮飯時炊煙的形狀,或者把老人的手塞進滾燙的熱油裡,試驗看看會不會出現魔鬼的痕跡。
這些對巫師所進行的可怕私刑,幾乎是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翻版,但卻發生在這個我們所生存的時代,這個我們所驕傲的,文明、高尚、優雅且注重質感的時代。
當然會有人說,那是因為非洲本來就是落後、野蠻和缺乏教育的。說這些話的人,多少還帶著些許慶幸,因為非洲距離我們是如此的遙遠。
然而,這個滅殺巫師的運動進行的時間,卻正好符合黑人民主運動發展的時程。第一個被檢舉為巫師,而遭到追殺的白人出現時,正好是1994年,曼德拉在全世界的喝采聲中當選南非總統,種族隔離時代正式宣告瓦解,美麗的新故鄉正在降臨。
(這就是我們人類自己,熱愛戰場和勝的歡呼,卻恐懼敗亡的孤單。恐懼向來遠比愛,更牽扯更迷戀我們的演進史。)因為對那個孤立和貶抑的年代充滿恐懼,如今,黑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再不要出賣靈魂、帶來詛咒的巫師或者白人,他們終於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仇恨和恐懼。
而仇恨和恐懼對他們而言,原是一種奢侈的特權。
滅殺巫師和民主投票一樣,竟只是弱者們一種防衛的方式,使自己能遠離魔的權威,鬼的統治。
於是,巫師死了。死的還有那個以血以肉搏鬥,無論生死卻還保存著正直胸懷的部落的時代。
3
恐懼幾乎主宰了全人類,貧窮、疾病和離棄全在惡神的眼睛底下,包括你我。
然而,當南非一個五個月大的小女嬰遭到強暴的新聞傳遍世界時,人們終於可以捏著鼻子,對遙遠的非洲所傳來的惡臭表示同情。不久後,另一個九個月大的女嬰,再度遭到六個成年男人的輪暴。
有社會學家說,強調男性英武的傳統社會,因為種族隔離而被摧毀,男人的勇氣和尊嚴遭到威脅,於是他們開始展開對女性的復仇,擎起勃然忿怒的性器官,如同擎起瞄準獵物的槍。
更有人說,那因為他們迷信和處女性交,可以治癒他們一無所知卻致命的愛滋病。而原來這些展現出主宰者和粗暴面目的男人,其實是哭泣著、發抖著或脆弱著怕死的。
僅存的巫師和巫醫們紛紛跳出來呼籲,靠少女救命的迷思毫無根據,然而,誰都知道,就算是巫師真的都死光了,暗黑的力量仍然無所不在,魔鬼和天使始終都同住在我們心裡,那個最虛弱,最不堪一擊的地方。
那是被遺棄者的,鼠臉的,對生命的貪戀。
4
然而,我對巫師的美麗幻想仍沒有消退。
畢竟,在那個純真的,依附著大自然的時代裡,是巫師們從母親的身上,接產了可愛的生命,也是巫師們,送走了每一個死亡後的魂魄。
他們本來就應該比任何人,更懂得關於人類膜拜和恐懼的事。
在巴索圖文化村的出口處,最後一間的草屋,展示的是近代巴索圖人的住宅,除了床鋪、電爐這些現代化的用品,他們仍喜歡用強烈誇張的色彩來裝飾他們的家。在藍色畫著黃色花紋的外牆邊,坐著兩個抱著鼓和破風琴的歌者,唱著歡樂的歌曲歡送我們。
他們是原來站在岩石上那個看守少年,和為人占卜的巫師,我花了幾分鐘才辨認出來。
而他們的樂聲不再有一點點的悲傷了,而是手舞足蹈的開懷和歡慶。我忍不住再三地向他們揮手,他們擺著頭回應我,彷彿說了:所有的戰鬥,都有勝敗的時候,而無論勝敗也都有遺忘的時候。只有分離時,仍想著一首歡悅的歌,才能使我們真誠地面對自己的恐懼。
我想,巫師和他的時代,將始終存在於某個角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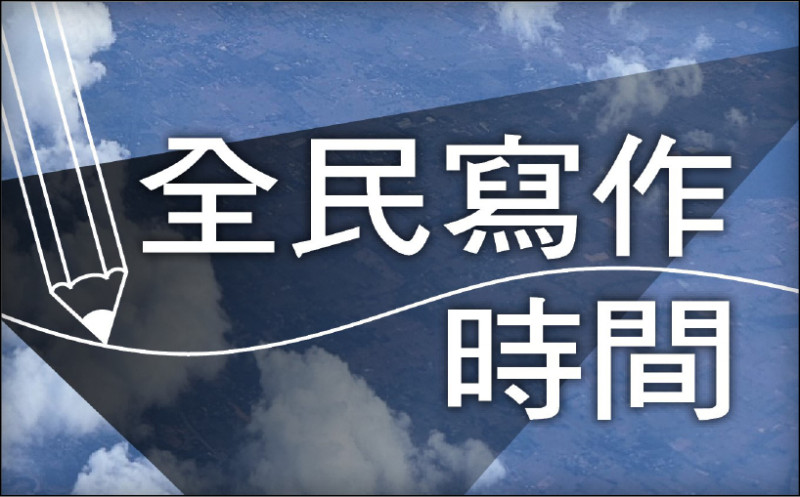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