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在相逢時說再見
文.圖◎張立曄
腳踏車
想起米貞,就想起大學時代騎著腳踏車載她穿過自強隧道的情景。第一次把一份友情放在腳踏車上,穿過車來熙攘的漫長隧道,感覺這台從故鄉嘉義運來的腳踏車第一次負載了別人的重量。
大學一年級,人際關係尚未展開,封閉的生活就是課餘時分關在住處畫畫。美術是我異地生活的一口孤獨糧草,只能一個人咀嚼反芻,一個人消化排洩。美術,跟這台腳踏車一樣,在這段青澀的時光陪著我,然後有一天,米貞坐了上來。
轟隆隆的自強隧道不曾減低彼此半吼半叫的說話熱情,汗流發痠的雙腳也不曾放慢那腳踏板的轉動。我用盡全身的力氣,踩著這象徵青春嘎嘎作響的兩顆齒輪,握緊手把往前衝。
星橋美術社
星橋美術社是教室城外的一座小小水塘。文藝青年紛紛在這裡跳下水,裸泳,抓彼此懷抱理想、尚未被馴服的風騷尾巴。
星橋美術社,與旁邊的文研社、電影社聯結成更大的水潭,可以嬉戲,可以捕捉藝術溪蝦,划詩之小舟。
米貞當時是美術社長,短髮、及腳踝的長裙,嚴肅認真的風格成為我們的大姐大。中午時分,幾個朋友常拎著便當來社團鬼混,偶爾我們會蹺課騎摩托車一起到淡水、淺水灣玩上半天,到士林夜市吃一碗蚵仔煎和花枝羹。有時,在群山靜謐的操場上數著星光,交談心事點點。米貞坐在夜晚的草地上,把齊豫的〈橄欖樹〉吟唱得宛如和風般輕靈地拂過聖潔純淨的青春草原。
我們共同擁有的這塊土地,可以用詩來做地基,電影做磚頭,美術做水泥,建蓋屬於我們的文學院。南京東路的影廬和國際影展是另一個必修學分,楚浮、小津安二郎與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替代了學校的課本,把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生放入我們的心中播放。
瑞明山莊
沿著外雙溪邊的小路,穿過一扇青苔滿布的小門,就會走進青鬱相思林的小三合院,這裡就是瑞明山莊。米貞在這裡度過她青年時期的幾個寒暑,即使畢了業,外出工作,依然捨不得這片綠色林園。簡約素樸的山屋是她的理想住所,涵蓋了她對於自然、植物、創作的生活哲學。
綠色是米貞的顏色,是暈染到她生命版圖的色母,是自世俗退隱的簡樸之心所需要的慰藉靈藥。與樹林的朝夕相處,典雅、安靜的氣息悄然落在她的畫裡、居家擺設與音樂品味中。樹林間一口綠色鼻息,沿著山路散步到鄭成功廟,我們呼吸著這份寧靜,走山閒聊,與遠方的山巒吐納對話。某些個夜晚,聞著從她電鍋裡散發出的蒸蛋、鹹粥香味,巴哈的大提琴無伴奏溫暖了這個小斗室。
出走
再來就是遷徙的季節了。
屏東老家的舊糖廠,米貞的童年地圖以這裡為首都,羅織黑輪攤和鱔魚麵店等散落的板塊,連結成心中故鄉的原型。而外雙溪的一草一石,十九歲的電影從這裡開拍,三合院、朋友、初戀的場景一一剪輯收音,存放在青春的檔案室。接下來,她要去法國,用法文寫她人生的新小說。
記得那是一個和風徐徐的夏日午后,我們一起坐在外雙溪的大石頭上,望著潺潺的溪水自腳邊流逝,米貞說她要去法國,她一定要去。我在想,是不是有一條宿命的線拉著她與法國?還是未來的輪廓已經在遠方像雲朵一樣慢慢堆積,變成厚厚的雲層,下起了鄉愁的雨滴,模糊了住在台灣的視線?堅定的心情刮起告別的風,拂向瑞明山莊上方的相思林,而唧唧的夏蟬依舊唱著小斗室的學生之歌,只是原鄉與異鄉的行囊搬來搬去,留下滿園的回憶,寄生在青苔上,爬上了三合院的老磚牆。
法國
之後,我到台東當兵,米貞則飛到了法國的中部小城克蕾夢飛虹。書信往返取代往昔的互動,一封封手寫信件,隨著我部隊的調移逐日逐月多了起來。相隔天涯的筆談更能交流彼此生活的悲歡,鏟起的冬雪足以餵養異地的寂寞。半年後,米貞搬到巴黎,依然孤獨的塞納河畔,未知的因緣站在命運的橋頭眺望。
幾年後,她奇蹟般地邂逅了未來的丈夫,巧遇了原生藝術,後來又因異鄉的旅驛愁悵而開始寫小說。
來來去去的遷徙、奔走,洗煉出她對無常人生的感悟,對於錯身而過的每一個人,都能洞見到瞳眼的深處。米貞的小說,就從悲憫之心下到社會底層,同理於站在命運之弦上的每一個小人物,傾聽掉落、沉淪、無助的人類哭聲。這一根弦,捲起大大小小不同的浪濤,即使奮力抓住漂流而來的救贖浮板也會被浪狠狠帶走。從這裡看,米貞的悲劇小說純然是宿命的,是荒謬的,是迷宮人生的具體現形。她筆下的人物都在找尋愛與慰藉,撿拾溫暖與幸福,雖然她又不經意地透露:緣分是刑具,愛是問號,關係是痛覺,但眾生們依然用力往前泅泳。
北京
離開巴黎,搬到北京,與台灣相屬同一個母體文化的中國社會更方便米貞去觀察五千年文化下的世間百態。她的〈橋墩下〉這篇小說,就寫出了中國版的孤雛淚,描述貧窮農村父病母離流浪北京街頭兩姐妹的蜉蝣童年,是赤裸暴露中國農村與兒童慘狀的社會學控訴。流浪的姐妹被萍水相逢的一對行乞的老夫婦收留了,提供橋墩下簡陋棚屋裡的破塑膠布那一絲殘破的溫暖。在這繁華城市外的荒地僻角,老人與小孩活得如蟲蟻般,地痞流氓和警察又不時在摧毀這已幾近赤貧的非人生活,小說的結尾,老婦在無奈中擱下這對茫然望著北京暮色的小姐妹。
這是她小說中最殘酷悲慘的一篇,完全的絕望,對於最無力無助的草芥階級,社會機制提供的不是照顧而是加害,像撲殺害蟲毒瘤般逮捕消滅。這篇小說的悲慘越過了人性可以提供的救贖底線,把讀者硬生生地拋擲到荊棘之地刺得滿身是血。
返鄉
北京的生活,逼使米貞更貼近社會實相的眾生場域。法國時期作品中殘存的一絲浪漫希望都被扒得精光,命運變得更像一個無聲尖叫,分離變得更接近老年的歎息,無奈被迫哽在嘴裡,連悲傷都太深沉,沉到深海茫漠的心底,而難以辨識。
四年後,她告別了中國回到台灣,和小說〈返鄉〉中的主角王柏慶一樣。然王柏慶返鄉面對的是年輕愛人的老去和死亡,以及唯一兒子難以相認的撕心之痛;而米貞的返鄉,則必須重新省視在一輩子的候鳥人生中降落下錨的強烈需要,並對自身理想與台灣土地做安身立命的規畫與對焦。就像她自己所講的:「因各種原因而離開家鄉的人,在異地流轉、迷途,終至散佚,而能回到少小離開的老家的,漂泊的心果真就能從此安頓下來了嗎?」漂泊,是不是已經被身體內化,變成她最常唱也最不願意唱的流浪者之歌?再幾年,她又得離開台灣,到法國或到世界其他的國家去,然後我們又會開始寫信,用文學藝術繼續把我們繫在一起,說著我們慢慢變老的理想殘念與未及實現的夢,我們會繼續向前走,繼續勇敢與生活。
也許在她離開台灣的那一天,我會到機場送她,擁抱道別的最後時刻,就如同〈返鄉〉的結局一樣:她會看見相思林下的那間小三合院,然後飛機就騰入雲中,不知道是因為雲,還是淚,她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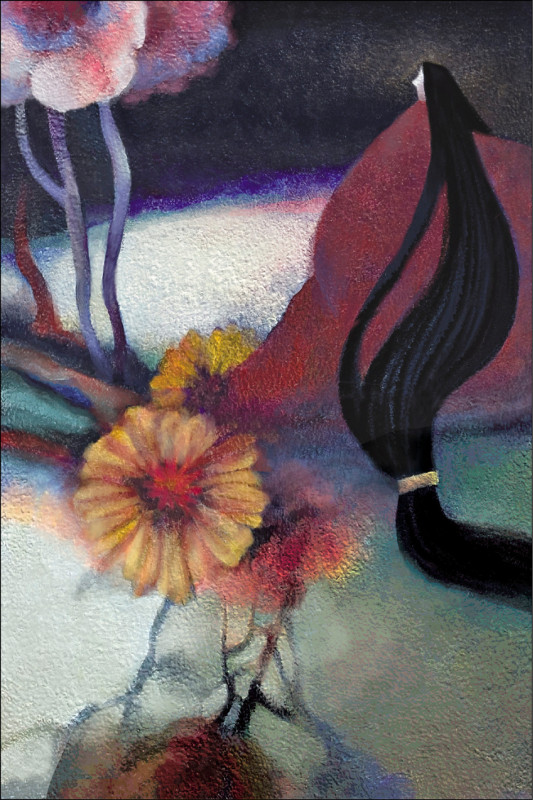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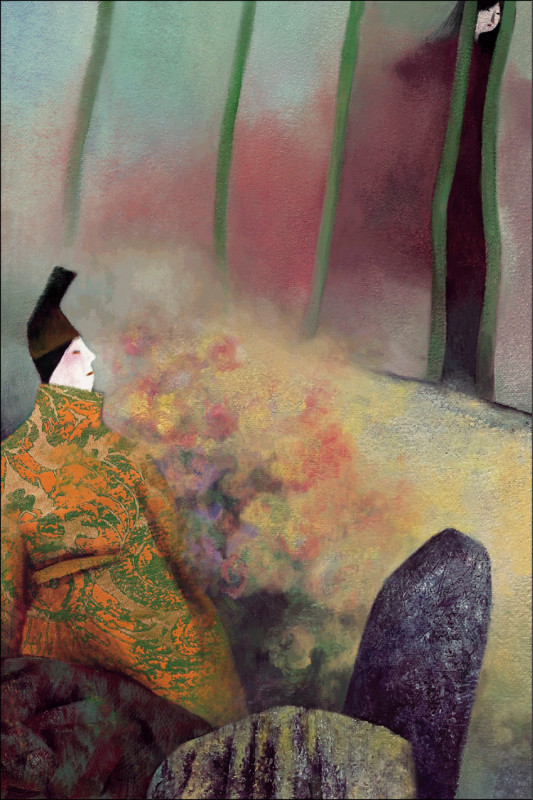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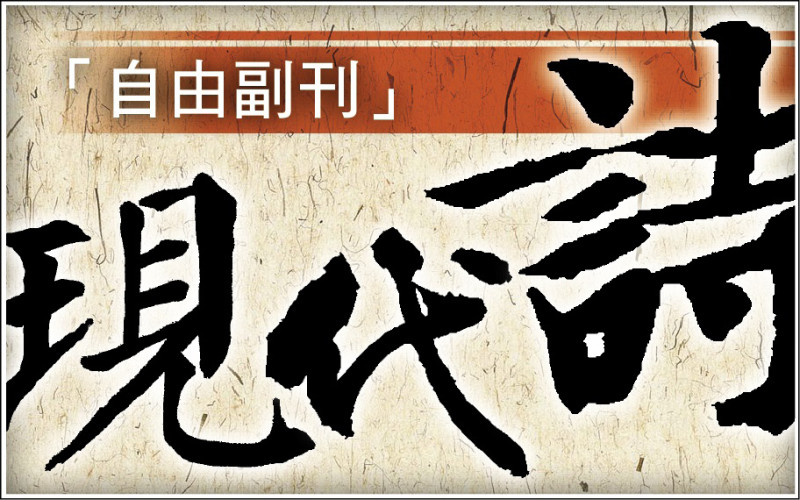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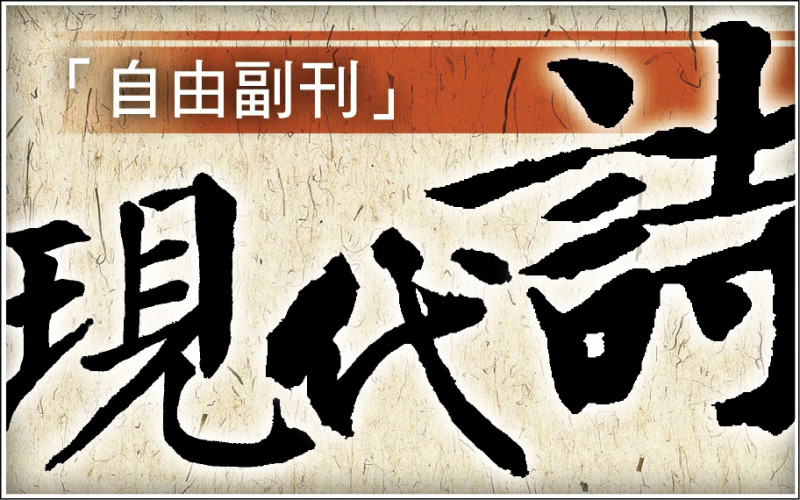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