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書與人】歷史暗湧下的文青性愛 - 楊照談《1981光陰賊》
 小說家楊照》。
(記者胡舜翔╱攝影)
小說家楊照》。
(記者胡舜翔╱攝影)
專訪◎翟翱
 新作《1981光陰賊》。
新作《1981光陰賊》。
小說家如何介入歷史──無論是對現下此刻不滿,或與已逝之物對話,一直是台灣文學迭出的主題。在楊照(1963-)的「百年荒蕪系列」之前,我們看過70年代的鄉土小說、80年代的政治小說,乃至企圖重塑整個歷史的大河小說等,甚至楊照本人也有《暗巷迷夜》等作。歷史,有無可能換個方式再說一次?或者,再說一次,歷史將會如何?
置主角於歷史中的一場實驗
「百年荒蕪系列」第一本《1981光陰賊》,以文學青年與已婚女子的禁忌之戀為主題,側寫80年代的台灣文學氛圍,寫得其實「很不歷史」。然則,正是要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得以了解楊照的苦心──擺落不得不的、大寫的、政治的敘事後,花火四濺的「小說自由」。台灣歷史,何以「荒蕪」視之?楊照表示,由於外婆家族的二二八受難經驗,面對歷史,他往往背負「龐大的壓力」,試圖追問並找出答案。過往他有許多「嘗試」,但深入挖掘後往往是一片空白。面對此境,楊照說:「認了,沒有了,然後呢?」
沒有了,於是有小說。楊照繼而說:「面對台灣過往,那是一個沒有觀眾的現場,至少我們都不是觀眾,所以只能自行拼湊,給出一個可能發生的事。」可能發生的事,便是將人物置於該時空下的推理實驗。小說中,主角是大學聯考前夕的高中生,他的情人是文學雜誌社的編輯;前者父母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恐共氛圍(1979年中美斷交),後者母親是台灣家父長制下的被壓迫者。「可以說,裡頭的情境搬離那個時刻就不會發生,其內在的獨特來自那個時代的局限。」楊照正是以這個角度切開歷史,讓我們一窺其可悲的血肉。
面對歷史的荒蕪之時,楊照在此系列的開山作中,卻選擇激出滿溢的愛欲;男女主角的靈肉交融、耳鬢廝磨,在小說中有不小的分量。楊照以為,兩者實是分不開的,在那個時空下,愈想「繞過」的東西只能愈強烈地迎頭撞上;在許多不可做之中,愛與被愛是兩人僅有的療慰──儘管是在歷史巨人的注目及其陰影中。
楊照說,那個時空有太多限制,而人們總「不小心」去做,做時又產生無比的絕望,再以各種方面迴避之。因此,那種擺盪在是與非,沒有即沒有,有了便是絕對的姿態,讓故事裡的情欲顯得更為猛烈。愛欲與世界(一個充滿陷阱的世界),因而交織成一種奇怪的螺旋──房間裡的性與房間外的政治,互為表裡,一來一往,更顯色情與複雜。「我想刺激大家思考歷史是什麼。」楊照如是說。
重返文學給人力量的時代
除此之外,文學(或者說詩)在小說裡是兩人關係的共通處與第三者。我們看到男女主角在對話中臧否作家,甚且,男主角因為同學的詩才而顯露妒忌。又或者,女主角在小說裡給了男主角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男主角選擇以詩來答辯。詩,在此成為男主角的「語言」。楊照說,詩是當時男主角抗拒世界的方式,表達無力表達的部分,以回應女主角感情;一方面承認現實(的挫敗),一方面延長這偷來的時間中的感情。
「詩對主角是種信仰,對現在的文青來說則是種嗜好。」楊照這樣說。小說一開頭,男主角說:「我很好,只在那小小的一瞬間,稍微跌了一下,只有那一瞬間,不在我想好的情況內。」「我成功了,我很好,我本來就說了這一天我會很好,不會有事,不會有任何事。」對此,楊照說,這本小說其實是在解釋男主角如何做到「不被打倒」的故事,不被現實打倒,不被家人打倒,不被無以名之的愛情打倒……而他倚靠的,正是詩。因此,這本小說也是為了向楊照年少時所信仰的文學致敬。敏銳的讀者當可從文本裡嗅出許多似曾相識,那是楊照的《迷路的詩》了(巧的是,男主角在小說開頭也迷了路)。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見到楊照一層一層包裹的理想,在逝去的時間,一無所有的歷史中,有做為創作者的他訴諸小說的理想;在小說之中,有主角對愛情的理想,對失敗於現實的愛情而投身文學的理想……
既背離又對話文學史
「百年荒蕪系列」化整為零,從1901年到2000年,時間線拉得如此之長,讓我想起了大河小說。然而,楊照表示他刻意迴避大河小說的寫法,希望讓不同的人物、故事在台灣歷史的時間線中「竄來竄去」──用不同觀點來建構一個時空,拉遠來看則能感受到台灣的變化。楊照接著表示,他並非否定大河小說,甚且他用了自己的方式來向大河小說致敬──在〈女兒時〉裡有位帶身世之謎的百歲人瑞,其實來自李喬的《寒夜》。
歷史小說在過去被認為是建構台灣魂的重要手段──許多人打倒中心,然後再立一個中心。楊照把歷史時間切成薄片,對於「中心」,又有什麼思考?楊照的回應相當直接了當,讓我這個問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我以為大家已經不用再找中心在哪了,而是改問中心外剩下什麼?另一個中心不可能是建構台灣的方式。或者換個方式說,得到自由之後,再鞭打已去的中心沒有意義。」
有太多故事可寫,何須中心?這是楊照思考「百年荒蕪系列」的心得了。因此,他跳脫直接對決時間歷史,跳脫歷史、年份的束縛,採取另一種方式探討那惶惶的威脅。時間不再,歷史荒蕪,小說續之。「我很樂意並且享受沒有中心。」楊照說。
除了向中心告別,並試著不回望它(回望即承認其存在),嫻熟台灣文學史的楊照在寫小說時,也時時警戒,以免重複他人走過之路。以《1981光陰賊》為例,這部小說較之相同時空的台灣文學作品,是我們熟悉的鄉土文學時期,但裡頭人物彷彿存在一個切片式的背景中──自有脈絡,既無關外界又與外界呈現幽微的對位關係。楊照選擇以一段禁忌之戀呈現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灣家父長制已受到挑戰,出現裂痕;「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正興;文學仍足以召喚人們,之於社會仍有力量。
對此,楊照說,他找到了打開歷史的自由視角,並且「不想跟過去的文學史一樣」。他以寫1945到1947年的小說為例,同樣的題材太多,寫歷史創傷不免流於既定印象,他自己在寫這時期的小說時,選擇的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人尋。楊照說,戰爭末期有許多人不知所終,專門找人的人尋因此應運而生,以此為切入點,可以看見更多不同的故事。
為什麼再寫小說?楊照表示:「沒有理由寫小說,更顯出小說的必要,創作讓活著更有意義。」無論是將《1981光陰賊》視為自身性強的「場內小說」,或為翻案的歷史小說也罷,顯然,做為小說家的他找到了自身經驗在歷史記憶裡的位置。楊照說:「在我十七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那時候的情感、記憶,仍陰魂不散。」
不散,於是有了小說。或者說,正是由於小說,才讓記憶免於失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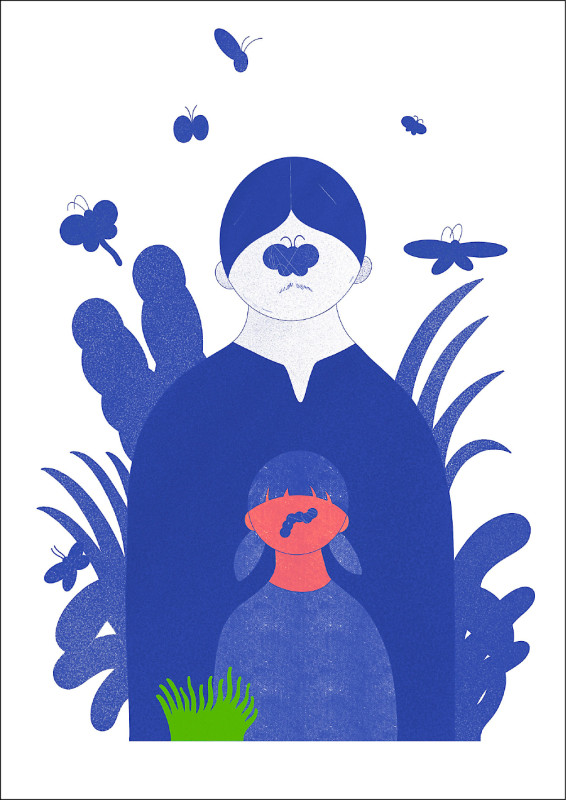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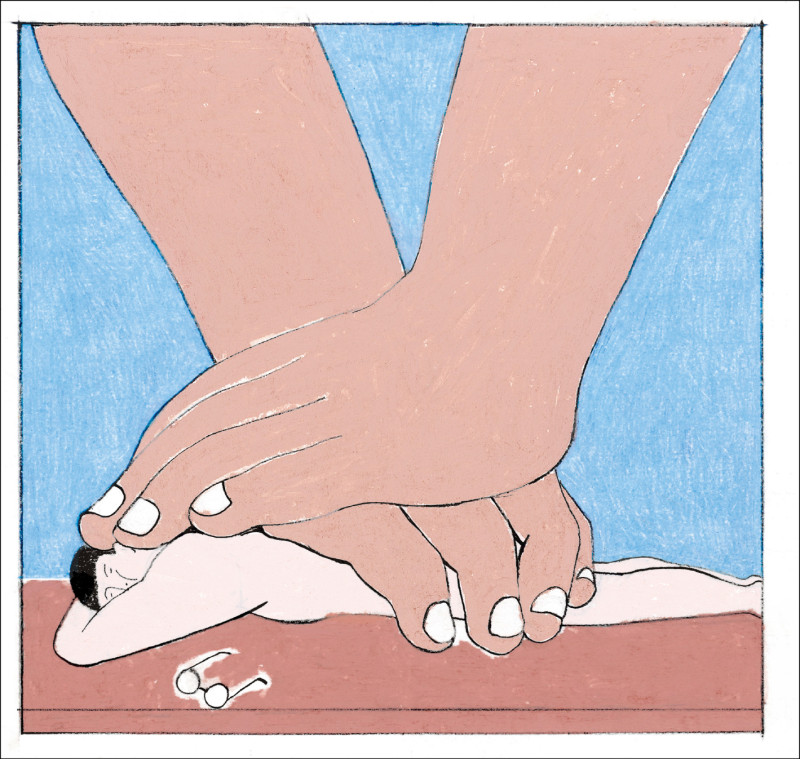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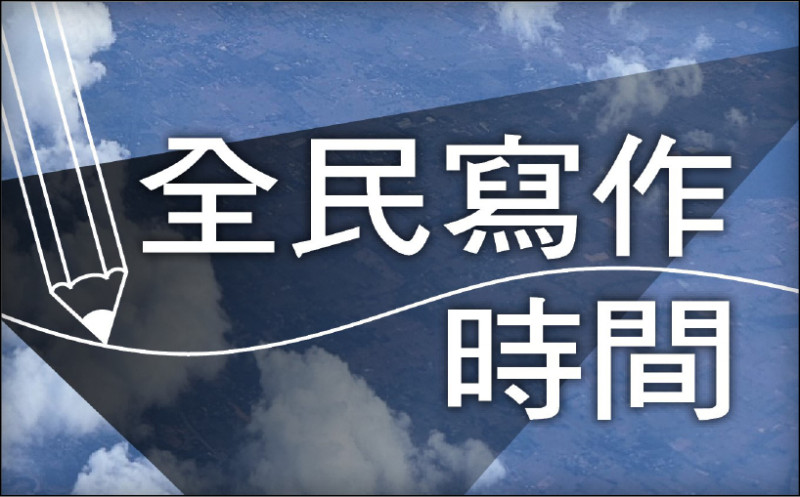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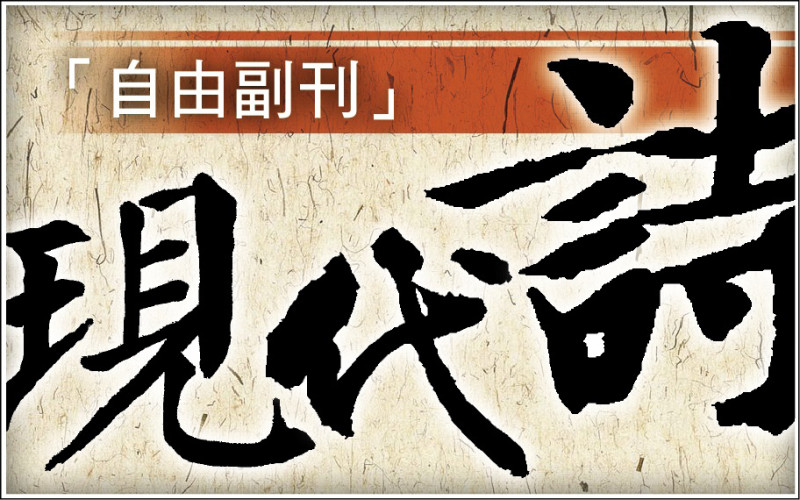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