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一手寫作,一手導演 - 林俊頴談紀錄片《我記得》執導
 拍攝《我記得》時的林俊頴,背後是朱家大門。(林俊頴/提供)
拍攝《我記得》時的林俊頴,背後是朱家大門。(林俊頴/提供)
編輯室報告:
 《我記得》拍攝朱家姊妹,左起朱天文,朱天心。(目宿媒體/提供)
《我記得》拍攝朱家姊妹,左起朱天文,朱天心。(目宿媒體/提供)
小說家林俊頴首度執導紀錄片《我記得》,拍攝對象是超過四十年友情的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小說家拍小說家,別具慧眼。今日刊出同為小說家的蔡素芬提問,林俊頴作答,暢談轉換於寫作/導演之間的心境種種。
《我記得》3月25日上映。
★★★
提問◎蔡素芬 回答◎林俊頴
一、讀者對俊頴的理解是散文和小說好手,也是專心於文字創作的作者,如今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紀錄片系列執導以朱天文、朱天心為記錄對象的《我記得》,接下這份執導工作立基於與朱家姊妹四十年的交情與熟悉,但對於初涉紀錄片導演,你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擅長的文字思考邏輯會運用在影像的形成上嗎?
這部紀錄片跨時三年完成,我得到最深刻的教訓是,影像與文字根本是兩個國、兩個系統,兩種不同的思考邏輯、生產方式與規格(直言之、成本與幣值)。寫作是一個人做有巢氏、燧人氏,一夕之間加入集體遊獵、採集,之所以可成,在於是侯孝賢導演的班底,拍攝過程因而形同自動駕駛,我得以專注在寫作與文學的軌道,看看以影像將二位傳主在這條道路走了四十多年的腳跡,能否立體且豐碩地呈現。影像是太過強烈的感官刺激,我以前的認知,將文字挪移、轉化到銀幕上,是被徹底推翻了。當然,澀滯漫長的後製時日,與製片、剪接的溝通,我將一己的想法與企圖一寫再寫,施工藍圖似的陳述,註解細節,文字還是最好用的工具。
二、在記錄朱西甯先生的《願未央》片中,你出現在某些畫面,而自己執導的《我記得》中也有你做為聆聽者的畫面,這些畫面中的你大都是無聲的。無聲有時形成一種張力,彷彿有一種介入的力量在貫串影片的進行。這種無聲的出現,是刻意的安排,還是表現了一種自然的相處模式?
有攝恐症的我不得不入鏡,唯一原因是必須做為二位傳主說話時的對象與凝視的焦點,螳螂捕蟬,愈是了解攝影機黃雀在後,我愈是得做個無聲的聆聽者。憾恨的是,前期作業我懵然不知攝影機的厲害,不明白可以躲得更遠更技巧。
三、
在執導過程,最大的困難點?解決這個困難點對你而言,有做為一個導演者的特別體會嗎?
紀錄片需要長期的守候與捕捉,亦即蹲點,又要被拍攝者卸下心防、坦誠面對、不至於不耐煩,尤其寫作是一個人極為私密的內心活動,影像化?叫河流改道,挾泰山以超北海,差可比擬吧。所以我非常佩服朱家人的真誠與勇敢,或是事無不可對人言、言無不盡的憨膽,幾乎毫不掩飾地讓拍攝團隊侵門踏戶,進入他們的生活現場,今年剛好屋齡整五十年的一戶尋常人家。因此這紀錄片若呈現了那粗礪的真實,不可易奪的樸拙,讓世人直面以對,那正是朱家的家風與個性。至於能否拍到/捕獵到,剪接時見真章。
我保存著昔年讀傳播理論的一本教科書,其中有蒙太奇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普多夫金(V. I. Pudovkin)的名言:「剪接是電影藝術的基礎。」攝製前期一如《紅樓夢》前八十回,默契甚佳的團隊,熱鬧好玩,一旦開始剪接,便是不斷的撞牆、摸索、調整,計較未及一秒或幾個格數的差別與效果。基礎才是最難的門檻,其堂奧之深闊,不亞於我們書寫的初稿到N稿。
四、在《我記得》中,取景點相當遼闊,曾遠到東京,哪個或哪些畫面的形成最印象深刻?最費工夫或最令你動容的部分?有沒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去到東京福生市的胡蘭成故居,對照老照片,片瓦不存,今是一大棟整潔彷彿沒有人息的公寓樓房;走在去羽村的河堤,三月底的天氣冷冽,櫻花尚未盛開,也是二傳主年少與胡同行的啟蒙之路。我們找到、拍攝到了什麼?沒有,如同追尋箭跡。尤其在剪接大神之前,一切意義的還魂再生,影像的創造,剪不進去就是剪不進去,沒有終究是沒有。因而我深深感念文字書寫的仁厚與大量。
五、在這部片中,最初預設的方向跟最後的成果是否有差異?什麼因素影響最後影片呈現的效果?
從發想到完成,是一路刪減的過程。《我記得》辛亥路的朱家第二代終究只能是以二位傳主為核心的光桿牡丹。沒辦法,影像的物理性限制,分秒必較。沒能剪進去而精采、令我大大遺憾的,比那二小時的版本多太多了。
六、文字創作和影像創作,各自的魅力所在?如果還有機會,會想再拍片嗎?紀錄片中,朱家姊妹用了「一生一藝」來詮釋對文字創作的執念,你在長期投注熱情與專注度於小說創作,也本本皆佳作的成績下,是否有同樣的執念?有想過如果你是被拍攝的對象,如何形塑自己的創作形象?
我絕對不敢小看影像及其魅力,那同樣是得投注一生修煉的技藝。借王家衛《一代宗師》的台詞,「我沒有時間了。」參與這紀錄片,因與朱家二代人是同輩同業,是超過四十年的老友的因緣際會,僅此一回。而且我的孤僻,甚享受獨處的自由自在,在在與影像作業的模式不相容,寫作才是我的洞窟,此後我怡然做一個好觀眾足矣。而且我是福婁拜與卡爾維諾的信徒,「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關於我自己的生活,我一句真話也不會說。」不只是想,我要做到,所以,嘿嘿,我絕對絕對不要成為被拍攝者!
七、你2017年出版長篇小說《猛暑》後,尚未推出新作,是因拍攝紀錄片延緩了寫作進程嗎?如今影像的實際拍攝經驗,會不會影響你對文字創作的思考?尤其你的文字風格一向繁複細緻,錘鍊功夫自成一格,這種對文字經營的風格與影像美學,你認為有關連嗎?拍完《我記得》,你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找不到值得寫的並且寫得慢,純粹是我自己的因素。正好三年的寫作空檔浸泡在這紀錄片,借用名嘴的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今想來,我獲益最多的好像與影像沒有直接關聯,再一次了解侯孝賢導演的話,他始終關注的是人,其處境其狀態,人與人的互動與氣味。因此識得的各路好漢,讓我開闊了眼界,希望來日有幸成為寫小說的養分。紀錄片完成日,自由了,我不禁大聲歡呼,寫作是莫大幸福,一個人擁有無限的自由。宣傳行程結束後,我是該收心,專注寫新小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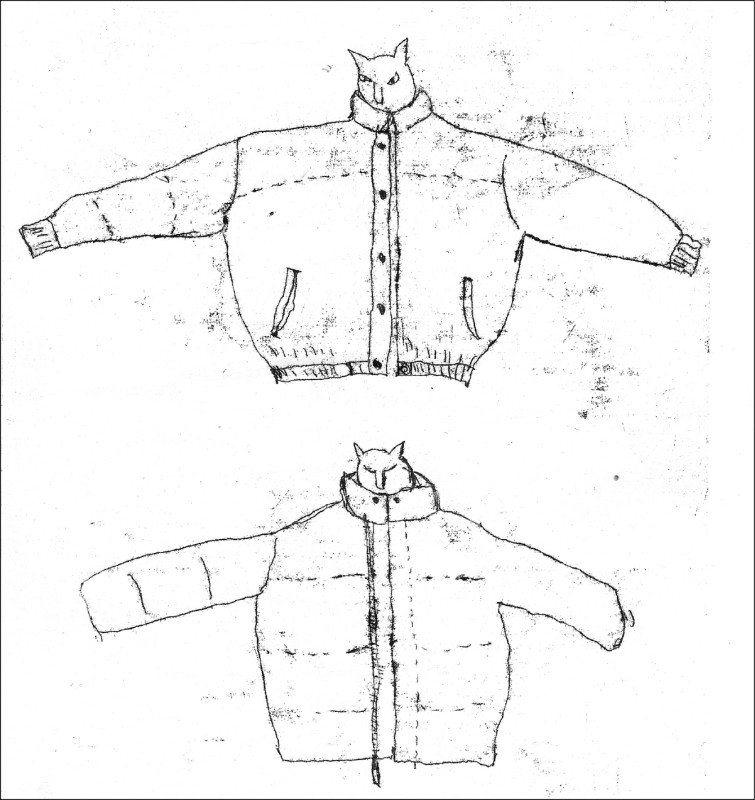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