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林薇晨/彼女日誌 - 2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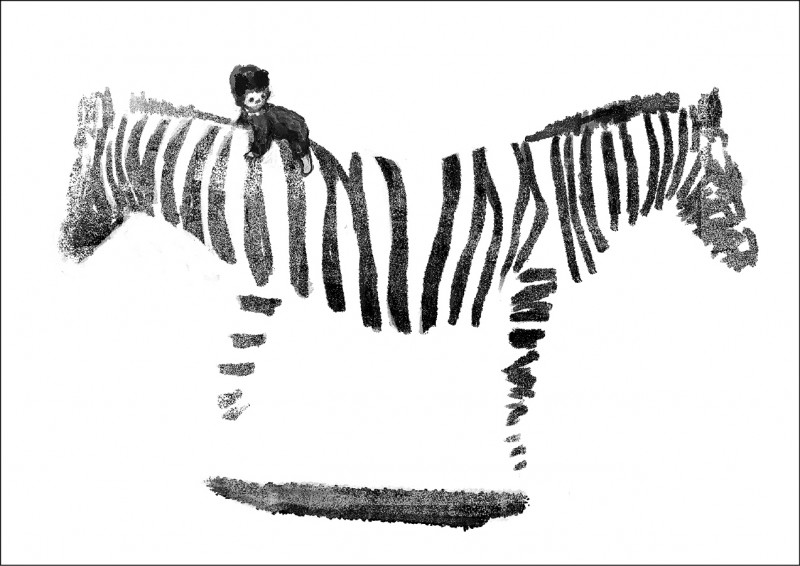 圖◎郭鑒予
圖◎郭鑒予
◎林薇晨 圖◎郭鑒予
儘管如此,為了獲得更多愛的證據,我不斷蒐集各種無法相信醫生的疑點。我從醫生的Facebook連結到妻子的帳號,妻子的動態時報上每個週末都有一家三口快樂團聚的貼文,照片裡的醫生看起來是一個最盡責的模範丈夫,模範父親,貼文底下一片欣羨留言。顯然只有我知道他們婚姻出了問題。忍受許久,我終於詢問醫生這些貼文和照片究竟是什麼意思。「究竟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我在信件裡責難不在身邊的醫生。「你不知道我們總是在吵,不然也不會分居了。」醫生在回信裡解釋。然而,為了維持孩子需要的婚姻,醫生也不希望每次回去就吵,可以和平過一天就這麼過一天,就連任由妻子發布這些快樂的照片,也是他保有和平的方式。她不願意親朋好友知道兩人婚姻的隱私,他也認同,因為那些好奇的眼神與探問對於孩子將是一種傷害。於是我說服自己,確實只有我知道他們婚姻出了問題。醫生的婚姻是一幅繪畫,就近觀察,方才發現那畫作不過是一組拼圖,早已給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碎片,裂痕蔓延。然而,即使是碎片,到底還是拼湊成一個宜於對外展示的模樣了。
獨自在台北的假日,我近乎自虐地查閱妻子貼出的美滿照片,反覆聽著宋冬野的歌曲:「斑馬,斑馬,你睡吧睡吧,我會揹上吉他離開北方……」醫生離開台北回到台南,離開台南回到台北,周而復始。我知道醫生這樣奔波其實也很辛苦,可是在體諒他的同時我也愈來愈不快樂。不像還是純粹的筆友時那樣無話不談,漸漸我總覺得我們之間充滿了祕密。然而,醫生告訴我多一點台南的事情,說好的,我不想聽,說不好的,我怪他根本把我這裡當成婚姻諮商室;醫生告訴我少一點,我倒又覺得他一味瞞我了。我愈來愈不快樂,於是愈來愈需要來自醫生的愛的證據,只要確定他是在乎我的,我不在乎他離不離婚。當然我也知道為了孩子他是不會離婚的。我說服自己,這一切不過是因為他把孩子放在他自己前面的緣故。孩子優先,因此孩子需要的家庭優先;他排第二,因此他需要的愛情也排第二,連帶將我的順位也往後移了。
返回台南的假日,醫生似乎不怎麼刮鬍子,星期一早上來到台北,他的鬍渣總是密密點點爬滿了下頷,彷彿不過兩天的時間他就蒼老憔悴了許多。終於見面,他緊緊抱著我,親吻我,新生的鬍髭刺刺地扎在我的唇邊。和醫生的接吻十分輕盈,吹泡泡一般,嘟起嘴是營造一顆泡泡,親一下,芬芳的泡泡就迸破,發出啵地一聲。不快樂的我隨著這些泡泡一次又一次綻裂,一次又一次消失殆盡,於是我和醫生又可以言歸於好,重新度過平安無事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五──當然星期五只有半天。吹泡泡一般流利飛散的七日復七日。
有一個週末,我在餐廳工作時,給碗盤的碎片劃破了左手的無名指,血漬乾涸了,我也就不去管。醫生回來後,看見那道傷口,仔細地幫我塗上藥膏,又包紮了一圈OK繃,看起來就像戴著結婚戒指一般。
就像愛的證據一般。
●
在日文系的課堂上,聽見「彼女」(かのじょ)一詞,我總會分心地想起自己的身分。這是日文裡的「女朋友」,也是「她」的意思。一個永遠的女性第三人稱。
和醫生交往的日子裡,我常常疑惑自己是不是被愛的,是不是被騙了。每個星期,醫生在台北的時間比在台南還多,可是放假他一回去,我又感到那個婚姻其實堅固無比。也許他們的分居就只是分開居住,並不代表兩人各過各的,各愛各的。然而,每當我這麼一想,立刻就要譴責自己又在負面思考,醫生都這麼努力讓我相信他了我還一直不相信,未免太過為難他了。我說服自己,我愛醫生,就要愛他所愛的一切。於是生活就這麼繼續著。我們的通信繼續著,我的中文系和日文系的課程繼續著,我母親的戀愛繼續著,醫生的婚姻與婚外情繼續著。
我們就這麼繼續著。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對我而言漸漸不重要了,我只要可以留在醫生身邊就好。也許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離開,而是保有離開的意願和能力。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轉身,留在這裡就不那麼痛苦,因為是自願的緣故。
在進行這段戀愛的時期,我一次也不曾和學校或餐廳的朋友提過醫生的事情。我受不了別人可能提出的質疑或建議,我自己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就夠了。我母親知道我最近常常和某某見面,並且外宿,但是也從來不深究,到底她忙她的工作和戀愛就已經自顧不暇了,根本沒空管到我這裡來。也是她的一貫作風。我與母親之間向來保持著一種互不干涉的尊重,彼此都信任對方是獨立成熟的,可以自己將自己的事情處理得很好。因此我們一直沒發現對方在三角關係裡受苦著。
又是一個目送醫生返回台南的星期五。我從車站回到小公寓裡,母親已經下班在家了,憂傷地對我笑道:「陪媽媽出門走走好不好?」她開著她的歷史悠久的香檳金福特汽車載我,沒有目的地,沒有特別要去哪裡,只是直直地開下去。車廂裡的氣氛十分凝重,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睫毛,鼻尖,唇,我偏頭看看母親的側臉,一道眼淚慢慢滑下來,以一種汽車漫遊的速度。「媽媽被騙了……」她的聲音忽然顫抖起來,但是仍然非常節制,不會到嚎啕的程度。母親在三角關係裡受苦著。電話那端的那人,另有一個小女朋友,被我母親發現了。我看見母親如此痛苦,眼淚在臉頰上橫橫斜斜,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告訴她,其實我就是另一段關係裡所謂的小女朋友。
坐在這個熟悉的副駕駛座上,我微微降下車窗,冬天的高樓風從縫隙不斷竄進汽車裡,在我與母親之間寒冷著。我要和醫生分手。我在心裡暗暗決定,我要和醫生分手了。醫生不能離婚,我可以離開,美麗而堅強地轉身,如同母親一直對我示範的那樣。我抽了一張紙手帕,幫駕駛座上的母親擦眼淚,按著,拭著,她的眼淚漸漸停住了,我知道她向來是不需要我擔心的獨立女子。不獨立的一直都是我。
和醫生提過幾次分手,我們總是無法徹底結束。知道我想要走,他總是就讓我走,可是我的手機不斷跳出訊息。「對不起,讓你委屈了,我愛你是真的,想膩在一起也是真的……」我不點開。「其實我早就明白你有天會離開,是我自己沒有勇氣放下現在的生活……」我不點開。「我知道自己沒有資格要求你留下來,可是……」我不點開。「希望你讓我陪著你,直到你找到心愛的人,我會一輩子祝福你的……」我還是不點開,可是整個人已經依偎在醫生的懷抱裡了。比起分開,和好總是比較容易的。這樣想斷又斷不了的情境,不知道重複過多少次,到了最後,我也知道完全是我自己想要回來的。我害怕沒有醫生的孤單。我也害怕沒有我,醫生自己一人在他的婚姻裡孤單。我簡直想要成為醫生的醫生,拯救他,治癒他。我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因為醫生讓我覺得自己之於他如此重要。這份重要的感覺,也許就是我們的關係裡,最令我上癮的成分。
又是一個和好的夜晚。在醫生的老公寓裡,我們躺在雪白蚊帳裡的大床上,兩人之間的不愉快的氣氛總是沒能立刻散去,睡眠與夢都籠罩在新娘頭紗一般氤氳的憂愁裡。半夜一時甦醒,我轉身看看躺在我旁邊的醫生,卻發現他一人在那裡無聲地流淚。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醫生脆弱的淚水。我克服不了保護他的念頭,一時之間無比內疚,遂也哭泣了起來,不能確定我們之間到底是誰錯,到底是誰錯得比較多了。我感覺身體裡的臟腑一件一件巧克力一般融化,心臟肺臟肝臟腸子和腦袋,一件一件都是如此濃稠而苦澀。溫熱的眼淚,巧克力一般,涓涓滴滴,從我們兩人的眼睛裡流出來。
醫生看我這樣難過,忽然決定還是分手比較好了。非常奇怪,醫生想要分手,我就覺得他是真心為我著想,反而更加捨不得了。我和醫生說不要,幾乎是乞求地不要。「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讓我學習一下好嗎?」我低低對醫生道。醫生聽了我的話,只是皺眉露出無奈的表情,眉心兩道懸針紋裡積累著的大人的年歲,也禁不住這份孩子氣的執拗。我相信只要再努力練習一下,我就可以接受這些痛苦了。當一個情婦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
醫生分居數年了,但是仍然保有已婚身分,但是卻和我交往著,但是又不能公開,那麼我的身分其實也就和一個情婦差不多──也許在大眾的眼光裡就是情婦。我將情婦的耐心應用在日復一日的生活裡。我漸漸明白,在這世界上的許多婚姻,也許都是妻子與情婦分工合作共同維持著的。如同妻子,情婦也一樣是一個婚姻的參與者,只是她們一人在婚姻裡面,一人在婚姻外面。妻子照顧家庭小孩,情婦負責談情說愛,顫巍巍立在天秤兩端。
天秤兩端是台北與台南,醫生區隔嚴明的愛情與親情。這個週末,醫生沒要回台南,可是我們也不能一起度過,因為妻子要帶孩子來台北遊玩,做為補習班考試成績優異的獎勵。當然是住在醫生的老公寓裡。為了迎接北上的妻子和孩子,醫生幾天前就開始打掃屋子,我也幫忙一起收拾,整理我留在這裡的大小東西。
和醫生過著半同居的生活,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日常用品散落在老公寓的各個角落。醫生拿來一個小紙箱,略帶抱歉地道:「要先暫時收納一下你的東西……」他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到處蒐集我的牙刷、漱口杯、洗髮乳、潤髮乳、乾髮巾、睡衣睡褲、裙夾衣架、外出的拖鞋,一件一件裝進小箱子裡。我也找出我的髮圈、牙線、護唇膏、防曬乳、指甲油、手環、手機充電線、除毛球機,一件一件放進自己的包包裡,預備等等帶回小公寓。我的東西其實不多,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細細小小的物件,稍微錯眼就有可能遺漏。大抵收拾完畢之後,我還是擔心可能有什麼沒注意到的針頭線腦,兀自環顧四周檢查了起來。小沙發安全。小衣櫃安全。大床墊安全。小爐台小冰箱安全。小鞋櫃安全。儘管這是個不甚寬敞的屋子,也放滿了我們朝夕相處的回憶。我的眼睛每看到一處,就看見我和醫生曾在那裡互動的身影。
視線再回到醫生身上時,只見他伏跪於蚊帳裡的雪白大床上,手持一支黏貼滾筒,移開我們的枕頭和棉被,來來回回地黏拭微小的髮絲。我的髮絲。我不化妝,不會留下唇印;也不噴香水,不會留下氣息。可是我的頭髮太長太長,一根陌生女子的髮絲出現在這老公寓裡,可以洩露的事情太多太多。我站在一邊觀看醫生這樣勤快打掃,就連一根髮絲也不放過,暗暗佩服地想道:「原來談婚外情是要謹慎到這樣的地步。」在這間我們度過無數日夜的老公寓裡,醫生一點一點刪除我的生活痕跡,終於我就像是根本不曾在這裡存在過。
一個念頭倏忽閃過,我想到醫生筆電裡我的那些寫作草稿,也趕緊提醒他。於是我開了筆電,將此前留存的文件檔案一一複製到隨身碟裡,再一一刪除,並且不禁佩服起自己的仔細。現在我就連在醫生的電腦裡也不曾存在過了。
為什麼我必須被隱藏?因為我們的關係是祕密。為什麼我們的關係是祕密?因為醫生不方便離婚。為什麼醫生不方便離婚?因為醫生希望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為什麼醫生希望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因為這樣孩子才不會在成長的過程裡崩壞。我再次確認自己這一整套精巧的邏輯:孩子幸福,醫生才會幸福,我才幸福。確認之後,沒有異議。
乾乾淨淨的老公寓。醫生將小箱子封得緊緊的,搬到權充陽台的小窗台上,關上窗戶,拉起窗簾。我從頭到尾都注意著不要流露難受的表情,因為我已經答應當一個最盡責的情婦。整理完畢,醫生臉上一個大功告成的滿意的微笑,我們都鬆了一口氣。
上班時間到了,醫生要前往復健診所,我要返回小公寓。出了老公寓的大門,我們走在一起,快到診所才轉換成一前一後,默契十足地。我在診所對面的公車站牌停下來等車,看著醫生的背影繼續走,過了斑馬線,上了階梯,進了診所。公車還有十幾分鐘才進站,我坐在候車亭裡一邊聽音樂一邊滑手機,百無聊賴。忽然一個紙袋出現在我眼前,抬頭一看,是醫生買了一份草莓奶油吐司讓我當早餐。愛的證據。只要有愛的證據我就可以再留在這段關係裡,再留在這段關係裡一下下。我知道醫生不是不愛我,他只是只能以他的方式愛我。
冬天的冷風颼颼吹著,醫生解開脖子上的羊呢圍巾遞給我,讓我圍著禦寒。我將圍巾纏繞在脖子上,幾乎遮覆了整副口鼻,於是可以聞見圍巾裡的,醫生身上的氣息。天空的小雨一滴一滴下下來了,這裡一串,那裡一串,斷斷續續的刪節號一般。醫生就這樣維持著兩個乘客的距離,佇立著,陪了我十幾分鐘,直到我的公車進站。我知道醫生不是不愛我。
●
醫生妥善地分配他對兩邊的愛。這世界上有各式各樣難以言詮的關係,我和醫生的關係只是其中一種,並不特別奇異,也並不特別複雜。自己想通以後,這段不斷送往迎來的關係,也給我微妙的安全感。醫生總是會來,也總是會走,總是會走,也總是會來。我只要關注我們之間快樂的部分就好。因為有不快樂的存在,快樂才更令人快樂。
耶誕節剛好在星期五。幾天以前,醫生就傳訊息問過我:「星期五一起過耶誕節,再陪我去牽車好嗎?」醫生要換一部新車了。這天中午醫生下班後,我們一起去咖啡店吃午餐,有生菜沙律,有水煮章魚義大利麵,也有草莓磅蛋糕。只有下午不必上班的星期五,醫生才能盡情享受義大利麵這類富於蒜香或醬汁的菜肴,因為他向來擔心口齒受到薰染,問診時刻影響了病患的觀感,儘管每次吃完午餐他必定要認真刷牙。吃完午餐,我和醫生交換耶誕禮物。醫生送我一張素描,是他根據我的照片畫出來的,畫作裡的我看起來非常像我。他總是說「畫人最難」,這次可以畫到連本人都認可,想必也是下過一番功夫。我想像他趁我不在老公寓時,獨自琢磨著照片和圖畫之間的相似性的表情,不禁悄悄地笑了。我喜歡自己在醫生眼睛裡的模樣。透過醫生的眼睛,我才真正看見我自己。
這天的天氣非常好。整個晴朗的冬天是項鍊墜著的一朵白金玫瑰,舒爽,乾脆,可是放在齒間咬嚙可以感覺到它微微的冰。我們的座位前方就是一面寬大的窗戶,窗外樹叢上盛開的玫瑰,在陽光照耀下,也像一朵一朵放射光芒的白金玫瑰。美麗的景色在窗戶外面漸次鋪展開來,放眼望去盡是無窮樹,無窮花,整面窗戶幾乎就是汽車的擋風玻璃。
醫生要換一部新車了。離開咖啡店,我們坐公車到台北郊區的汽車展售中心。醫生的復健診所就在老公寓附近,上班不必開車。平常我們出門,總是騎機車坐公車坐計程車。週末他回家則是搭乘高鐵,也從不需要汽車。因此這次換車,當然還是放在台南的家裡,假日他可以載著家人出遊,平時就給妻子用來接送小孩。醫生妥善地分配台北和台南的耶誕禮物。
在汽車展售中心裡,醫生和業務先生一起檢視購車合約,林林總總的條款。我坐在醫生身邊,旁聽他們討論諸般我不甚明白的細節,小茶几上三杯黑咖啡冒著嫋娜的白煙,只有我一口也沒喝。來到汽車展售中心我才知道,原來地下室就是個停車場,許許多多名貴的汽車都停放在這裡。業務先生帶領我們走下一道窄仄的旋轉樓梯,找到醫生預訂的汽車,又陪醫生上路試駕一程,沿途介紹車上各式功能,冷氣怎麼調整,暖氣怎麼調整。「台南的冬天很暖和,暖氣大概用不太到。」業務先生笑道。我坐在後座,窗外的風景不斷飛逝,無窮花,無窮樹,整條街道筆直簡潔得如同一句誠摯的「耶誕快樂」,沒有任何轉彎或埋伏。回到停車場,業務先生準備幫醫生拍一張人車合照。我不知道這個步驟的用意是什麼,也許是證明車主已經當場交車,也或許就只是一種慶祝儀式,畢竟買車總是喜事,買車的日子也是紀念日。業務先生待要指導我和醫生怎麼站,怎麼擺姿勢,然而我悄悄避到了一旁。他不知道我是不適合入鏡的。
醫生的新車是一部墨黑的汽車。我對於汽車的知識太過缺乏,並不能分辨那車來自什麼廠牌,屬於什麼款式,儘管我知道那必定是個不錯的牌子。我想到母親開了十數年的福特你愛她,她總是想換而沒有換的香檳金色汽車,忽然好奇醫生的新車裡,駕駛座和副駕駛座的遮陽板上是否都有化妝鏡。拉下來一看,果然兩邊都有小鏡子。台南的妻子開車載著孩子時,也許也會在等待紅燈的片刻,對著駕駛座遮陽板上的化妝鏡,補一補臉上的粉底或口紅。
也許醫生的新車也是一部你愛她。
●
新車離開地下停車場時,台北的天色已經昏黃了。我是這部車,第一個乘客。醫生輕輕旋開了音響,播放著他最喜歡的專輯《安和橋北》。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靜靜聽著宋冬野的歌聲。失語一般的兩人。汽車登上了高速公路,我們就像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旅行。歌曲一首輪過一首,終於還是來到了〈斑馬,斑馬〉。宋冬野在喇叭裡憂傷地唱道:「斑馬,斑馬,你回到了你的家。」每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和醫生總是要回去各自的家。
學校的期末考週快到了,我必須準備中文系和日文系的考試。在中文系一門語言學的課堂上,我學到關於大腦語言中樞的知識,布洛卡區主宰語言的表達,韋尼克區主宰語言的理解,這些區域受損就會導致失語症,影響日常的聽說讀寫。儘管我們學的不過是最基礎的部分,想到我和醫生共享著同樣的復健醫學知識,我便覺得又更理解他一點,理解他做為一個醫生,對於孩子的身心健康的重視。
坐在副駕駛座上,我看著醫生的側臉,一如每次我在母親的汽車上,看著她的側面的輪廓。紅燈時分,醫生也轉過頭來看我,他的臉龐如此憂鬱,深邃,即使面對面也有一種遠眺的感覺。我望進醫生的眼鏡,眼睛,像是透過小小的窗戶窺探花樹掩映的山稜。他的眼神堅忍如青山,那長長的睫毛便是簇擁山景的密花,親近而柔軟。如此美麗的一個人。
醫生將汽車停在小公寓樓下。我下了車,整個白晝的晴朗和煦到了夜晚陡然失溫了,我不禁摩擦雙手取暖,又用雙手捂住嘴巴,呼出熱氣蒸蒸手。大約是因為熱氣的緣故,我的眼眶忽然溼潤起來,無論定期實踐過多少次,我始終無法習慣目送醫生回家這件事情。那時距離我和醫生真正分手,還有好幾個季節。在那之前,我們每次的短暫分開彷彿都是一種預演,為了終將到來的,最後的道別。從含淚的眼睛看出去,整個世界茫茫一片,街邊的車燈、路燈也暈散出一圈一圈的虹彩。我有一種失去醫生的不安,可是隨即又有一種古老的安全感,不過兩天而已,下個星期一我們又要見面了。降下車窗,醫生微微笑道:「再見。」我也微微笑道:「再見。」這樣日復一日重複著,循環著,幾乎看不到盡頭的關係,大抵也就是一種永恆了吧?
醫生的車子回轉離開我的身邊,漸行漸遠。我的心痛的眼淚停不下來。忽然手機震動不迭,是母親打來的電話,接起來,她在那端含笑問道:「你要回家了沒?今天是耶誕節,晚上要不要一起去逛百貨公司?」我忍住哽咽的聲音,只說好啊好啊,等我一下。
黑色汽車遠到已經看不見了,我還站在原地默默望著車流,直到滿天亮起每個路口的紅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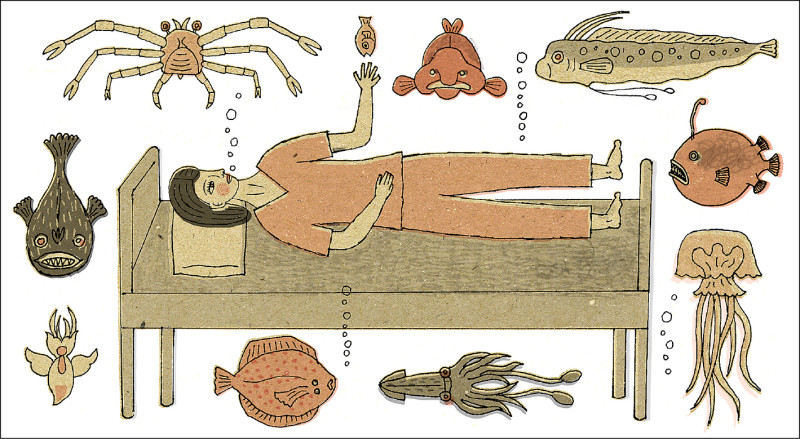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