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陳蒼多/瞧,這本書
 圖◎顏寧儀
圖◎顏寧儀
◎陳蒼多 圖◎顏寧儀
W.H.奧登(W. H. Auden)是20世紀偉大的詩人,與W.B.葉慈和T.S.艾略特鼎足三立,但奧登的後世聲名有超越後兩人的趨勢。
我無能翻譯奧登的詩集,但我記得早在五十年前就譯過他的散文〈閱讀〉一文中的幾則雋語,登在報紙副刊。在〈閱讀〉的文前,奧登引用G.G.李奇騰堡的名言「一本書是一面鏡子:如果一匹驢子攬鏡自照,你不會預期出現一位使徒」,令我印象深刻。
2023年是奧登去世五十週年,我譯了他的散文名著《染工的手及其他散文》(以下簡稱《染工》)之中的三個部分〈序曲〉、〈染工的手〉和〈納希修斯之井〉,自成一書,上述〈閱讀〉一文就是第一部分〈序曲〉中的一篇。
奧登在《染工》中喜歡以片段式的雋語方式寫作,他也編了一本四百多頁的格言雋語集《某個世界》。有人把他的《染工》和德國大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哲學語錄相比。奧登在《染工》中所展示的,不僅是文學創作的智慧,更是哲學的深博洞識。
奧登對格言的定義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染工》的〈巴蘭與他的驢子〉一文中說,「格言的趣味並不是在於內容,而是在於表達內容的特殊方式。」我們在閱讀《染工》一書時可以趁機一窺奧登是以什麼方式經營他的格言雋語。
回到奧登在書中的〈閱讀〉一文。他在此文中說,「閱讀就是翻譯……一個很差的讀者就像一個很差的譯者:應該意譯時卻直譯,應該直譯時卻意譯。如要學習在閱讀上獲得成果,學識雖然很有價值,但卻不如本能重要。有些偉大的學者卻是很差的譯者。」多年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提到「學識」在閱讀中不如「本能」重要。
既然奧登提到「閱讀就是翻譯」,我就想到閱讀與翻譯的另一種關係。我通常是在翻譯中閱讀,或是,我是用翻譯取代閱讀,當然會同時享有翻譯與閱讀的樂趣。單就翻譯的樂趣而言,當我發現,同一篇(部)作品我的翻譯不如別人,我會深自檢討自己技不如人,以求進步,反之,如果我發現別人的翻譯不如我或有誤,我會暗中竊喜。
事實上,我就發現,中國大陸的一位譯者把《染工》中的一句話譯錯了。在《染工》第二部分的〈詩人與城市〉一文中,奧登在正文前引用《曖昧的七種形態》一書的作者威廉.燕卜蓀的一句話:…Being everything, let us admit that is to be/something,/Or give ourselve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的翻譯是「……讓我們承認,成為最重要的人,就是成為具重要性的人,/或者就是假定我們自己是無過失的人……」。中國大陸的那位譯者則譯成「……讓我們承認,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什麼,/或者讓我們受惠於這種疑問……」其中的關鍵是在於對原文中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的正確了解。
再回到書中奧登的〈閱讀〉一文。奧登在文中說,「在文學中,人們喜歡『俗』勝過『無』,就像人們喜歡雜貨商的葡萄酒勝過蒸餾水。」我認為,這句話為「君子之交淡如水」下了註腳,但也許不然。
在同文中,奧登說,「有一種涉及到文學的惡,我們絕不能視若無睹……那就是語言的墮落。作家不可能發明自己的語言,而是要依賴他們所繼承的語言,所以如果語言墮落了,他們一定會墮落。但是關心這種惡的批評家,必須攻擊這種惡的源頭。其源頭不是在文學作品中,而是在於一般人、記者、政治人物等等誤用語言。」
21世紀已經走了四分之一,奧登在20世紀的這種文學語言墮落說,也許值得作家、一般人、記者,尤其是記者和政治人物,再加檢視。
接著,《染工》中的〈寫作〉一文也頗有可觀之處。奧登說,「當一個明顯很笨的人告訴我說,他喜歡我的一首詩,我會覺得好像我扒了他口袋的錢。」也許奧登意在諷刺笨人,或者故作謙虛,但我只覺得這種幽默很冷。
奧登在同文中說,「最偉大的作家無法看穿一道磚牆,但他跟我們其餘的人不一樣的是,他不會建一道磚牆。」這記冷箭不知會傷了多少作家的心,但也許不會傷到同為作家的奧登自己,因為他可能是在自嘲。
《染工》第二部分的第一篇文章〈行、知與判斷〉是奧登被聘為牛津大學詩歌教授的就職演說,頗具奧登之為詩人的簡短自傳成分。我們從文中得知,讓他走上寫詩之路的所謂第一個「師父」是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奧登也在文中提到,某位教授朗誦英國古詩《貝奧武夫》讓他很著迷。他又在文中表示,W.B.葉慈一首詩中的某些詩行「很愚蠢」,20世紀的三大詩人之間免不了有王不見王的情結。
在《染工》第二部分的第二篇文章〈聖母與發電機〉中,奧登曾用面孔跟詩加以比較。根據他的說法,如果一個人的面孔,其對稱性一如數學那麼完美,那臉孔看起來就不會像面孔,而是像沒生命的面具。詩也是一樣,就算一首「英」詩是以五音步抑揚格寫成,但如果每行的每個音步都相同,則詩聽起來就會令人無法忍受。奧登有時會想,很多現代詩人及其讀者會厭惡正式的詩,「也許是歸因於他們把規則的重複和形式上的限制,跟現代生活中最令人厭煩和沒有生命的東西――修路鑽機、打卡鐘、官僚的規條――聯想在一起」。這個想法不知台灣的現代詩人以為然否?
在同樣這部分的第三篇文章〈詩人與城市〉中,身為詩人的奧登竟然談到政治,他認為政治爭論有兩種,即「政黨」爭端和「革命性」爭端,詳情不在這兒贅述,但台灣有意政治事務的人士和朝野兩大黨應該可以從中獲得啟示。
《染工》進入到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這」與「那」〉之中,有一句雋語談到希臘神話中的自戀者納希修斯:「納希修斯並不是因為自己的映影很美而愛上它,而是因為映影是『他的映影』。如果是他的美迷住他,則美在幾年後褪色,他就會自由了。」這樣說來,自戀者是沒有自由之路了?從「自戀」到「自傲」也許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奧登接著在此文中談到「自傲」:「自傲既不是可笑的也不是可原諒的,但是卻是所有罪中最致命的……」奧登也對此詳加闡述,有心的讀者幸勿錯過。此文中還有一句話極盡諷刺之能事:「寫文學懺悔錄的人是可鄙的,就像乞丐展示傷口來乞錢,但他們卻沒有像買他們的書的人那樣可鄙。」可真是把盧梭的《懺悔錄》及其讀者都罵進去了。
在第二篇文章〈巴蘭和他的驢子〉中,奧登花了很多篇幅論述「主僕」的辯證關係,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環遊世界八十天》、歌劇《唐.喬凡尼》、《魔笛》等全都上場,奧登可真博學。
奧登意猶未足,又在第三篇文章〈有罪的教區牧師〉中軋上偵探故事,在第四篇〈沒有自性的「我」〉之中以卡夫卡為壓軸。在前者之中奧登說,人們都認為,讀偵探故事是為了在幻想中滿足暴力或殘忍的願望,但他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相反的,偵探故事所提供的那種神奇滿足,會讓讀者幻覺到自己與凶手並沒有關係。在後者之中,奧登指出,卡夫卡要求好友布羅德銷毀他生前作品的原因,並非出於一種奇怪的精神自傲。奧登說,卡夫卡曾寫道,「寫作是一種禱告的形態。」而只要很真誠禱告的人,都不會希望禱告被第三者偷聽到。奧登的結論是,「也許,當卡夫卡希望他的作品被銷毀時,他預見到太多讚賞他的人的本性。」
奧登在《染工》一書中的寫作風格很像尼釆,但在片段的智慧雋語中迸出更多彩的火花。尼采膽敢把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為《瞧,這個人》,基於奧登把「自傲」視為最致命的罪,他也許會不屑尼采,但我身為文學、哲學的愛好者,願意充當打手,為這篇談論奧登的《染工》一書的文章,冠以「瞧,這本書」的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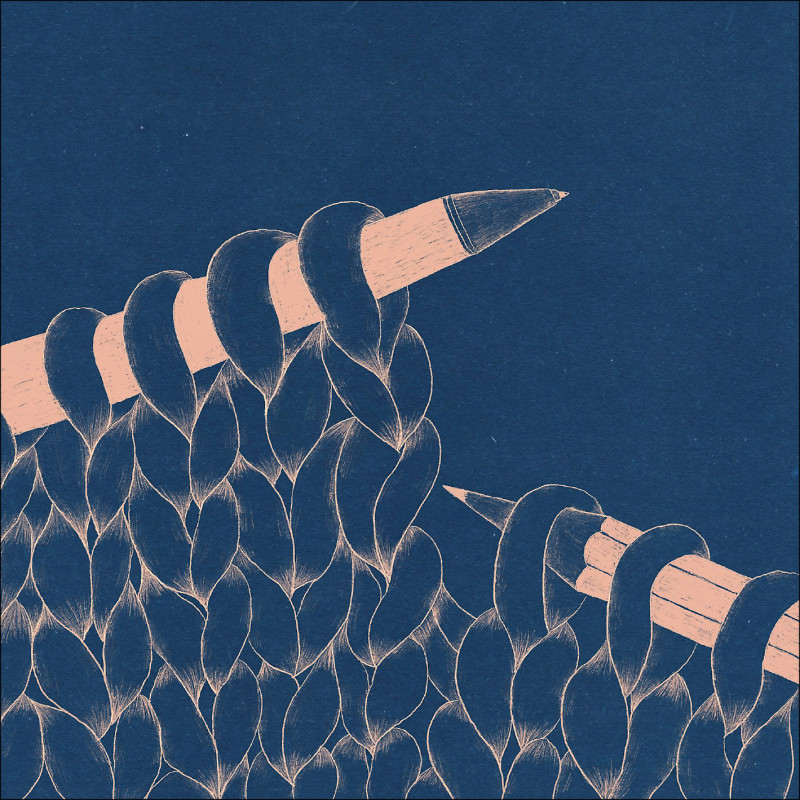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