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周志文/談賈科梅蒂
 賈科梅蒂銅雕作品《行走的男子》。
賈科梅蒂銅雕作品《行走的男子》。
(歐新社)
◎周志文
我對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有興趣是大學畢業之後的事,大約是1967年左右,當時我初在中學教書,在一本過期的《歐洲雜誌》上看到一篇江萌的文章談及賈科梅蒂死亡的消息,才知道有藝術界這號人物。後來知道作者江萌,其實就是藝術理論學家也是作家的熊秉明先生。
 賈科梅蒂青銅雕塑《貓》。(美聯社)
賈科梅蒂青銅雕塑《貓》。(美聯社)
《歐洲雜誌》是上世紀六○年代幾個從台灣到法國的留學生在巴黎創辦的,好像原始也有其他國的留學生吧,但以在法國的為主,當時主編筆名叫飛揚,本名馬森,曾醉心歐洲劇壇,之後寫過很多有實驗性與啟發性的舞台劇本,雜誌的另一位主持人叫金戴熹,與太太李明明都是台大外文系高材生,當時都在巴黎留學。金戴熹又名金恆杰,是名翻譯家金溟若的兒子,他有兩個弟弟都有名,大弟弟名恆鑣,是有名的植物學家,小弟弟金恆煒,曾做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後來又創辦過《當代》雜誌,曾風靡一時,三兄弟都有好文筆,都有著作問世。
 賈科梅蒂銅雕作品《傾斜的男子》。
賈科梅蒂銅雕作品《傾斜的男子》。
(法新社)
當我初讀《歐洲雜誌》時,跟他們幾位都不認識,雜誌有時在圖書館看到,有時在書攤自購,都不算當期,也不連續,但當時我對幾個在歐洲的窮留學生能在外國辦一份全中文直排的傳統中文刊物心生敬佩,雜誌上介紹的多是歐洲的人文藝術,也都是我喜歡的。隔了十幾年,我到大學教書,想不到竟先後跟上面說的幾位交好,我在幫三民書局編《三民叢刊》時,曾收入過金恆杰與李明明的書,後來幫北京的世紀文景主編《台灣學人散文叢書》,也請馬森、金恆鑣助過拳,第一輯的十冊中都有他們兩人的散文作品。
 賈科梅蒂。
賈科梅蒂。
(達志)
回頭來說賈科梅蒂。賈科梅蒂是一位瑞士籍的畫家與雕塑家,他在世的早期,歐洲藝術界印象主義當道,但他好像沒受到太大印象主義影響,後來立體派與野獸派崛起,對他產生了些作用,但依我看來作用也不算頂大,他的創作,受到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好像更大些,而存在主義是哲學上的一種流派,喜歡探討生存的本質,賈科梅蒂似乎一直在思考「人的本質」這類的事。他的雕塑有個特色,就是把人物(包括動物)雕得極為細長,面目上的表情不是全無就是十分模糊,看到他的作品,任何人的內心都難以阻止悸動,哇,好個削瘦又孤獨的人啊。他喜歡雕刻人行走的樣子,但他雕刻的人總孤伶伶的,這個行走的人不要說沒有朋友,甚至可以說沒有自己,他的驅殼被層層削去,只剩薄薄一層且千瘡百孔,甚至半點肌肉都沒有的骨架似的,空間呢,則是遼闊的、荒蕪的,行走的人一無憑藉,他還能向前行走,依靠的是不屈的意志嗎?
賈科梅蒂曾形容他雕刻的東西說:「真實彷彿躲在一層薄幕的後面,你扯去了,卻又有一層。一層又一層,真實永遠隔在一層層薄幕的後面。然而我幾乎每天都接近一步。」說明賈科梅蒂的雕塑是在尋找人存在的真相,他將人的形體一層層地削去,希望見到人更為真實生命的部分。他又說:「我每次工作,都毫無猶豫地把上一次所做的修削、刪改,因為我感到看得遠一步了,其實我也不過是按照當前的感覺去做。作品還是失敗的,終要被搗毀,在我自己卻總是一次勝利,因為我已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若干新的感受。」這些話有點似是而非,重點在「感受」,我特別感受他最後一句話的力道,他的創作常被自己搗毀,這證明他的藝術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這樣的藝術最為純粹。他的話讓我想起孔子也曾說過:「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學為人沒什麼不好,但總有幾分炫己的成分,為學或藝術一涉炫耀,就喪失了主體性了,它的意義就算沒有消失也會立刻變質,所以純粹的藝術家只為自己而創作。
 瑞士法郎百元紙鈔,正面是賈科梅蒂的頭像。
瑞士法郎百元紙鈔,正面是賈科梅蒂的頭像。
(shutterstock)
當然這是從賈科梅蒂以自己的角度看自己的作品,別人也許不是這樣看的,作品「自毀」不盡,總會讓別人看到,那別人看,自會發生詮釋的問題。沙特曾分析過賈科梅蒂,說他的作品有兩個基本的要素,便是絕對的自由及存在的恐懼。我認為這應該是兩個孤立的要素,否則既有存在的恐懼,何來絕對的自由呢?賈科梅蒂在他作品中,試圖將人的靈魂從他的形體之內抽離,但他沒法完全抽離乾淨,那行人仍然存在著也許更為敏銳的感覺,行人的感覺,或者說賈科梅蒂的感覺是什麼呢?套一句心理學的術語,那叫做「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
《維基百科》對這個名詞的界定是:「廣場恐懼症是一種焦慮症,其特徵是人們認為環境不安全並且不容易逃離而產生焦慮症狀。這些情況可能包括開放空間、公共運輸、商場,或僅僅是在自家外,在這些情況下可能會導致恐慌發作。」人在廣場上,益發覺得自己孤單與無靠,從而想逃走,回到自覺安全的地方,比較小也比較可靠的地方,外來的災害可由屋頂與厚實的牆壁擋著,大約是自己習慣窩著的家吧,原來賈科梅蒂描述的是這種感覺。
熊秉明做更深一層的說明,他說:「我們只知道這是一個人初始的慘淡形象,他連個性都沒有,性別都難辨,然而直立著,走著,惶惶地,瘦伶伶地,一無所有,單純得像一個符號。他可能有一個欲望,存在的欲望;只可能有一個恐懼,不存在的恐懼;只可能有一個問題,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他動搖在方生方死,將滅將起的邊緣。」這話說得迷離與弔詭,他又說:「奇異的雕刻,以人體為題,卻是反人體的,卻是描寫人體後面的主體――超人體的人體。遠離現世生命跳動的歡醉與悲苦,微笑與憤恨。生命的嚴冬:凋棄了一切花與葉、芽與果、翡翠與火紅,留下黑越越的枝椏的人體。」他說的也許都對,但也是有很多問題在的,賈科梅蒂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作品雕得那麼「難看」,為什麼把他人生的花與葉、芽與果、翡翠與火紅都捨棄掉,真相真如熊秉明說的「留下黑越越的枝椏的人體」嗎?賈科梅蒂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當然跟19世紀末之後歐美新興的美學思維有關,藝術不再標舉女性的柔美、男性的陽剛,畫花不待花之盛開,認為花之未開,或花謝、花落同樣也有美感,且可能有更深沉的涵義。不只藝術,文學上、音樂上也有同步的進展,文學不再強調和諧,也可強調人性的衝突,音樂掙脫「唯美」的牢籠,如荀貝格、阿班.貝爾格等,走向無調性、新和聲的方向,在在都在實驗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賈科梅蒂的藝術其實不求圓熟,一刀一鑿,也可說是他嘗試的痕跡。他是孤獨的思考者,也喜歡孤獨感,他呈現的廣場的恐懼,一邊是真的害怕群眾,一邊是害怕他自己在群眾中被肢解分離。依附群眾是無法維持獨立的,他有過被分離的經驗,他的作品試圖描述自己在被剝了好幾層皮與血肉之後仍存在的靈魂,正依附在幾根殘肢上勉力前行的狀況。
總帶著點恐懼的幽默感,他一刀刀的刻痕,似在探討人的最後支撐力來自何處,結果真正找到了嗎?好像沒有,至少找到的不算明確。賈科梅蒂的孤獨不是憑藉宗教,他的支撐力來自個性的倔強,有點像希臘神話裡盜火到人間的普羅米修斯,或者像薛西弗斯奮力推頑石上山,個人的意志高過一切,但過高的意志也同時昏迷了自己,使得自己眼光有時也一片茫然。
大約二十年前,我在休士頓美術館的一個戶外展場看過幾尊賈科梅蒂的大型雕塑,除此之外,我看過的作品都不算大,譬如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畫廊收藏的更有名的幾尊行人雕塑,都還不到一個人的高度,雖如此,看他的作品卻非常「費力」,儘管環境從容,在他作品前,你的情緒也都是緊繃的,他雕塑、油畫或素描,也都有同樣的「效果」,都會讓人感覺到透不過氣來。
藝術的功能有部分是讓人驚醒緊張,讓人憬悟生命中的某些特殊的消息,但這該不是它的終極目的吧,藝術的目的也許是讓人在更寬廣地認識一切之後,找到一條合適的路徑,可以更安穩且優美地處理自己的一生。賈科梅蒂的藝術也許達到了提醒的那一部分,另外如有需求,觀賞者可能要找其他來彌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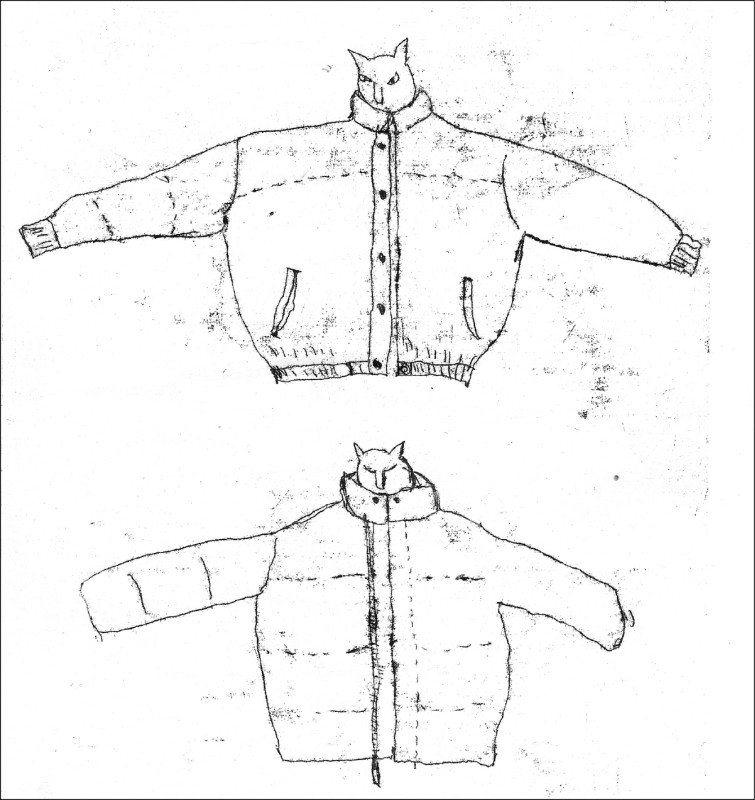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