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嗅覺
五感 小小說 五之一
編輯室報告
人有五感,以識世界。今天起我們將不定期推出【五感小小說】專題,邀請多位創作者以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知能,延伸出一個又一個殊異物語。
循著記憶的味道
◎廖輝英
空氣裡飄散著食物的味道。明確一點講,那是豌豆、綠色花椰菜、煎蛋,以及一小片白帶魚的混合。她甚至還可以聞出這些全是筷子和口水肆虐過後的剩菜殘羹。
不,不!她當然不喜歡自己的好嗅覺,老實講,活了這許多年,真實經驗告訴她:有好眼力遠比任何其他功能有用,這任何其他功能,特別是指嗅覺而言。譬如現在,如果聞不到這麼濃烈的氣味,該有多好!床在丈夫出去用餐前,已依她要求被調轉到七十五度將近筆直的坐姿。眼力正常的話,十五樓的視野,的確有可觀之處,起碼看看這個城市屋頂組成的海洋,也算一種樂趣──在她住進這間病房時,還擁有不算好,但勉強可用的視力。如今,她原本眼力較好的左眼,此刻正戴著開刀後的保護眼罩;而右眼呢?散光加上近視六百多度,眼前一切恍如一團一團的光暈,有物,但不知何物。
上午女兒帶來的富田柿滲透出一絲成熟的甜味。女兒結婚多年,看來還不甚懂得持家之道。一次買來十個,可買這麼幾近熟透的,能放幾天呢?她早已學會不開口批評的好習慣,人家好不容易來看妳、誰要聽妳教訓啊?即使是自己親生的女兒。
她維持這樣的坐姿應該將近一個小時。面向窗外,不是因為貪看什麼,而是躺得太累了,必須變換一下姿勢。丈夫去了很久,遠比她預期的時間長很多。他不挑食、吃飯很快,而且他出去的時間還不到十一點,人潮不多……他倒是十分放心把她獨個兒掠在這裡啊!碧芝蒼涼地哂笑著。雖然視網膜剝落不是重症,不過,經過這麼多年同住的日子,在她住院的時候,不免需要他的扶持;她不開口,難道他不明白?她不開口,是的。不知從何時開始,在丈夫習慣性用嘲弄的語氣否定她或揶揄她之後;在兩個孩子叛逆地經常性頂嘴之後,她私下費了好大勁,用坊間暢銷書所教的勵志方法不斷肯定自我,才免於憂鬱到崩潰的地步。然後,她學會在他們父子女三人面前不發表意見,並且開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去學標準舞──當然,所有人是指他們父子女三個以外的其他人而言。那是幾年前?應該是她四十二歲那年的事吧?也就是那陣子,她才意外發現自己有著更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嗅覺。
在熱舞時,舞伴的汗味混雜著他古龍水的味道,讓她驚覺自己還是個會心動的女人!而那也同時讓她發現:四十二歲的她,原來也依然能夠魅惑一個三十五歲的男人!在事態變得不可控制前,她便快刀斬亂麻換了舞伴。她最終明白,她所要的不是婚外情,而是別人,不!應該是丈夫的尊重。
她的轉變是否贏得什麼?答案是否定的,可是她已經不在乎了!丈夫到底只算個室友罷了。
下午丈夫回來時,她在空氣裡聞到台灣啤酒的味道。當他遞給她一杯溫開水時,一股眼淚的鹹味,淡淡在她鼻下散開。丈夫哭過!然後,更奇怪的是,她從丈夫伸過來的手和靠近的身軀,分辨出一種遙遠而似曾相識的味道。
除了囑他將病床搖下之外,碧芝沒有第二句話。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已完全放棄對他做任何要求了。
碧芝閤上眼睛,那股在丈夫身上聞到的味道,忽然像一道清晰的光在眼前一閃!十多年前父親過世前,整整一年,她一直嗅到父親身上那股說不出來的腐敗味道……那正是丈夫下午身上帶著的味啊。
傍晚時分,在新竹工作的兒子匆忙趕來,一進病房便問碧芝:「媽,爸也有什麼親朋好友住在這家醫院的重症病房嗎?」碧芝不動聲色,說:「你看到了?」「是啊,應該是個老太太,雖然很瘦,不過看那輪廓,很像以前爸的同事黃阿姨,只是她應該沒這麼老……爸推著她的輪椅在中庭散步……」碧芝覺得心猛地抽痛一下!那個女人!雖然形式上跟丈夫分手,十五年來卻一直長駐在他心中……碧芝平靜地說道:「我聽說她病了,看來病得還滿重的樣子。」向來少一根筋的兒子,一直不知道丈夫和黃之間的糾葛,當丈夫終於回到病房時,兒子問他父親:「爸,媽說黃阿姨也住這家醫院,她是什麼病?看您推著她的輪椅,好像很嚴重。」丈夫的表情,碧芝看不清楚,但她聞到一種類似被拆穿謊言的駭異。過了兩分鐘,他才訕訕地說:「我也是在中庭散步時意外遇見她……十幾年沒聯絡──」有解釋的味道,「已經沒救了,是直腸癌,就數日子……可妳怎麼知道?」碧芝冷笑:「聞到的。」她轉頭看窗,淚水的味道洶湧而至,但這會兒,分不出是他的還是自己的……
五樓太太
◎吳鈞堯
遇著訪客時,我如此報列地址:五華街,巷口是麥當勞,直走到底,見著赭紅色建築,就是了。大樓一百來戶,構成凹字型,橫向站立。車過重陽橋,或飛機駛進松山機場,都看得清楚。
居然它這麼清楚,有沒有可能,成為飛彈瞄準地?萬一落彈來,會擊中大樓東邊或西側?雖屬妄想,卻無法抑止,尤其當它這麼顯明,且愈看愈覺明顯時,一場火就那麼燒著了。有人在陽台呼救,有人從五或六樓跳下,有的,跑到樓頂空地。當時,人人都急,都被莫名的命運擺弄,沒有人發現,可以從南側住戶陽台,跳到背後另一棟公寓。但我在妄想裡看見了。
這是預兆,意思是說,萬一有火,得往南逃?假設,預兆跟夢一樣,經過變裝,設了密碼,往南,是到人間還是地獄?
●
幸好,不是燒炭。
電影《瓶中美人》女主角燒炭前,以膠帶封住門縫,等親友闖進,還救出小孩。我認定主臥房偶爾充滿的悶燒味,不來自燒炭。燒炭自殺,若有規律,就著實可怕了。
有一天下午,一家人逃也似地離開家。到中庭,岳母來訪,我們說,別進去,有人燒東西,客廳、房間,都有煙味。岳母內急,雖聽著,仍直衝進屋。我瞧著大樓,堅實的內裡氣管、水管相通,它其實像一隻大火龍,火花一丁點,就足以喚醒它。
在超商、影片出租店盤桓幾小時,再回家,岳母留下一袋水果,人也走了。
客廳沒了煙味,主臥房還一陣焦氣。當天夜裡,總睡不著,深怕一個醒來,樓下燒炭自殺者沒死成,濃煙往上竄,連累樓上住戶。
我驚醒多次,進主臥房聞了又聞。妻跟兒子睡得正熟。
躺在床上,我推論,煙往上冒,一到六樓,究竟那一戶?一樓三戶,計有十八組嫌疑犯。我翻來覆去,睡不著,直到夢見自己變成火人而驚醒。
●
我跟妻說,不行這樣下去了。
先前,已發出十八封勸告書,塞進住戶信箱,卻無功效。煙味從主臥房通風管竄進。沒有顯明的煙,但氣味變濃,像灰色加上灰色,一層一層,不瞬間變黑,卻還是黑了。
我下樓,想查明煙味來源,好阻絕一次一次妄想。平時搭電梯來回七樓,二到六樓,卻少經過。門口格局相同,樓層不同,人不同,樓梯間就陌生了。門口擺放鞋、雨傘,有的,在牆上釘了框畫,電梯門開,映入好風景。而牆後呢?就不知道是什麼呢?我從六樓查起。站近門口,聞了聞。沒有煙味,卻聞到暖呼呼的腳氣味,這氣味,又跟鐵工廠廢棄油污合融。慶幸自己閉著嘴,沒吃進那口味道。我皺眉,看了一眼門外一雙爛污的球鞋,掩掩鼻,觸按門鈴。六樓住戶說,他也聞到煙味了,門打開,讓我進去,我嗅了嗅,果然不假。
抱怨了一陣後,我說,我下樓問。我關上門前,特地多看他兩眼,他門一關,卻不好奇煙味從何來,也沒有隨我下樓的意思。難道,就讓那一層莫名的、灰灰的霧,鎖住我們嗎?糟糕的是,那一層霧,沒有顏色,既然看不到,也就容易忽略了。
但是,人可是每一秒都在呼吸呢。鼻子看管的,盡皆無形無色;眼睛照管的形形色色,都讓鼻子消蝕跡影了。而鼻孔洞開,毫無拒絕權利,總之,香的、噁的,只要還能呼吸,就得照單全收。鼻子本身,像生命寓言,我想下樓去,想給鼻子一個好的寓言;至少,不要一個壞故事,不要成為一個火人。
●
五樓燈壞,但還瞧得見門鈴。我壓下門鈴,聽見門後,有人蹦蹦蹦跑過來開門。門一開,是認識的太太。她一臉驚惶,不知道鄰居來訪何事?我說明來意後,她居然關了門。我使勁按鈴。沒回應。我又繼續按。隔不久,換先生過來開。他滿眼惺忪,開門後,朝屋內嚷嚷,埋怨妻子沒來幫忙。
二到九樓,格局都一個樣兒,我熟門熟路,衝進主臥房,正要打開廁所的門時,太太自個兒開門跑出來。她一邊咳嗽,一邊掉淚,門開的剎那,濃煙竄出。
我沒搞懂發生什麼事,先生也摸不著頭,又氣又驚。太太經我質疑,火速進屋,掩滅證據。陣陣門鈴催促,她一急,撞翻更多紙人,火勢更旺。
「紙人?」妻吃驚。我說是啊。
五樓太太燃燒一個一個紙人,幫先生擋災,最重要的,要讓先生再一次愛她。
「巫術嗎?」妻問,我點點頭說,大約是吧,「而且,還算是一個愛情故事呢。」我還沒全盤了解。
總之,已經解決了。我打開門窗,消弭五樓冒上來的煙。主臥房的窗,看得見五華街上,紅底黃字的麥當勞招牌。
這麼望著時,招牌卻也隱隱生煙,就要飄忽而去。我警醒,跟家人不斷說話、說話。這樣,我們的話語就成了一個拉力,把我們牢靠定住,沒有隨著陣陣濃煙,被風吹散。
臭豬油拌飯
◎甘耀明
村子流傳一則臭豬油拌飯的故事,主角是七十歲的阿菊婆。如今她膝下承歡,子孫滿堂,如果有人想聽這故事,她倒很樂意說。如果想憑故事重現那碗人間至臭與至香的拌飯,阿菊婆絕不反對,但她會說:「人生和食物的美味總是短暫,得消化的長。」時間回到1942年,昭和17年冬天,那時的阿菊婆八歲。每天凌晨三點,阿菊被同床的阿姨喚醒,兩人點著蠟燭來到灶下煮飯。窮困加上食物配給制度,她們能煮的飯不多,一杯米要煮家族十人份,只能摻了大量的番薯,沒工作能力的阿菊通常只能吃番薯。而且米缸由阿婆管制,藏在她的床底,睡前才拿出隔餐的份量。在這樣的情況下,阿菊要偷吃到飯太難了。
但是,阿姨總有辦法騰出一碗飯。她每回把那杯米攢出兩粒米,要阿菊存在竹筒。撲滿在竹節上鑿小洞,恰好投下米粒。老鼠鑽不進,外人也看不出。每日投下三餐六粒米,她逐漸聽到竹筒的飽滿聲。每過一季,她攢足一百餘粒米,阿姨教她把適量的水灌近竹筒,塞入爐灶烤。剖開竹筒飯時,米香四溢。
這時阿姨會放下因為防貓而掛在樑上的豬油罐,舀出油脂放在熱飯上。豬油霜溶,把每粒飯抱得緊,迸亮亮的。那是阿菊最幸福時刻,這世界彷彿只剩她和阿姨,兩人蹲在黑暗的灶房角落,就著爐裡竄出的火光,吃起豬油拌飯。阿菊發明很公平的吃法,她吃一口,阿姨一粒。阿姨也覺得很公平,這碗好時光她吃得飽飽。
某天早晨的爐火邊,阿菊說:「阿姨,大家對妳恁壞,是不是妳剋夫。」她這麼說,因為家人說阿姨害死丈夫,沒給過好臉色。阿菊二歲時,阿姨的丈夫採水果跌落谷,再也沒醒來過。阿菊對此沒記憶,當時太年幼了。
「不要亂說,亂說的話,灶神年底回天上時,會跟天公說的。」阿姨對她使出壞眼色。
「那說好話呢!」「可以。」「那說願望呢?」「灶神會跟觀音娘娘說。」「說了呢?」「觀音娘娘會幫妳。」「那我要日日吃豬油拌飯。」阿菊打開灶門,對裡頭說。
「緊吃緊長大,將來要嫁給好先生。」隔年夏天,村子進來兩輛三輪,來到阿菊家前。今天是阿姨改嫁的日子,但阿菊被後頭那輛車吸引。
車上照禮俗綁了一根竹子,竹子上頭掛塊豬肉,晃呀晃的。阿菊很少看到這麼大塊豬肉,目珠不離開那,一直逗留在三輪車邊。婚禮很簡單,一盞茶而已,打扮漂亮的阿姨上車時,注意到阿菊的眼神掛在豬肉上,便踮腳把肉取下給她。
「妳要煮給我食呀!」阿菊說。
「等我轉來。」阿姨說。
阿菊仔細顧緊。天氣好熱,鮮紅豬肉很快轉成暗紫,失去彈性。過了幾天,豬肉漸漸腐爛了,她用繩子綁了泡在井底,結果整座井成了臭水。第六天,歸寧的阿姨帶了一包黑糖給阿菊,卻發現她臉臭臭,身體更是惡臭,最奇特的是阿菊的雙掌闔得死緊。阿姨狠勁掰她的手,一塊長蛆的臭肉掉下來。原來阿菊這幾天看不到阿姨,一直哭,用淚水的鹽分減緩豬肉腐化,用手掌隔絕空氣。即使這樣,豬肉還是長蛆,把一塊手肘長的肉塊吃成棗子大小。
「妳回來幹嘛?」阿菊憤怒,又說:「豬肉壞了,不能吃。」阿姨安靜地蹲下,拾起爛肉和白蛆,全部放入燒熱的鍋子。一股臭味散發出來,愈來愈濃烈,彷彿該是數天才腐化的肉因為煎炸瞬間釋放惡臭,如屍蟲鑽入腦門,如刀子割毀五臟六腑。家人和阿姨的丈夫全掩鼻離開,樑上的老鼠和牆縫的蟋蟀竄到農田,房屋周圍一百公尺沒了人。
那個時代,阿菊為了避開親子間的凶煞,只能委婉稱母親為「阿姨」。這一次,她怕永遠失去什麼,竟用盡全力喊:「阿姆,帶我走。」她淚水失控地說給母親,也說給火堆裡的灶神聽。忽然間,柴火大發起來,鍋油沸了。來一聲阿姆,阿姨心都碎了,淚也直猛猛地落鍋。吱啦一聲,油水噼哩啪啦爆濺開來,噴湧大量水霧,灶房被瀰漫的煙霧籠罩成巨大的暗影。好安靜呢,像回到往日清晨的時光,灶房只剩下母女兩人似有還無的偎靠。漸漸的,由於阿姨的淚水混入熱豬油,先前的臭味轉韻,在鼻間沉澱成芬芳,由於大開大闔的落差,香味是翻兩番,那些臭肉竟煉出了至極香水。豬油淋上飯,把阿菊迷住,她沒有吃半口,光是聞那香水味就飽了。她滿心歡喜得很,捧碗蹲在屋角,等待我一口、妳一粒。
天黑了,夜空迸流星,廚房的灶爐也火星流迸。阿菊仍在角落捧那碗飯,不知阿姨早就趁煙霧之際離開,從此沒回來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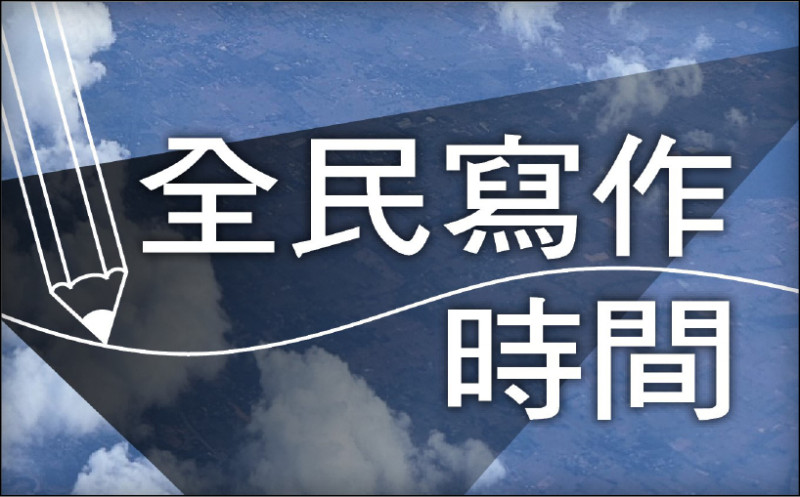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