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紙書籤
 照片◎敖古仁
照片◎敖古仁
文.照片◎敖古仁
手邊的圖文書是有關老明信片的介紹,我從圖書館借來,剛翻閱了幾頁就想暫時擱下,所以將書反扣在床板上,起身,從雜物盒內摸出幾枚書籤,攤到桌上,這才發現盒子裡已經沒有紙書籤了。
桌上的書籤,有兩枚小熊維尼的磁鐵書籤,那是幾年前便利商店的集點換來的。小熊維尼的上頭是兩枚不成套,塑膠製,長條形,半透明藍的書籤,可能是購書滿額時的贈品。塑膠書籤旁還有一枚金屬書籤,想想應該是以前訂閱雜誌時的贈品,號稱多少K金,可以夾在書頁上,但是過重,所以幾乎沒用過,現時已經罩上一層薄霧,不再閃耀金光。所以,沒有我想要的,簡簡單單的紙書籤。曾幾何時,它們逐漸失憶在日常的生活裡。
很早以前,在書局裡隨便買本書,年輕的櫃台小姐將書裝袋時,總會細心地再放進一、兩枚紙書籤。如果印象無誤的話,那個年代,文具店或是書店還特別闢出專櫃,用來銷售書籤。我向姊姊查證這項記憶,於是她搬來早年的收藏,足足兩本專用的收藏冊和一個鐵盒,同時手指鐵盒上另外的兩套書籤說:「這是比較近期的,但是書店已經關門了。」
這批紙書籤,近兩百枚,仔細審閱後發覺它們大概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東西了。起先是書局或文具店想要幫自身或是經銷的商品做點廣告,所以印製書籤贈送給讀者或是消費者;商家後來發現,有人收藏他們贈送的書籤,甚至本末倒置,為了書籤來買書,於是嗅覺靈敏商人開始設計精美的書籤,給人收藏。
一般說來,書局贈送的書籤,設計上較為樸實,都是紙質的印刷品,有時還是成套的。它們的正面通常是美麗可愛的圖畫或攝影作品,有時候籤底還會印上商家的店名;這些書籤的反面通常是印製「功課表」,或是月曆,用來增加書籤的使用價值,免得不珍惜的人隨手拋棄,有些積極一點的商家還會在功課表的旁邊宣傳他們的新書或文具。
為了和書局的贈品書籤有所區隔,專業公司設計的書籤有時改稱為書卡,因為它們除了原有的書籤功能外,還加進生日卡、問候、邀請,或其他的功能。不過,書卡的尺寸倒沒有太大的變化,可能是為了方便收藏的人收進同時銷售的專門收藏冊。這些書卡通常是套裝設計,但是也可以個別單張銷售。統計一下手邊的書卡公司,大概有十四家,發行量較大,較為知名的有企鵝、凸凸、海山和亮冠書卡等,想來這些公司現時不是轉型,就是不在了。
這些設計的書卡在素材上較為多元,除了紙製品,當時還會採用木片,或是軟木的材質,也有些書籤是用蝴蝶或是葉脈的標本來製作;金屬書卡在當時的市面上還看不見。它們的紙質更為精美,手法上除了套印現有的照片,或是專人手繪的圖畫外,少數的書卡還會使用鏤空的手法,或是將絨布裁成圖案,再黏貼到底紙上。書卡的正面是美麗可愛溫馨浪漫的風景、人物、動植物攝影或是圖畫,背面則是一片空白,方便購買的人寫上一些文字,當成送人的短籤。當然,書卡上絕對沒有廠商的廣告文案,不過有些書卡還是保留了生活格言或是生活小語的傳統,閱讀這些文字,有時讓人發笑,但是多數時候只讓人感歎過去歲月的單純。
姊姊曾在琺瑯禮品工廠做過彩繪員的工作,當時工廠的一條生產線就是西洋式仿古的金屬書籤,這些產品都是提供外銷,所以市面上買不到。姊姊送我一根鵝頸鍍金的書籤,鵝頸的頂端還栓上一個琺瑯的黑貓墜子,多年來捨不得用,卻還是摔破了一隻貓耳朵;對了,好像我還有兩個不同造型的墜子可以替換,但是收在另外一個鐵盒裡。
或許只是單純的慣性,我還是覺得紙書籤最方便,使用起來最沒有負擔。
於是,一些零碎的記憶跟著書局的贈品書籤,從小學班上私設的小圖書館,來到台北城,西門圓環天橋下的「中國書城」,穿過信義路,到了「國際學舍」年度例行的國際書展,轉回「城內」火車站前的書店街,再越過後火車站,迂迴來到大橋頭下的補習街和書店。這些書局文具店,多數不是沒落,就是被連鎖書店打敗,像是好萊塢電影裡演過的情節,不在了。而我也隨著這些逐漸消跡的地址和名稱,終於離開那座城市,來到陽光燦爛的南城。
想來,多少有些傷感,於是我的中指滑動滾輪,翻閱重重的網頁,想多了解一下書籤的資料。因此得知西方第一枚有案可考的書籤出現在1584年,那是Christopher Barker獻給女皇伊莉莎白一世,一枚絲質流蘇的書籤。不過當時比較常見的方式是在書背上黏貼一條固定的緞帶,用來標示讀書時暫停的書頁,目前一些精裝書還是經常見到這樣的裝幀。第一枚可分離的書籤出現在1850年左右,一直到1880年以後紙製的書籤才變得愈來愈普遍。
據說,書籤古稱牙黎或書簽,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唐朝的杜甫〈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和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的詩裡都曾提及這項文具。當時的人用動物的牙骨插入竹簡或卷軸,用做標記,後來又在頂端繫上絲繩,讓標示的功能更為明顯,兼做裝飾的功能。當竹簡轉為摺頁的書冊後,牙籤狀的書籤轉成薄片,方便夾進書裡。於是宋代以後,書籤的標準樣式便大致定型了。
民國時,茅盾在他的短篇小說〈陀螺〉裡提到的「美術書籤」,大概就像我手中這一枚「東方出版社」的書籤吧,正面是清朝華喦畫的〈午日鍾馗〉,雖然紙面已經泛黃,但還是散發一縷念舊的閒情。還記得亞森羅蘋和福爾摩斯探案嗎?那條街區,曾經是我買書,讀書,工作的地方,來來去去不知走過多少回?如今只剩手中這一張書籤,憑弔曾經幻想過的冒險。
現在連鎖文具店裡已經看不見書籤的專櫃,上次我去,只見少數不同材質形式的書籤,瑟縮在卡片專櫃的一角,不特別找尋便會忽略過去。這裡頭有幾枚紙書籤,是網路上的人氣部落客作者授權出版商發行的,未見太多雕琢的童趣筆觸倒是另有一番況味。逛到軟性磁板區,這才發現還有一些磁性書籤另外掛在層架的壁板上。
所以,廠商真的不再設計生產典雅的紙書籤了嗎?網上的海外商城還有,不過現時方便購買的只剩名家設計,材質複雜,功能多元,花俏可愛,或是KUSO的書籤,但是相對的,價昂。所以,大概是紙書籤利薄,除了連鎖書店偶爾用來當做贈品,慢慢淘汰了,
倚賴床板,就著大窗,斜光下閱讀,手中的書本幾度開闔,夾頁的書籤跟著幾度進出書頁。我已經報廢了一枚小熊維尼的集點書籤,從騎馬處的軟磁片折斷,現時手中的用品是一張已經失聯的名片,夾進取出,我想用個幾十年都不會折損吧。
我沒有收藏書籤,不過我知道我還有一些年代同樣久遠的紙書籤,夾在架上的舊書裡,哪天,時間、天氣和心情都對了,趁著曬書的時候就把這些紙書籤,統統兜攏,說不定還能取回一些古早的記憶。也或者,利用硬碟裡儲存的素材,設計自己專屬的書籤吧,那天,等心情到了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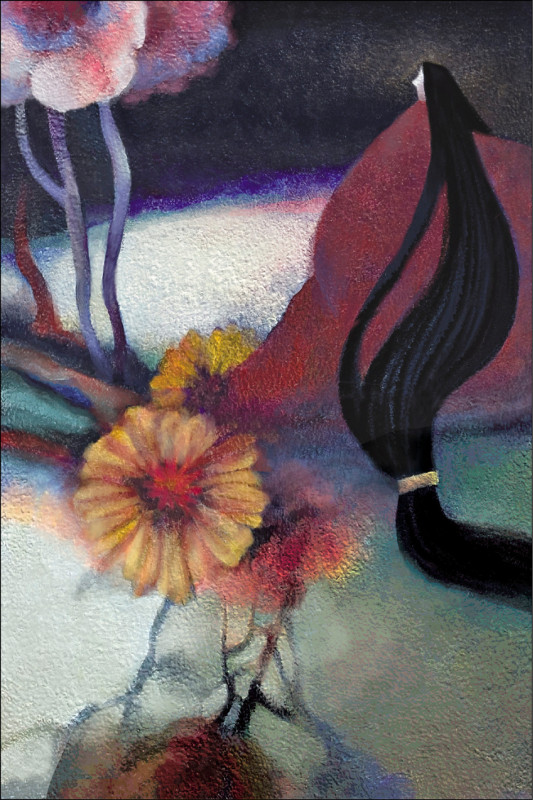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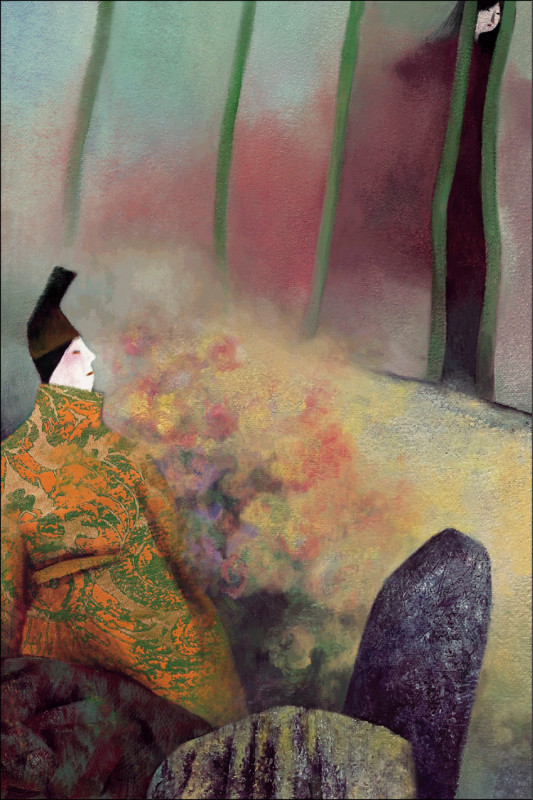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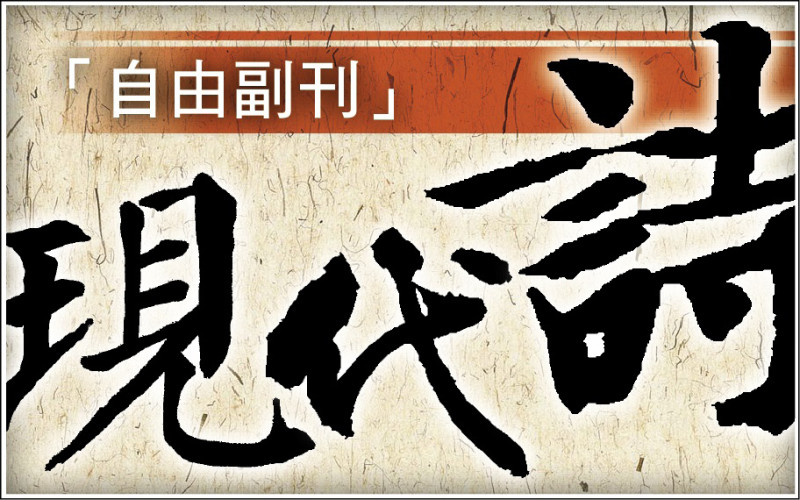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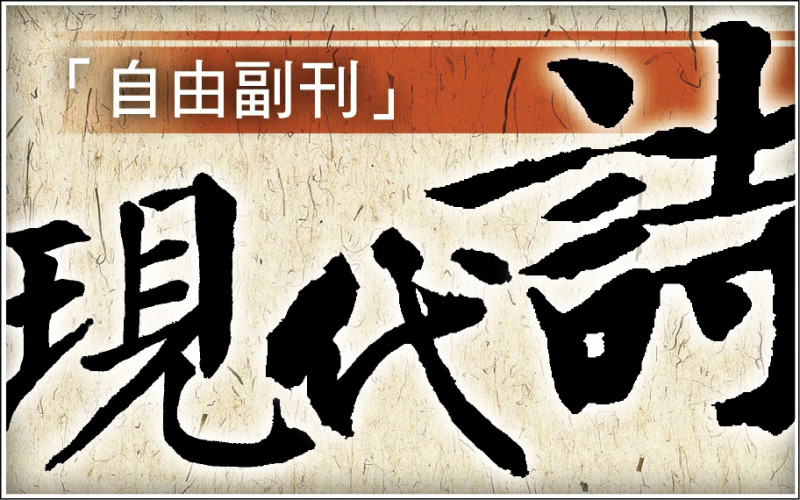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