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閱讀小說】 樓上的神 - 上
 圖◎吳怡欣
圖◎吳怡欣
◎張耀仁 圖◎吳怡欣
姊姊的那頂帽子其實是我拿走的。
失去帽子的當晚,姊姊近乎失控地翻遍家裡每個角落,汗水沿著額心滑進眼窩,像哭,愈發突顯無所適從的焦慮。但姊姊並不咆哮,專心一意拉開一個又一個的抽屜,從樓上至樓下、從書房至臥室,細細的嗓音喃喃自語:跑去哪了?跑去哪了?
跑出門的姊姊穿反了鞋,只聽見母親尖叫著追出去,緊接著是更遠更遠的尖叫聲,約莫是從鐵道的那個方向傳來的吧──與自殺無關,純粹是姊姊每天必經之地──每天,姊姊騎著單車從家裡出發,拐過巷口的大時鐘,拐進鐵道旁,行經柵欄、行經平交道,再拐過另一個巷口──也許在雜貨店前停下來買罐養樂多或一小包蘋果麵包──然後再次看見大時鐘,抵達家門。
日復一日,姊姊像是上了發條那樣,時間一到就戴上帽子跨上車子,繼續她傍晚的必然行程──似乎是從奶奶病倒之後開始的吧?或者父親逐漸從家裡缺席的時分?無人知曉,因為姊姊從來不說,我們也不知從何問起,只能默默支持著於他人而言理應是運動,於她而言卻是肅穆儀式的這一行為。疰夏灼燒,姊姊依舊一臉的汗壓低著帽簷,任憑髮絲黏貼於兩鬢與頸後;嚴冬寒霜,她愈發倚賴那頂鵝黃的漁夫帽,帽子軟薄,幾度被風吹跑的,母親為它縫上鬆緊帶,白色的帶子牢牢箍住下巴,箍出鮮紅的印子,讓姊姊看起來好似童騃的小學生,儘管她已近不惑之年了──儘管帽子陳舊、綻線,並且由於久未清洗而發散出雜揉了汗與油脂的餳澀,但姊姊格外珍惜它,去到哪裡都非得戴著它,彷彿身上的一部分。
彷彿一則隱喻:不可能再好,也不可能再壞,就只是一頂帽子而已──就只是一名「失魂落魄」的人。
「掉了三魂走七魄啊。」親戚們七嘴八舌。
「要去收驚啦,要給神明做契子!」
「要念經!」
「要吃素欸!」
那些林林總總的宗教儀式與信仰,早在姊姊辦理休學那年,因著父親的堅持已有了諸多體驗,包括祈禱、香符、過火、開壇、作法──甚至牽紅姨、觀落陰都曾經歷過──泰半是寤夢般的腳步、漫漶的煙花以及鬼氣咻咻的咒語,它們往往冷不防迫近,大喝一聲或者飛散金紙,以致浮塵亂舞,姊姊就這麼沐浴在光燦燦、粉亮亮的世界底,不知所措、不明所以,唯獨父親用力地按著她的肩膀示意她坐好。
那一刻,她還是戴著那頂褪了色的帽子,眼神飽含淚水,飽含恐懼的情緒。
她在向我們求助。我這麼想著。那幼獸般的濕黑的眼神盡是懇求與茫然,盡現姊姊的魂魄仍丟失於未名的荒蕪底,那個強勢的她而今怯怯抓住衣角,一點也不若當年坐在燈下大聲批判社會議題、聆聽濁水溪公社,並且努力背好Feminist、Feminism這類攸關女性主義的字眼。那一刻,我多麼想衝過去握住她的手,告訴她:沒事了沒事了,等等就可以回家了唷,等等我們來去騎腳踏車。但我什麼也沒做,只是任憑那些粉塵漫盪於半空中,一點一滴跌進姊姊的髮窠底,一點一滴匯聚成父親手上的那包香灰,以及幾張蠟黃的符紙。
「為什麼不帶她去看醫生?」許多年後,向父親問起當初之種種,只見他寒著臉說:「汝懂什麼!」隔著那麼迢遠的年歲,還是不願意承認姊姊「有病」──有「神經病」,那些親戚背後是這麼說的,我們知道,父親也知道,然而他以為那不過是姊姊壓力太大罷了──「伊只是需要休一下。」父親說,臉上流洩著萬分疲憊的表情,揉捏太陽穴成為他習慣的動作。我相信我也有這樣的困頓。畢竟時光被拉得太長太長了,而今回想起來,最初踏進家門的那個警察已經極為模糊了,唯獨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清晰地烙印在腦海底,只因那是「正式的宣判」──國家機器代理人的「判讀」可能出錯嗎?也許吧,但當下我們只感到風暴來臨前的憂畏,我們期待著他的說明,也希望他的一字一句能夠為事件帶來轉折。是剛畢業的警專生吧,語氣不帶感情地說,深夜裡遇見在街頭遊蕩的姊姊忘了如何回家,被他們帶回派出所安置,最終在她的背包裡找到一封打算寄回家的信──
言下之意,姊姊失去了與人溝通的能力。
「還好,地址已經寫上去了。」年輕的警察說。他的人生正要開展,但我們的困惑從此滯礙。我們追問著:為什麼突然變了?為什麼最不需要爸媽操心的孩子,卻蒙上灰撲撲的色彩?我問姊姊:妳怎麼了?她搖搖頭。父親問她:汝知道阮是誰否?她小聲地說:「把拔。馬麻。」母親也牽起她的手:阿珍,妳是不是哪裡不爽快?乖,跟媽媽說。姊姊什麼也沒說,給了母親一個深深的擁抱,我看見母親忍住的淚水,那使得她原本就顯得濕潤的眼神更形濕黑。
姊姊突然問道:「米米露呢?米米露跑去哪啦?」
米米露是我們在颱風夜裡遇見的一隻米克斯犬,當時一家人從餐館出來,聽見細微的嬰兒也似的哭聲。好小好小的米米露像隻小兔子般躲在車底下,大概是被狗媽媽拋棄了吧,那是最最脆弱的毛孩子的普遍命運,所謂物競天擇啊。然而米米露的體格其實勇健得很,只不過眼睛容易產生分泌物,所以牠看來總是「睡眼惺忪」,憨態可人地伏在永遠欠缺睡眠的姊姊身旁,大概是這個緣故,姊姊才這麼倚賴米米露吧,也許早在這之前,她就發現殘缺的米米露也就是內裡欠缺的那個自己。
不幸的是,米米露早在姊姊升上高三時,就因為狗瘟死去了。
我還記得那個寒流來襲的清晨,獸醫院來了緊急通知:說是米米露輸血時突然休克……當我們趕至醫院,米米露只剩下微弱的抽搐與幾乎渾濁的雙眼,但牠仍不放棄地循著聲音看向我們這邊。「米米露呢?」姊姊問,好似回到最初的那個時間點,那時候抿緊了唇的她看不出激烈的情緒變化,只是不斷掉淚,一面緊緊握住米米露的腳,一面撫摸著早已失去光澤的毛絮,儼然召示我們日後回想起這段時光,勢必無法迴避做為起點的這個事件──無法迴避我們第一次目睹「真正的死亡」。
「不對!是你們把米米露藏起來了!米米露呢?米米露呢?」姊姊尖叫起來,發了狂似地在家裡翻找著,然後就是永遠地瘋狂了。
沒有人發狂。父親說。沒有。他迄今還是這麼堅持著。似乎只要孩子是「正常」的,他在應酬場合的面子也就不會掛不住。儘管說這番話的語調微微顫抖,但父親仍然在我們提到這一字眼時,屢屢糾正道:「一定是恁不夠關心汝姊姊。」「一定要多讓讓汝姊姊。」「要記得多關心伊啊,多和伊講話!」這麼說彷彿暗示著姊姊終有復元的一天,而我們必然回到歡樂無憂的家庭時光──但,原本的時光究竟生得什麼樣子呢?這麼一想,好像我們把所有的希望與失望都繫在姊姊身上,忽略了會不會是原本的傾斜導致姊姊的病症?
「就已經跟你說了,她沒病啊!」父親再次斬釘截鐵道。也許如此,家裡有一陣子供奉了許許多多的神明,大部分來自佛教與道教,微妙的是,後來甚至出現了聖母瑪麗亞、耶穌基督受難像。約莫人到了渴望解決問題的臨界點,就是需要各路神佛的協助以強化信心吧。那是我們離神最近的一段歲月,只要有人提到哪個地方的廟宇、宮殿、法會有靈,父親就帶著姊姊前往,希冀神佛能夠拯救姊姊的魂魄於萬一,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許是屏東萬巒鄉萬金村的聖母形象,在那個群山環繞的素樸聚落裡,到處張開雙臂的聖母塑像流露著慈藹的神情,而我們都成了孩子,需要母親的擁抱──姊姊張著圓乎乎的雙眸,看望念念有詞的神職人員為她祝禱、為她祈求赦免──那一刻,我仍舊想衝過去握住她的手,告訴她:沒事了沒事了,等等就可以回家了唷……因為我知道,有罪的也許是我們,我們沒有正視她的病情,反而不斷掩蓋這樣的事實,試圖將精神疾病導向「非自然」的、難以啟齒的狀態。
每每行經大廳,那些姿態不同或怒目或低眉的神佛投下參差不齊的暗影,也投下深淺不一的恐懼,不免使人感到惘惘然的,說不上來出自於敬畏抑或亟欲逃避的心情。祂們不會聊著聊著就吵起架來吧?祂們會嫌空間太狹窄嗎?我這麼揣度著,責怪自己怎麼可以這麼無禮?無論同不同意父親的做法,祂們終究是為了挽救姊姊而來的──儘管如斯荒謬也如斯真實:荒謬的是我們這麼需要神竟不知道該相信誰,只能聚合祂們以免掛一漏萬;真實的是有一陣子,父親日日夜夜跪在案前誦念佛經、符咒,駝背的身影不同於那向來罵罵咧咧的性格,看得出他愛女心切,也看得出他的堅持何其頑冥,一如姊姊頑冥地愛上了漁夫帽,並且變得易怒易疑,一度每夜質問我:是不是拿走了她的東西?是不是喝了她冰在冰箱裡的養樂多?說著說著動起手來,一面大聲道:「為什麼妳要這樣?為什麼為什麼所有東西都要不告而取?」
彷彿要從我身上奪回什麼的,姊姊毫不留情地毆打著我,那許是自幼以來,一板一眼的姊姊固然受到父母稱許,卻總是比不上擅於察言觀色的我……會是因為這個緣故,姊姊一直以來看似沉默壓抑,實則不甘心嗎?我看著手臂浮現的瘀傷,它們像姊姊烏黑的眼珠,牢牢盯住我,向我抗議什麼的,也抗議這個世界的不公。這麼一想,不知該為她慶幸抑或悲傷,慶幸她終於能夠放心表達「真實的自己」,悲傷她竟必須透過這樣的方式吐露心聲,代價未免過於沉重。然而姊姊似乎樂此不疲,反覆排演著相同的戲碼,直到我拿走了她的帽子,直到我再也無法忍受愈來愈多的神佛進駐家裡,祂們發出被煙薰、被花香環抱、被精油縈繞的諸多氣味,那些氣味混雜在一起顯得俗不可耐,一如鹹到極致則苦,濃郁極致也等於多此一味,如此而已。(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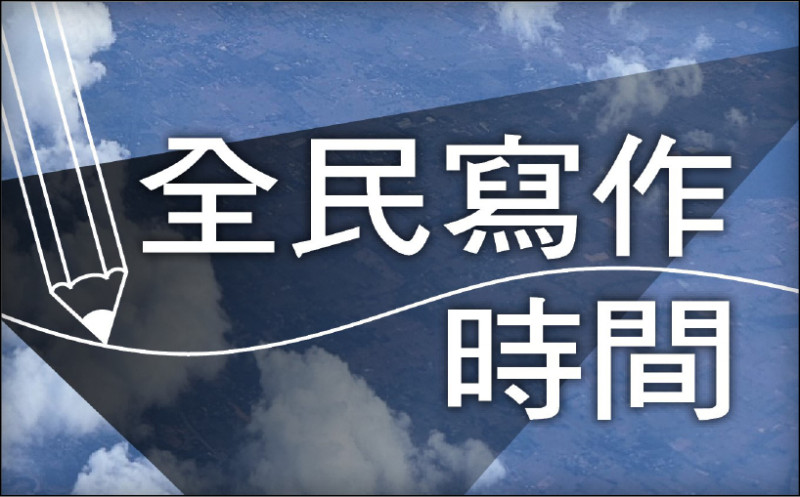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