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須文蔚/在遮蔽與傷痛間迴環複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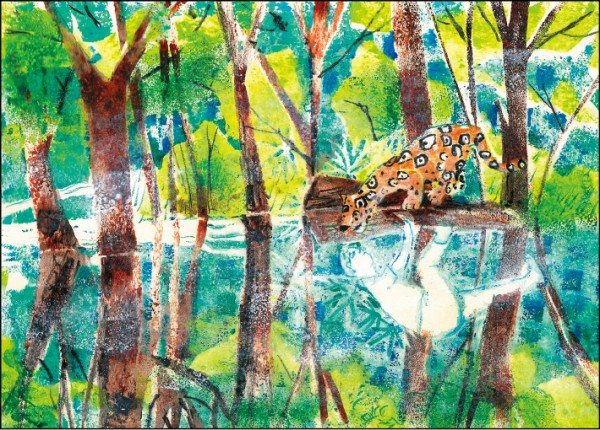 圖◎王孟婷
圖◎王孟婷
◎須文蔚 圖◎王孟婷
記得第一次和你談詩的前一個晚上,示威群眾衝進行政院,爆發大規模的衝突與驅離,學生靜坐在立法院前。我依約在夕暮時分抵達淡江大學,走過宮燈道,左手邊的球場燈火輝煌,走進文學院,找到你和微光詩社的青年詩人們,波瀾不驚地談了一晚的創作經驗。
等你到縱谷裡讀書,問起你,在那麼喧騰的時刻,詩社裡怎麼還有人要聽文學的演講?
你的回答很實在:「不少人下午要打工,沒辦法去示威。」
慢慢認識你,知道你和「不少人」一樣,需要四處兼職,把辛苦賺來的錢拿去繳學費、房租,偶爾奢侈地買幾本詩集。更辛苦的是,你總是遇到大大小小的災厄:腳踏車鍊條常鬆脫、姊姊罹患失語症、至親重病逝世、好朋友有躁鬱症等等。我們每次的專題討論裡,你總是苦笑著說近況,有幾個月不停地咳嗽,有幾次一邊談著詩,一邊抹去鼻血,要大家不用擔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讓人好奇與擔心。
我想起猶太詩人策蘭(Paul Celan)的一首詩:「發生了什麼?石頭離開了山坡/誰醒來了?你和我/語言、語言。下一個地球,相隨的行星/更為貧窮。打開屬於家鄉」。薛西弗斯反覆推著上山的石頭終於可以滾落山坡,當永無盡頭而又徒勞無功的苦難結束後,我們陷落在更為貧困的時代裡,因為詩,我們可以逃離現實,遠赴另一個宇宙旅行?因為詩,我們可以回到故鄉的懷抱,能夠容忍孤寂時的冷清?記得一起讀策蘭時,你眼神裡總是閃耀著光,無畏那些艱澀與充滿死亡的隱喻,因為只有你讀過策蘭的傳記,知道這位目擊過集中營苦難的詩人,只能以反諷與質疑的語言,挑釁造物主的不公不義。
在縱谷裡的創作課和專題討論有個基本模式,就是讓有創作經驗的作者相互評論,讓作者更具有「讀者意識」,能與多個讀者共享訊息、思考與理念,自然能促進書寫與修改更細緻的反思。和絕大多數我互動過的青年詩人不一樣,你很樂於傾聽批評,當伙伴們浮想聯翩,新點子和例證不斷湧現,你總是興奮地一一記錄下來,反覆修改。
有天你提出修改了兩次的一首詩,很有把握地說:「這個版本我拿給女友讀,她很感動,都掉下眼淚了。」
老師和同學們都肯定新版本很傑出,題材相當動人,可是大伙沒放過推敲的機會,畢竟我們並不清楚詩篇背後的故事,沒有辦法感受到強烈的情感衝擊,所以挑戰了敘述不夠明確的問題,同時也提出好些個前衛的語言實驗的建議,供你參考。接著就放暑假了,你持續寄信來,討論、抽換、實驗與斟酌了兩種不同的樣式,等到報刊登出你的定稿,我比對先前的版本,可以發現你大力增刪的痕跡,也發現了你耐得住寂寞,願意在書齋生活中展現對文字的敬意。
很多有志寫作的青年總覺得不受重視,評論家不能理解創作的理念,和他們互動幾次後,不難發現他們過早自滿,未必會回應編輯、同伴或師友的建議。而你樂於修改,甚至有些執著,一如唐庚在《唐子西語錄》說:「詩在與人商論,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盡法家,難以言恕矣。」原來往復調整,錘鍊字、句與結構,把瑕疵除之而得到快意,想必是你獨到的創作體驗。
這一年多來,你試圖發展新的書寫風格,意象繁複,簡略敘述,一反新生代流行的語言模式,為此你閱讀了大量象徵主義的論述,有意開展出新的詩風。如同艾可所說:「一個符號愈晦澀愈模稜兩可,它就愈具意義和力量。」你期望掌握象徵的力道,同時能展現更為精鍊的篇章結構。你說:「我對石頭感到好奇/於是我選擇了土地/對隱喻感到好奇/於是選擇了詩」,我總以為應當是詩選擇了你,而你迷戀上了隱喻。
就像你在〈我害怕屋瓦〉裡所展現的,你既崇拜但又害怕屋瓦,這種矛盾與背反的態度,無非在探討文字作為屋宇,既有遮蔽的作用,但又有限制的傷害,同時屋瓦做為情感的依附,愛情與家庭不也同時能庇蔭,也會壓抑情人與家人。所以當你說:「我想逃跑/──但我害怕逃跑/倘若離開了屋瓦/我會餓,衣服會皺/雨不會離開/詩會死」,顯現出魯蛇的進退失據,想要海闊天空,獨立自主,但又擔心失去了家庭與情感,將會遍體鱗傷,連詩也無所依歸。
於是你寫出一組又一組作品,把恐懼、瘋狂、告別、出發、行進建構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道出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1942-)所說的「人皆裸命」(bare life)的看法,法律與秩序表面上是維護社會的秩序,實則以神話暴力與血腥的權力,讓統治者為了自身的目的而攫取裸命。如此一來,屋瓦就又有了一層深意,可以用來象徵政治權力的兩面刃作用,表面上保護公民,實則又宰制生靈。
更多時刻,你在詩中召喚屋瓦下的亡靈,在歇業的麵店中,在新莊的八德路旁,在雨中等待垃圾車,你都試圖主持一場又一場的降靈會,或更精確地說,你更熱衷出入墨西哥的亡靈節,以詩造景,在嘉年華會的歌聲中,讓遠去的親人再度歸來。記得你讀過帕斯《孤獨的迷宮》中的一段話給我們聽:「死亡和生命一樣,是不能轉讓的。如果我們的死亡不像我們的生活,那是因為實際上我們過的日子不是我們的:那樣的死亡不屬於我們,那樣的日子、殺死我們的厄運,也不是屬於我們的。告訴我你怎麼死,我就知道你是什麼人。」所以你也耽溺於辯證生命與死亡的議題,不求解答,而是更清晰地證明傷痛、生活與存在的意義。
有天你告訴我得了個文學獎,我恭喜你,你回答:「多虧前陣子那麼衰!」
哭笑不得的我說:「藝術家的養分來自生活的悲慘,這強求不得。」
你說:「看來我還有很多養分……」
是啊!在遮蔽與傷痛間迴環複沓,你有太多故事想說,就如同我們初識的淡江校園,詩人們與火熱的革命行動保持了一個距離,你以謎樣的象徵隔開了讀者與你直接接觸,這是你對詩的堅持。如同在一次微醺下,與廖啟余、蔣闊宇、蔡政洋、陳延禎等青年詩人,一起在深夜的東華校園漫步時,你寫下〈再走一段〉中的句子:「銳利如金屬的詞語/在風中不停打轉/鋸開空氣/詩歌在裡頭萌生」。正是你豪氣的宣言。
期待你反覆思索、斟酌、改定的詩篇,意象繁複如熱帶雨林,但意義尖銳如子彈,可以穿透與擊中時代的要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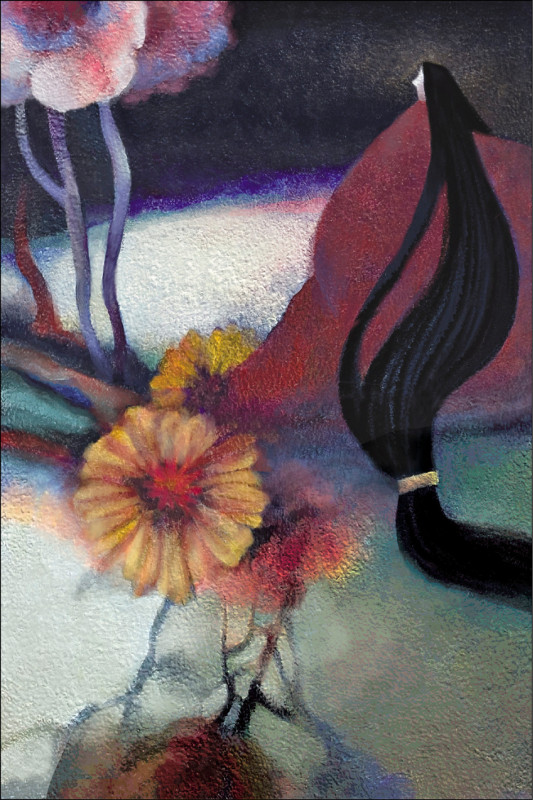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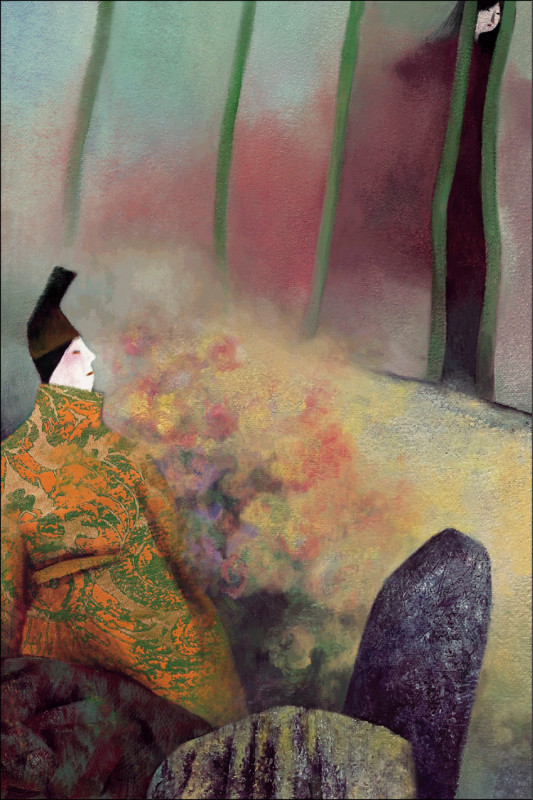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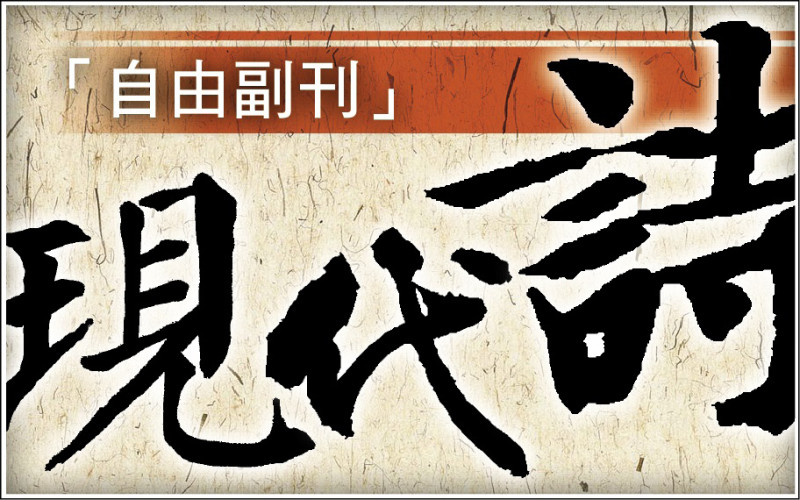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