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吳晟/深情而不專情
 圖◎顏寧儀
圖◎顏寧儀
◎吳晟 圖◎顏寧儀
1
1971年2月,我從屏東農專修完學分,正式畢業,某種巧遇機緣,應聘返鄉任教溪州國中,專任生物科教師,同時兼幾堂物理、化學;假日協助母親耕作,夜間閱讀、寫作,鄉居生活安定、平淡、忙碌而充實。
1980年秋季,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赴美訪問,為期四個月,年底返國。過了寒假、開學前,有位也在教書的文友見告,我有一首詩作選入國中國文課本第二冊。開學日到校,我找教學組同事要來一本,翻到第二課,即為我的詩作〈負荷〉,驚喜不已,幾乎不可置信。
我從未接到任何徵詢、或同意函,可能是我正在美國,聯繫不上吧。
當年的國中課本,統稱「部編本」,即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編輯,全國唯一版本、一致使用(直到2002年才開放民間版)。當年國文課本的作者,很少見還在世的作家。而我一位無甚名氣、還年輕的鄉野寫作者,何其榮幸被編輯委員青睞,感激之情難以表達。
新學期開學之初,我和一年級生物課班上學生,有一場很有趣、又令我有些尷尬的對話。
正準備上課,有位同學拿出剛發下來的國文課本,對我說:老師,這學期國文課本有一課作者和你同名呢。
我故作驚訝說:真的?怎麼那麼巧?
我稍做停頓,笑了笑,反問他:你為什麼不會想到,也許是我呢。
好幾位學生哄笑起來:怎麼可能?
我繼續逗他們:為什麼不可能?我不像詩人嗎?
幾位學生直接反應說:你教生物,又不是國文老師,怎麼會寫文章?
我不需要急於表明。呵呵笑道:是啊是啊,我又不是國文老師,怎麼會寫文章。
當年的國中國文課本很樸素,沒有作者照片,作者介紹很簡單:「吳勝雄,筆名吳晟,台灣省彰化縣人。民國三十年生。現代詩人。著有《泥土》等書」(隔年改編再版更正民國三十三年生)。多年來,確實有不少人,既定印象,想當然耳認為我是「國文老師」。
2
我從年少初中時期,偶然機緣接觸文學,廣泛閱讀文學作品,近乎癡迷;並嘗試學習寫詩。
時值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文學雜誌、學生刊物,非常蓬勃,我的習作四處投稿,屢獲刊登。我的中學階段,至少發表了半百篇詩作。
我熱愛文學,無庸置疑;然而深情、卻不夠專情。
依我的傾向、表現,高中應當選讀文組,大學就讀文學系;我卻選擇自然組(第三類、亦稱為丙組,醫學系或農業科系),讀得很辛苦。高三即將畢業之前,我還在補考化學,有位很愛護我的國文老師走過來,歎息說:讀文科「好代好誌」;偏偏讀什麼自然組,讀得「欲哭欲淚」。
至今仍常有人好奇地詢問我,既然年少即對文學有濃厚興趣,為何高中不讀文組。
我總是含糊以對,很難以三言兩語作答。
其實我很篤定、從不曾考慮讀文組,並未經歷任何內心的「衝突」,或來自家長的壓力。
或許整體台灣社會普遍「輕文」的傳統風氣,咸認沒有什麼背景的家庭,讀文科不容易找到頭路,大都傾向實用的工商科系,應該也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就我個人來說,不只這麼單純。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將文學創作一直當做崇高的興趣和志向,希望保有絕對自由揮灑的空間,不願成為賴以為生的工具,而受到約制,被迫或陷入貪圖利益的泥沼,寫出違背良知的文字。
我多方探問清楚,當年國內大學中文系(或師範院校體系稱為國文系),沒有新文學的課程;我既然決定從事創作,定位自己當作家,不做評論或學術研究,何須鑽研經史子集考據訓詁。以我這樣的文學基礎,可以靠自己進修。不無一些年少狂妄。
同時我出身農家,從小即需擔負農事,自然而然和土地有不可言喻的深厚情感,對農業也有一定程度的想望,總想學以致用,改善生產技能和農村環境。
綜合諸多因素,順理成章選讀自然組,沒有任何「壓力」或「掙扎」的故事。
可惜我天資愚鈍,又不善分配時間,以致「雙頭無一咬」,文學與農學都無所專長。和文學系出身的友人相處,我不忘強調我的本行是農科;一旦遇上農科的「同行」,則強調我特別「愛好文學」。
不過,文學基本上是反映生活,正因我從小在農村成長,所學也是農業,並實際耕作,不曾間斷,我的寫作題材,當然以土地和農村人們的生活為主。
雖然個人才學所限,我的詩文不夠豐富、不夠深刻,至少真實記述了廣大農民的生活;刻畫了某些台灣農村的樣貌,記錄了台灣農業的變遷。
曾有文學朋友提問,如果我選讀文組,很可能也躋身都城,成為「文字工作者」,投入和文學相關的工作。那麼,我的文學創作又會呈現什麼風格呢?這當然無從揣測,不過可以肯定,不可能如此專注書寫農鄉,我這一系列一系列密切連結土地和農作的作品,應該很難產生吧!
得失之間,不知如何衡量。
3
我對文學的熱愛、深情,無庸置疑;但確實不夠專情。
是天生個性呢,或是家庭環境的影響,我從小就很關心社會事,例如對地方選舉很有興趣。
就讀國小六年期間,我都當班長,愛「出頭」、愛打抱不平。父親很擔憂我容易惹事,管教特別嚴格。其實我深受父親耳濡目染。
我父親在日治時代擔任過公職,終戰後在溪州農會「食頭路」,當選過二任鄉民代表。戰後初期一、二十年,多數農鄉人不識中文字,常有村人、鄉親來找父親排難解紛、請父親代辦事情;常見父親為鄉里公眾事務奔走,常有政治人物來家裡,多有機會聽到他們議論時事。
很難想像十歲左右小小年紀,每逢地方選舉投票當日,我會跑去投票所觀看開票情形,父親若有參選,更關注。
戰後初期地方政治,基本上是有名望、受尊重的「人格者」鄉紳,被推舉出來參政。然而選風快速變調,有二大因素迫使父親失望退出,其一是賄選風氣開始盛行,從一包味精、一塊肥皂開始買票,逐漸加碼,再改發現金;其二是「被要求」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二樣,父親都不從。我多次聽到父親深深感歎。
在我國小五、六年級(1956年),彰化縣長選舉,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陳錫卿,有一首競選歌曲,歌詞如下(台語):「地方自治、初初實施,縣長由咱來選舉……陳錫卿,飽賢能……」最後高亢呼喊:大家選予陳錫卿……
學校老師教我們反覆唱,並「鼓勵」我們上學、放學沿路大聲唱,回家也要唱。「陳錫卿飽賢能」我們都唱成「陳錫卿肚腹硬硬」。和我同輩的彰化子弟都很熟悉。
(爾後才知道,這首競選歌曲的曲調,是出自日本歌〈長崎物語〉。)
陳錫卿的助選聲勢很浩大(不談有沒有買票),相較之下,另一位候選人石錫勳,就顯得很稀微,不知為什麼,當時我只覺得很不公平。
我向班上幾位家境比較好的同學,每人募集一角銀,合資去買一串鞭炮,藏好,等待午休時間,聽到石錫勳的宣傳車,我們衝到圍籬邊,點燃鞭炮,宣傳車上的人不斷向我們打拱、道謝:囡仔兄,真多謝!回去記得跟父母講……
那一幕、那聲調,在我小小心靈留下深刻印象。
初四(補習班)及高中階段,我在台北就讀。感謝種田的父母給我的生活費、零用錢,還算充裕,可以買書。經常在牯嶺街、重慶南路、衡陽路等書街留連。
文學書刊之外,我接觸到《人間世》、《自由中國》、《文星》等社會評論的雜誌;《文星叢刊》等自由主義思想著述……似乎比純文學更吸引我,啟蒙了我質疑、批判黨國體制教育的歷史觀,培養了我自由、民主的堅定信仰,激發了我社會改革的懷抱。高二時,我也成為《文星》的作者。
高中畢業,勉強吊上大專聯考火車尾,考取屏東農專,專一暑假,即因好發議論、「言論偏激」,遭到國家情治單位人員會同派出所警察來家裡搜索;專三即因「發展」「校外非法組織」文學團體,遭到調查局人員到學校調查,總教官氣急敗壞找我去訓斥,幸賴課外活動組、白尚洲先生出面維護、擔保才沒事。
1971年返鄉教書之後,台灣民主運動暗潮洶湧,自然而然和多位「黨外」人士相識、來往。我從不掩飾熱衷政治,不顧教師身分,不由自主投身運動中,耗費很多時間為民主理念相近、認同台灣主體意識的候選人,彰化縣黃順興、謝聰敏、姚嘉文、周清玉……台中縣市王世勛、廖永來、林俊義……製作文宣,站台演講,無數個夜晚,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一個鄉鎮又一個鄉鎮,一場又一場,義務助選。
都會型知識分子很難理解,我們要對抗的,不只是威權體制,更艱難的是依附在封建威權體制下的地方派系、「民間組織」、角頭勢力……
1980年,我辦理留職停薪,赴美訪問,重重關卡受盡刁難,始知人二室我的資料,記載「思想有問題、安全有顧慮」,每一關都是靠有力人士出面,才得以通行。最後一關教育部文教處,如何說明也不准,本已絕望、準備放棄,正步出教育部大門,走下台階迎面遇到林懷民,了解了我的情況,帶我進去找文教處處長,當下即核准、審核通過。行政人事真是複雜;人生際遇真不可測。
2020年5月,我通過申請,去「促轉會」調閱我在1970、80年代被情治單位(線民)監控的檔案,促轉會人員教我操作滑鼠,查看一件一件言行紀錄及「案情研判」,詳盡到令我無比驚異,深深搖頭歎息。
文學藝術、社會思想之外,我的閱讀,也是我日常最關注的領域,擴及農業問題、自然倫理、環境變遷。
我信奉思想轉化為行動,才有力量;我關心政治,直接投入民主運動,但不站上第一線,無意謀得權位;我為台灣農業及自然環境的惡化而憂慮,1990年代之後,耗費很多心思參與環境保護運動,推動種植台灣原生樹木、平地造林、友善耕作……但只能選擇性參與,未能全力以赴。
總因不能忘情文學,捨不下文學創作。
我的文青年代,台北流行現代主義、存在主義文學風潮,我不免受到影響,但保留深切質疑,尤其是所謂的「虛無」哲學,和我的現實生活體驗、和我接觸的思想啟蒙,社會力十分蓬勃,顯然格格不入。
我的文學作品,少有玄思冥想、風花雪月,大都是從真實生活體驗醞釀而來。我喜愛文學的純粹性,但不避諱文學的社會功能,甚至無妨做為廣義社會改革的「工具」。
.
不掛刀、不佩劍
也不談經論道、說賢話聖
安安分分握鋤荷犁的行程
有一天,被迫停下來
也願躺成寬厚的土地
――〈土〉
.
從書寫到行動,從理念到實踐,相激相盪、相輔相成,而又彼此拉扯、相互擠壓,每個人的時間、心力有限,如何兼顧、如何轉換,我必須不斷做調整。
畢竟我「旁騖」太多,對文學不夠專一、才情又不足,我的作品產量不多;而我何其幸運,些許成績常獲得各種形式的共鳴,無論是選入課本、選入文學選集、譜成歌曲、以詩入畫、為文評介、學位論文、詩句引用……總是十分珍惜,滿懷知音情誼,尤其是榮獲文學獎的肯定,既感謝、又惶恐,唯恐「名過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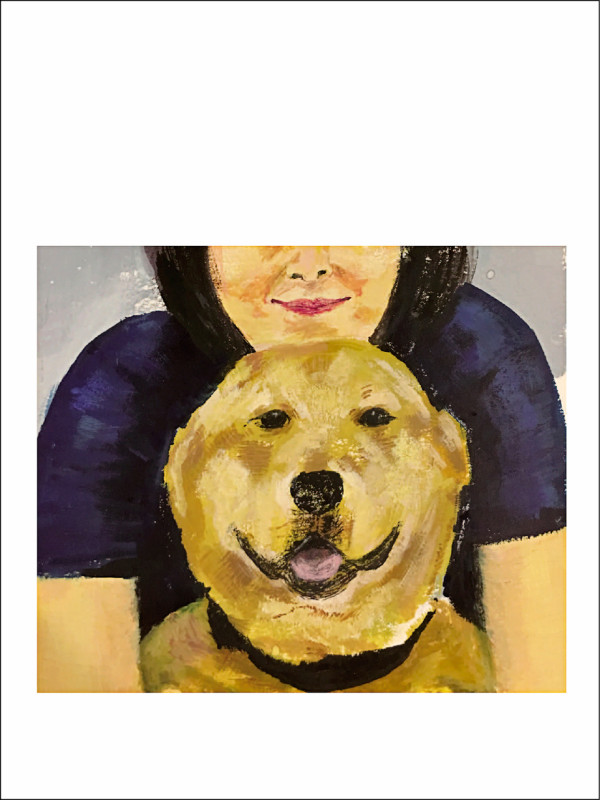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