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李桐豪/沒有人打電話給歌王
 圖◎黃子欽
圖◎黃子欽
◎李桐豪 圖◎黃子欽
家住永和,工作的地方在內湖,生活動線大抵如此:捷運頂溪站搭橘線到古亭,轉綠線至松山站,又或者橘線自頂溪到松江南京,轉綠線到松山,兩條路線殊途同歸,皆是出火車站,騎YouBike或搭公車到內湖上班,回家尋相同的路線折返,應酬、約會和社交,皆落在沿途兩條路線停靠的中山、西門與公館。橘、綠兩線,堪稱日常生活裡的任督二脈。
橘線中和段,偶爾頂溪到站不下車,搭到終點站南勢角,烘爐地土地公廟、圓通寺、華新街的緬甸米干跟來滋烤鴨,吃喝玩樂,不愁無處可去,可是列車反方向,便止步於大橋頭。大橋頭的大橋,意指橫跨淡水河的台北大橋,河對岸的三重或者新莊有什麼?全然陌生。跨越不過大橋頭,除了受限於日常生活動線,其實也是心理障礙。
若干年前,在大橋頭訪問過歐吉桑。嚴格來說,那個會晤連訪問都稱不上,捷運二號出口出站,和歐吉桑約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館,單純表明心跡,說想代表自己服務的雜誌社採訪歐吉桑、角度要怎麼切、報導做幾頁都想得妥當,未料,毆吉桑全程不耐煩,每個問題皆以無情的句點扣殺。例如大讚口述傳記《文夏唱/暢遊人間物語》太精采,讀罷意猶未盡,敲碗第二集,他一句話堵死:「一本冊愛寫足濟年,費氣,你是欲幫我寫膩?」不出書,不出新專輯,那學時下歌手先來個一首、兩首放網路讓死忠粉絲過過癮啊,他吐槽:「彼袂曉啦,這馬無人買唱片啦,你愛阮去SEVEN,邊唱邊賣膩?」來來回回幾個過招皆碰壁,求證生命中幾樁大事的正確年份,他不耐煩地說:「無咧記彼啦,兩、三年前的代誌攏無咧記矣,我哪會記遮爾古早的代誌。」
被噹得七暈八素,並非沒有做功課。歐吉桑的歌從少年時代聽到現在,依舊在歌單裡,自忖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世紀九○年代,聽歌不在iTunes或Spotify,而是CD和音響,城市鬧區隨處可見玫瑰大眾唱片Tower Records。唱片行買專輯分紅標與綠標,台語歌除卻江蕙、黃乙玲,還有一區亞洲唱片專區,洪一峰、郭金發、紀露霞……封面一律牛皮紙包裝,彷彿志文新潮文庫洪範叢書形成書系,辨識度極高,其中歐吉桑的專輯占比極高,《文夏的行船人》、《文夏的演歌》、《文夏的港都》……每張專輯皆有特定主題,頗有概念專輯的味道。作品一字排開,兵強馬壯,氣勢硬是比他人還強。
其時,對歐吉桑的來歷一知半解,看過他上過幾集豬哥亮餐廳秀錄影帶,方興未艾的黨外運動總將〈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放得震天作響。然而專輯入手,並非本土意識抬頭,而是亞洲唱片總是被放在綠標價格,一張一百二十塊,單純是貪小便宜,但聽到後來是真心喜歡。大學時代在書店打工,上班可聽自己帶去的專輯,歐吉桑的CD放進音響,按下播放鍵,書店的氣氛為之一變。歌聲裡每句台灣話都聽得懂,可是那聲腔、咬字卻無比陌生,如泣如訴的歌聲充斥書店每個角落,有奇特的異國情調,整個空間彷彿透過海鮮店褐色的啤酒杯望出去,充斥金色的光輝。起初鍾意的是〈男性的復仇〉、〈青春悲喜曲〉口白歌,彷彿廣播劇,有惡趣味。可後來曲目走到〈漂浪之女〉、〈悲戀的酒杯〉,哀傷的吟哦,聽著聽著就恍惚起來,「錯愛的車輪,輾轉誤了青春,像花落沉在苦海,不是愛情奴隸。心內有你一人,紅的心血,白的純情永遠,送所愛的人。」歌詞古意而直白,歌聲亦如音響雷射光束直直投射在心上,一轉一轉地旋轉起來。
此後,專輯一張一張買,網路陸續蒐集歐吉桑的資料,對傳奇歌王的身世也能拼湊出個大致輪廓:歐吉桑本名王瑞河,1928年5月20日出生台南麻豆,父母在台南經營「文化洋裝店」,母親設裁縫學校,開班授徒。父親開布行,當布業公會理事長,一件洋裝從布料、到剪裁、到販售的旅行,上下環節一網打盡,在府城一時風頭無兩。王家是基督徒,瑞河小朋友幼年在教會唱詩班展現音樂天分,小學畢業,赴日本工業學校讀書,課餘與宮下常雄學聲樂與樂理。1945年,台灣光復,小瑞河返台,父親安排入台南高商讀高中,盼長子能克紹箕裘,繼承家業。然而他未能忘情音樂,與同窗許文龍組「夜之樂團」,十八歲就創作〈漂浪之女〉、〈南國的賣花姑娘〉,在南台灣闖出響亮名號,順理成章出唱片,他取其母親「文化洋裝店」的名號諧音,以「文夏」之名出道,風靡全台,此後,有收音機、老曲盤之處,皆有文夏,他灌唱片、拍台語電影,堪稱台灣戰後初代偶像。他真正唱出「鄉親的口味」,悲戀公路上的快車小姐,流浪天涯的兄妹,聽著聽著都在歌裡流下歡喜的眼淚,寬解了悲傷。六○年代,電視興起,限制方言節目播放時數,一天僅能播放兩首台語歌曲,無疑是掐住了台灣歌謠的咽喉,兼以戒嚴時代有歌曲審查制度,歌王有近百首歌曲遭禁,理由是妨害社會善良風俗、反映時代錯誤。七○年代初期,時不我予,遂遠走他鄉,在日本箱根等溫泉鄉走唱,至八○年代歌廳秀大熱,捲土重來復出歌壇……
依稀記得歌廳秀錄影帶裡,豬哥亮虧他:「是真正好命囝」,他謙稱至今尚為三餐煩惱,豬哥亮頂一句:「啊就三頓煩惱毋知影愛食沙西米、壽司,抑是鮑魚魚翅。」出身富貴人家,早年留日返台發片旋即躍升一代巨星,然而從寶島偶像到禁歌之王,那抑鬱之感為何?貴公子盛年流落日本溫泉鄉按著客人的要求,唱著故鄉的情歌,可會心有不甘?網路上的資料可以拼湊這個人的形象,但他內心的愛憎為何?那是自己最想知道的事,可歐吉桑三緘其口,「政治,我不要講,私人的事情我也不想講,我又不認識你,我的祕密共你講欲創啥。」訪問途中,見他有幾個神采飛揚的表情,忍不住拿起相機拍照,他見狀簡直是翻臉了:「我就是無愛翕相,已經共你講好矣。我的相片我有版權,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拿我的相片去別間雜誌亂用。我不知道你的目標啦,我要回答什麼?我的代誌就按呢爾爾。我無必要逐項啥物攏共你講啊,我無彼个義務。」
場面一度尷尬,事情怎麼收場,已不復記憶,只依稀記得歐吉桑老婆文香在一旁打圓場,然後是自己就訕訕地離開咖啡館走到捷運站,臉頰熱熱的,像是挨了耳光,飄飄渺渺晃到大橋頭捷運站,模模糊糊記得車站牆壁復刻了郭雪湖名畫《南街殷賑》,畫面是熱鬧的大稻埕中元景象,但從自己眼裡望出去,是山雨欲來,愁雲慘霧。那遭遇太難堪,巴不得將此事從記憶中抹去,那挫敗變成心理障礙,此後無事不登大橋頭。
記憶塵封心底,直至今年初春,某日閒坐家中掛網,得知歐吉桑故世噩耗,心下有些悵惘,不由自主地點開錄音檔案,心不在焉地聽著,「你要問什麼,趕緊問啦,很多事情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政治,我不要講,私人的事情也不想講,我又不認識你,我的祕密共你講欲創啥……」聽到難堪處,頭皮一陣發麻,可聽到下一句啞然失笑:「無名的,講予四界知,一出名,啥物攏無愛講。」心想這人未免太直白?腦海閃過一個畫面:服務生將咖啡端上桌,他二話不說就拆了三個糖包,倒入咖啡杯,我驚呼這樣對健康不好吧,「我體質好啦。唱歌的人講吃麻辣喉嚨會壞掉,但我麻辣鍋當水喝,大中辣看我當天心情,不夠辣,就摻沙茶和蒜頭。話隨便人講啦,至今登台,每一擺我攏講我今仔日聲音上好。」
電腦錄音檔的歐吉桑,簡直是另外一個人,當日他給我的那些難堪,如今聽來有些幽默與真情流露,問他什麼樣的契機寫〈媽媽請你也保重〉,歌曲反映台灣各個階層,靈感何來?「台灣囡仔去金門做兵攏會想媽媽,我只是把那個心情寫下來,有一擺去理髮店,理髮小姐替我理髮,有感而發,寫了〈理髮小姐〉。你會觀察,你有心情,就看你要不要寫而已。」又問〈運河悲歌〉是自己失戀的故事嗎?「毋是啊,就創作啊。小說家寫足濟冊,敢講攏是伊的親身經歷嗎?」但書上說你跟初戀女友去安平運河邊玩,她家人反對,你很傷心,寫了歌啊,「你怎麼這麼笨?我不這樣講,你們記者會有故事可以寫嗎?!」
錄音檔聽著聽著,突然就笑了出來,勘破世情,全然做自己,他根本傲嬌天王欸。《文夏唱/暢遊人間物語》中,陳昇提到,乱彈阿翔在金曲慶功宴對他說:「欸,那個文夏是不是很難相處啊,為什麼有一次我跟他同台演出的時候,我衝過去要抱他,他突然一個拐子就把我推開了。」陳昇柔聲安慰:「阿翔,天王只有一個,我猜他是怕你弄壞了他的頭髮。」歐吉桑的不拍照和不配合,與他給乱彈阿翔的拐子,兩相對照,是否可以解釋成他對音樂和形象的執著?想通這一點,一切都釋懷了,檔案在文香大姊有事先走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那個心結也打開了。
未料瞥見電腦螢幕,同一天的檔案夾怎麼還有另外一個音檔?一頭霧水地點開,撲面而來唏哩嘩啦的雨聲。雨聲中聽聞我對歐吉桑說:「下雨了欸,老師你有帶雨傘無?」「無呢。」「按呢你按怎轉去?」「等雨停。阮兜就佇路對面。」「我陪你開講好無?」「好啊。」登時想起來,當日本來我們起身都要離開了,未料下了一場大雨,兩個人被雨困住了,有一搭沒一搭地尬聊著。
問愛看電影的他最近看了什麼戲?他答:「我問你吼,最近有一齣電影,足歹看,但大家都跑去看,大家都在講,但我報紙掀開來,看不到哪裡演,我要去哪裡看?」「《台北物語》啦,抑無我??你去看電影好無?」「免啦,我家己去看就好。」「老師你怎麼這麼討厭訪問啦?足歹鬥陣呢。」「無啊,較早起來,就愛化妝,愛想等咧欲穿啥物衫,閣驚講到朋友的代誌,費氣啦。中晝欲出門,朋友敲電話講欲約我食飯,但我想給你約下去了,袂使失信,對無?抑無,我予你問五个問題啦!」「好啊,好啊,你幹嘛去日本還改名夏邦夫?」「就想講去日本發展,換一个日本名試看覓啊,邦是國家嘛,我是夏日南國來的,夏日國家的男人,毋是叫夏邦夫嗎?」「你剛剛說你寫〈漂浪之女〉,是看了上百本言情小說,有感而發,你是看日文還漢文啊?」「中國冊啊,阮佇日本時代,講日本話,到中國時代,才學中國話,看中國冊。」
從日本時代到中國時代,時代的車輪,輾轉誤了青春,夏日南國的男人在夾縫中生存,絕口不提政治的他最後還是鬆了口:「電視開播,『群星會』很轟動,暗時,一群女明星予大官叫去陪酒,女明星攏一寡外省的,對大官講台灣歌沒水準,大官就共阮攏禁掉矣,阮的〈悲戀的酒杯〉變成謝雷的〈苦酒滿杯〉,〈新娘悲歌〉變成余天的〈相見不如懷念〉,好笑的是那些大官禁我們的歌,他們的小孩,新聞局的小孩喔,九○年代去西門町看日本合唱團,多諷刺啊。」時代沒有容身之處,寶島歌王盛年流落異國溫泉鄉,抱著吉他,按著客人的要求,唱著故鄉的情歌:「若唱出愈會想起昔日的故鄉情景,忍著忍著忍著,忍著目睭墘,熱情的珠淚,一時陣忍不住,煞來哭出來。」心聲也都寫在歌詞裡了。
錄音檔的話題轉到歐吉桑說隔天要去日本旅行,要去山陰、山陽,他說他要去吃一蘭拉麵,我趁機說老師,要不你回台灣,我閣敲電話予你,咱約訪問好無?「好啊。」那是錄音檔案歐吉桑跟我講的最後一句話。一切的記憶都不算數,原來記憶愁雲慘霧,是當天真正下了雨,聽著檔案中唏哩哩的雨聲,竟然有一種泫然欲泣的酸楚,歐吉桑並未拒絕我,但始終沒有給他打電話,我到底是辜負了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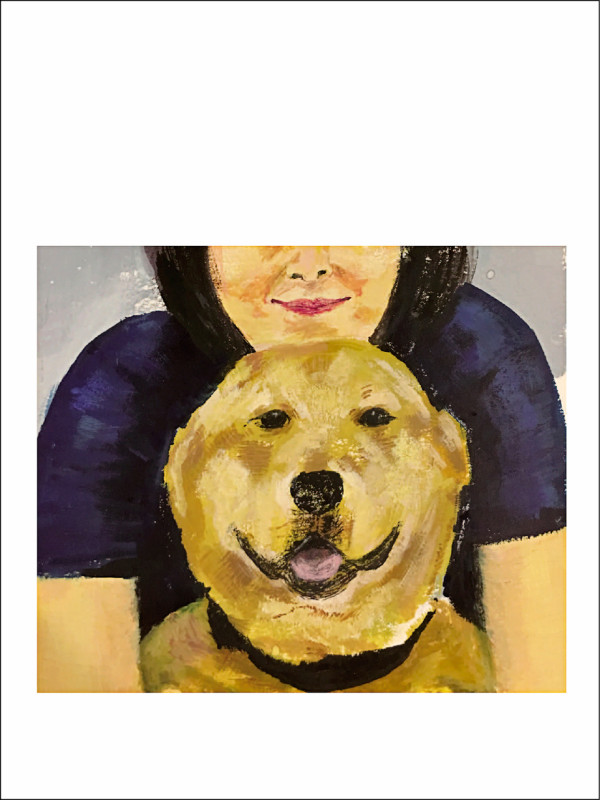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