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 林靖傑/王文興的純粹時刻
 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王文興。以「慢寫、慢讀」,信守文字信仰而聞名文壇。
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王文興。以「慢寫、慢讀」,信守文字信仰而聞名文壇。
編輯室報告:
 宜蘭南方澳拍岸的濤聲,以及地方文化啟發了在當地服兵役的王文興,而後將長篇小說《背海的人》的書寫舞台設置於此。
宜蘭南方澳拍岸的濤聲,以及地方文化啟發了在當地服兵役的王文興,而後將長篇小說《背海的人》的書寫舞台設置於此。
小說家王文興(1939-2023)於9月27日辭世,其獨特的小說美學成為台灣文學的珍貴遺產。《文訊》將於12月9日下午2時至4時,於台大文學院演講廳舉辦「王文興追思紀念會暨文學展」,本刊今日刊出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導演林靖傑的追憶文字,明日刊出小說家郭強生細數父母親與王文興的珍貴因緣。
 王文興極其在意節奏和選字,自述其小說就是樂譜,「把每個字當音符對待,停頓的部分是休止符。」
王文興極其在意節奏和選字,自述其小說就是樂譜,「把每個字當音符對待,停頓的部分是休止符。」
★★★
 1972年,王文興發表歷經七年完成長篇小說《家變》,筆鋒一針見血揭露家庭與社會的問題,乃至結構、語言形式上的創新,在當時文壇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被冠上「離經叛道」的「異端」之名。
1972年,王文興發表歷經七年完成長篇小說《家變》,筆鋒一針見血揭露家庭與社會的問題,乃至結構、語言形式上的創新,在當時文壇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被冠上「離經叛道」的「異端」之名。
◎林靖傑 圖片提供◎目宿媒體
 每一夜,小說家王文興在斗室內和自己搏鬥,而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的鏡頭撞見了作家的雕鑿精神。
每一夜,小說家王文興在斗室內和自己搏鬥,而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的鏡頭撞見了作家的雕鑿精神。
得知消息的隔天,我寫下:
 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刻畫了王文興私下忘我而狂烈的創作風景,他表示自己「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處求生」。
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刻畫了王文興私下忘我而狂烈的創作風景,他表示自己「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處求生」。
王文興離世讓我非常非常難過,我的難過有很自私的理由──因為王文興很純粹,而我跟他有連結(拍攝他的紀錄片),所以我幸而在這個俗世中尚有一絲跟純粹的連結,否則做為一個人要如何度過這無數個庸碌的歲月?
有幾個時刻,幾個鐫刻在腦海裡的畫面,經常跳出來,宛若眼前,讓我會心莞爾,或回味再三:
(然而,我寫到這邊便沒能再寫下去了,因為惆悵。)
今天,我將試著接下去,以下……
之一 :武俠人物登場
生平首次見到王文興,是由目宿媒體安排的、紀錄片導演與傳主的第一次見面討論。因為王文興住在台大教師宿舍,於是目宿便很貼心地跟王老師約在台大側門的西雅圖咖啡,時間是下午兩點。為了占到適合座位以及讓拍攝團隊製作人、監製、策畫、企畫事先與導演會前會,目宿跟我約提早半小時先到。大家都為即將與傳聞中的文壇異數、現代主義巨匠王文興見面而興奮戒慎。
時間接近時,卻下起一場少見的午後豪大雨,西雅圖咖啡出乎意料地人滿為患。幸好目宿媒體夠戒慎,他們比起我又更早到達,已在內邊找到一、兩桌空位。等著滿座的顧客流動起來,我們又機敏地占得第三桌併在一起。目宿加我共七人,我們空出中間的位置,圍坐著沙盤推演等會怎麼跟王老師討論。時間在緊張中流逝,有人發現已經兩點了;有人提醒著王老師從不遲到,只會早到;有人整理儀容彷彿下一秒王老師就會出現眼前;但時間過了兩點,王老師仍沒出現……然後時間來到兩點半。「這不尋常。」有人說。
有一、兩位目宿同仁不斷往門口張望,始終不見王老師的蹤影出現。我忍不住驅動導演本能起身勘景,除了注意大門出入處,同時掃視每個可能的角落,終於,在熙來攘往如雨後滔滔洪流的擁擠咖啡館裡,發現一個特別安靜的小角落,那是靠門口的一個位置,一個瘦小的老者與人共桌、氣定神閒地坐著看書,彷彿外界再怎麼喧譁,他只在他的桃花源化外之境之一立錐之地,老僧入定地徜徉在他的閱讀裡,彷彿已坐在那邊一個世紀之久了。
我沒見過王文興本人,但我見那內力深厚的定力,確定那應該是王文興老師了,我叫企畫來確認,然後我們穿越嘈雜的人群,走過去跟王老師輕輕地打招呼,如輕敲一聲引磬,把高僧從入定中喚回人間。
在會議中,王老師以他一貫的不疾不緩語調,輕聲說出他的想法,由於環境太嘈雜,所有人拉長脖子往他的方向靠攏,此時若是俯拍鏡頭,畫面會是一個由七顆頭顱構成的具有向心張力的圖形,那朝向的圓心正是灰白頭髮的王老師。好一個特別的磁場,安靜、深沉、不張揚而凝聚。在周圍散逸迸射的氣流中,那樣安然地穩住。
而周圍的那些背景人物,那些群眾演員,一定都不知道,那天午後他們參與了武俠片中高人登場的經典一幕。
之二 :家徒四壁新解
王文興的大學同學李歐梵教授說,他回國想跟王文興聯絡,只能用傳真機,因為深怕打擾王文興寫作。其實,每個跟王文興聯絡的人都知道只能用傳真機,只是親近的大學同學文學摯友,也只能用傳真機,特別令人感到王文興的純粹是那麼被周遭的人珍惜著。
對於「盡量不去打擾王文興」這件事,在他的學生身上表現得更為顯著。做為紀錄片導演,無法拍攝到被攝者的生活面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但拍攝之初我卻一直被告誡不要太打擾王老師,「進入他家?這不太可能,連他最親近的學生例如康來新最多也只是偶爾在他家門把上掛個小禮物,不敢按門鈴,更不要說進他家打擾他了。」得到的答案多半如此。
但做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決定打破這個戒律,我認為這是王文興老師決定要被拍攝時,就已經有的心理準備。於是在經過幾次拍攝後,慢慢建立彼此的互信,我與他的拍攝逐漸默契地由邊緣走向中心,有一天我終於進入他家──那是一個與想像中的大作家截然不同的場景。沒有環繞住家放滿書籍的矗立書櫃,沒有古董字畫,沒有珍玩收藏,沒有可拿來說嘴的品味家飾或裝潢……他家的牆壁,大片白白的,很乾淨,沒有長物。一個以閱讀和寫作為生的作家,他的書都到哪去了呢?倚著牆壁堆起兩層半透明塑膠收納櫃環客廳鋪展開來。在一次邀請年輕作家伊格言來拜訪並與之對談時,伊格言天外飛來一筆問說:「我幫楊佳嫻問一個問題,老師喜歡植物園還是動物園?」王文興老師凝思片刻,起身彎腰拉開一、兩個塑膠收納櫃抽屜,然後找出一張A3大小的裱褙好的報紙廣告,那是一隻灰熊壯碩的背影。王文興將這張圖交給伊格言,然後孩子般純真地笑了。
王文興是一個總和藝術家,他酷愛美術、劇場、音樂、電影、建築……但他的生命後期先是把電影戒了,再來把音樂戒了,幾十年收藏的電影光碟、音樂CD全部捐出去,再也不碰。他聽音樂不是像一般人把音樂放著當背景然後做自己的事,他聽音樂必須放下一切,百分之百專注聆聽每一個音符、每一個樂句、每一樂章的結構……但因為時間有限,所有心愛的藝術終究不可兼得,最後他選擇了寫作,戒掉了其他的藝術愛好。
而乾淨空白的四面牆壁,也是這樣逐漸變得單純的吧。別的大師的收藏是加法,他的是減法,直減到更趨近內心純粹的應許之地。其他都乃身外之物。
之三 :你對中國有什麼看法
台灣文學史把他歸類在外省第二代、現代主義派作家。大部分的人理所當然覺得他的認同是大中國,一開始我也是。有一次拍攝的空檔,王文興興沖沖問我:「你對中國有什麼看法?」接著他跟我發表了他的兩國論。那次讓我非常驚訝,他說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他七歲跟父母來台,一開始住屏東,念東港國小,那時他講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後來搬到台北,一輩子生活在台北南區,從同安街到台大教師宿舍,他每天的散步地圖是台大校園幅射出去的周遭區域,晚餐後酷愛逛公館一帶的二手書店。他活得很現代主義,尊重個人自由、追求藝術前衛性、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厭惡威權、厭惡偽飾媚俗、極簡……他年輕時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用言行、作品表現他的反抗。我想,他是個黨外人士,只差沒搖旗吶喊,而是用《家變》更深沉地表態。
之四 :舟山路出遊
拍攝到尾聲,我安排了一個閒散的午後,讓王老師散步校園。他選擇了往舟山路走去,裡頭有廢棄的校舍、教學實驗農場、親水公園……拍攝期間王文興老師難得這麼閒適。之前選定拍攝地點後,假如在他的生活活動範圍,有時他還會提早一天獨自去勘景、丈量從甲地到乙地要花多少時間,路線怎麼安排比較恰當,準備隔天精準執行。
但舟山路那次他沒有。我們的拍攝已到尾聲,他有默契地知道我想拍一個閒散的、未經安排的散步。沿途他如好奇的孩童,不時對暫時荒廢閒置的一排木頭平房校舍發出種種歷史身世的猜測,觸摸小徑兩側不知名的小花並發出讚歎,走到親水公園的木棧上,欣賞游在水中的大番鴨的大紅臉。當大番鴨爬上木棧跟餵食牠的小女孩追討手上的吐司,急得小女孩頻頻斥喝時,他又笑著趨前過去用他溫文儒雅的肢體語言,與輕柔的話語對大番鴨道德勸說,然後又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赧地笑了,像個國小三年級小男生似的……柯慶明老師說,王文興的感受力太強,一次出門所感受到的是常人的數十倍。所以他自己說二十八歲之後就可以不必出門,因為二十八歲之前的人生經驗夠他寫一輩子。
也許王文興小說裡頭主人翁的暴戾、孤獨性格,令人以為他是個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孤高之人。但其實對比於他在創作時絕處求生的暴烈,他實則純真得像個孩子,面對生命的未知謙卑得像天主所牧養的羊群一般。
之五 :最好的文學作品是《論語》
我喜歡聽他談最好的文學。在不同的時期他談到:「我最喜歡的西方小說家是福樓拜。」「最好的中國小說是《聊齋誌異》,它的結構非常好。」「我最近最常看的是宋明理學,假如有一天我必須一個人住到無人島而只能帶一本書的話,我會帶朱熹的《朱子語類》。」
拍攝期間他說,他很遺憾還無法克服《論語》,還無法感受它的好。
紀錄片完成了,上映又下片了。事隔五年左右,台大圖書館辦了一場放映加映後座談,我有機會再度跟王文興老師同台。這次他說了:「我兩個禮拜前終於克服了《論語》,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文學作品。」他總是這麼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又總是這麼有說服力地給了你意想不到的嶄新觀點,讓你熱切地、迫不及待想去重讀他說的那偉大的文學作品。我想他的誇張用語絕非為了驚人,而是他總是用最純粹的、百分之百的心力與熱情去感受、反芻,然後傾倒出來。
好多年中,映後座談與王文興同台成了我最期待的事之一。超越了年齡世代、職業身分、社會位階、生命經驗、成就高低……每次見面剎那總感覺一切世俗庸碌剝落,迎面而來那最清澈的一泓清泉,使我靈魂為之一振。那次台大圖書館的活動後,我一直期待著下一次映後講座同台的短暫交談,總覺得什麼時候會再被通知,然後我就可以又一次跟他面對面聆聽他對文學藝術甚至政治社會的新發現。
但後來機會一直沒再來了……
之六 :……
我還有無數個記憶,但我想,就像他的《星雨樓隨想》那樣吧,三百萬字的手稿,要挑選編輯成書,永遠有未竟之時,永遠還有無數個珍珠還未出土。就看日後的緣分吧。「有生之年來得及完成當然很好,也有可能來不及完成,那也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重要的是那個過程,填補那個空洞的過程。」(大意)王文興在紀錄片中講到正在寫的宗教小說時,如是說。
寫王文興的純粹時刻,於我,永遠有未竟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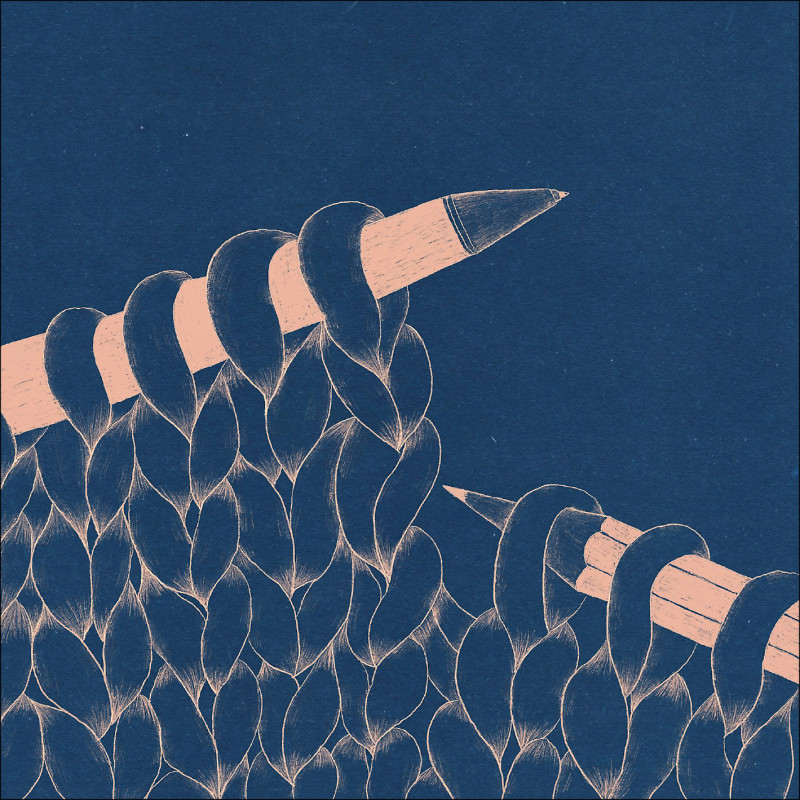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