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獎 獎 獎
參加林榮三文學獎頒獎典禮有感
◎吳鈞堯
十一月中旬,《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公布,該獎項採取先入圍再揭曉的做法,因此許多入圍者坐立不安,而許多得獎者(如李進文)也不諱言他們的緊張心情。
秋冬之交,是國內文學獎的豐收之際,「林榮三文學獎」加入這趟豐收之旅,從其得獎年齡分布,以及事前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不斷呼籲老將、新手一起爭奪桂冠,我覺得是有些意思的。
還記得《中國時報》、《聯合報》九○年代風光舉辦文學獎的盛況嗎﹖當時兩報文學獎都吸引眾多藝文界人士參與,我當時常參賽,更常鎩羽而歸,不過,主辦單位都會很有「人情味」地寄來邀請卡,歡迎蒞臨會場,給予得獎者祝福。
祝福對我來說,還真是談不上。當時的文學獎,都會集結得獎作品,許多文友錯過報載閱讀機會,也慶幸有書得以收藏,為了收集得獎著作,辛苦跑一趟是值得的。再加上主辦單位給予的贈品,更讓頒獎活動也成了一趟不折不扣的「豐收之旅」。於是我,一個文壇的生面孔,便常常站在角落,客氣地、小心地,喝著咖啡,吃著點心,更不時將目光來回台上與台下,對比榮耀和黯淡,在悲涼中,感受到義無反顧投注文學的悲壯。而這一種自虐的悲嗆,卻是督促我自己的力量。
九○年代,正是許多四年級生、五年級前段班風起雲湧之際。正確地說,這一群實力可怕的早慧者,早從八○年代就開始風光文壇了,如目前影響力依然深遠的張大春、曾經入選年度出版風雲人物的楊照、散文入選「經典三十」的簡媜、以老靈魂書寫姿態再起高峰的朱天心、豎立「都會文學」旗幟的林燿德、以《鹽田兒女》竄紅的蔡素芬,還有《聯合文學》總編輯許悔之、醫生詩人陳克華、得獎常勝軍張啟疆、剛獲得中山文藝獎章的林黛嫚,雖說大將崛起,可是有更多的大將早環伺著文壇,如黃凡、楊澤、劉克襄、陳義芝、羅智成、向陽、渡也、李瑞騰、蘇偉貞、平路、朱天文等,數也數不清的文壇好手。
要在民國八十幾年間崛起,猶如見縫插針,文學獎以及勤發表、常出書,是不二法門。八○年代,得個獎,就算不能家喻戶曉,在文壇間,也算有了小小知名度了,到了九○年代,除了大報獎項,地方縣政府也鼓吹文學,寫手們不必如從前,守著徵獎時間規律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教育部、梁實秋散文獎、《中央日報》等,而呈現一種動態,得時刻關心各地藝文,瞧瞧有無文學獎徵獎。
在這個同時,出版大老詹宏志也發出警言說,「文學已死」、「小說已亡」,這些被許多人當作「唱衰」的論調,給了詹不少困擾,在公開場合宣告說,他不是「唱衰」,而呼籲文體興亡有其定律,危機的突顯,也正可看出台灣目前的閱讀困境。
在這個同時,報紙副刊(甚至是雜誌)漸漸地編排輕薄化了,連載已屬鳳毛鱗爪,五千字以上小說、散文,見報機率大降。
很多人一度以為,地方性文學獎的加入,可以彌補、以及鼓勵好的作品,甚至是好的文學創作跟閱讀風氣了,可惜獎項繁多,多數卻沒有公開場合發表,而《中國時報》、《聯合報》已停止集結得獎專書,小說、散文跟新詩選集,在出版市場上更顯珍貴了。
參加《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的感慨,在徵獎前蔡素芬不斷的鼓吹中就已開始了。走到會場,散文決審委員廖玉蕙的一句話就問出關鍵,她問,「鈞堯你也來了,你也參賽嗎?」我答說不是啦,就來看看,「而且,彷彿不再合宜參賽了。」上一次參賽,約在民國八十九年,以〈女班長〉入圍時報文學獎小說決選後。早些年,張啟疆常得獎,引發的「關愛」眼神不勝負荷,鍾文音也因得獎,收到黑函攻擊,紀小樣更因為得了獎,在網路上被眾聲討伐,得獎的尊榮只在台上一閃,到了台下,卻是如此不堪。如此這麼著,文藝界這些年來,竟也流行「把機會留給新人」的呼籲,從文學獎起,到創作補助等。
許多五年級生,偶爾回首往事,偶爾或要心生感慨,在八○年代,何以就沒有這樣的呼籲?我深信這些想法,只會偶爾閃過他們心頭,寫了這些年,還能不知道所謂文學書寫,是自己在創造的嗎﹖鼓吹新手出頭,確讓老手們紛紛卻手,陳大為、鍾怡雯、郝譽翔、唐捐、袁哲生、張惠菁等,各自擁有十來座獎項的好手早不參賽,他們有各自目標,得獎已是其次。
對我來說,志不在此是其一,跟新手同台較勁,卻被撂倒的失敗感是其二。
不能說,老將出手,作品就好,但老將們不參賽,且畏於參賽,多少跟新手出頭的文壇風氣是關聯的。而過去這些年,鼓勵新手出頭的情形又如何呢?果然新人輩出,遺憾的是,大獎、首獎時也從缺,評審委員感歎文質不佳常有所聞,得獎者也多有「從一而終」情形:也就是,就得了那麼一次,再如何參賽,也沒有得過大獎,這跟九○年代,鍾文音、陳大為、鍾怡雯、郝譽翔、唐捐、袁哲生、張惠菁、紀大偉、張瀛太等人,連番獲得大獎的氣勢真有天壤之別。
有人懷疑,那些人,都是得獎專家啊,但要連番通過初審、複審、決審,獲獎,在不同的評審當中顯現其得獎之「專」,這當中除了「專」之外,難道就不是一種文學實力?這其中除了「專」之外,不也是一種錘鍊嗎?這錘鍊,在於一次一次自我突破,且接受挑戰,甚至是迎接失敗了。過去幾年,向享文壇最高榮譽的時報、《聯合報》文學獎,幾乎成了新銳大賞,可說是受了這股風氣影響。林榮三文學獎頒布後,蔡素芬力邀多人明年再來參賽呀。蔡的想法是,希望選出最好的作品,這跟時下的鼓動新銳風迥然不同。
我到了頒獎現場,方瀏覽入圍名單,很訝異鍾文音、蔡逸君、鴻鴻居然都參賽,後來頒獎,鍾文音獨獲散文三獎、小說二獎,蔡逸君獲得散文第一、李進文獲得新詩第一。
老將跟新手同台較勁,一般的認識是老手贏是應該,輸就難看,壓力全在老手這邊,可以想像鍾文音、蔡逸君、李進文、鴻鴻、嚴忠政、紀小樣、甚至停筆十數年的賀景濱也得面臨莫大壓力,而知其可能挫敗,卻仍不畏懼,這不也是文學的堅持?發表園地、創作跟出版補助,獎掖新秀有其必要,但文學獎似乎還宜回到作品本身,我們應該想的是這一年選出多少好作品,而不是這一年,選了那些人得獎?就我所知,駱以軍幾乎已經成為六、七年級生心目中的文學「教父」,許多人習其風格,而駱以軍的成就是奠基在《第三個舞者》、《遣悲懷》、《月球姓氏》等作品上,可不是他的老師張大春「讓」給他的。夜空無垠,只要找到位置,就能發光,不是嗎?願意比賽,願意接受競賽後的失敗,文學進化的動力,不也在此?期許更多優秀作品獲獎,至於他們是老是少,就不重要了,畢竟,一部好作品的壽命,遠遠超過人的壽命了。我想,不少人都跟我一樣期待,在文學獎得獎名單上,再看見張大春、簡媜等人的大名。
至於落選者,就莫傷懷了,多年前《中國時報》也依此法辦理,五名入選者獎角逐三個名額,我竟落選了。
這個印記,鑿得深刻啊,細節都還栩栩如生,當時的屈辱跟遺憾,而今提起,雖不至於是一種光榮,但的的確確,是一種深深的鑿痕。
至於鑿痕裡是什麼,就要我們,戮力往裡望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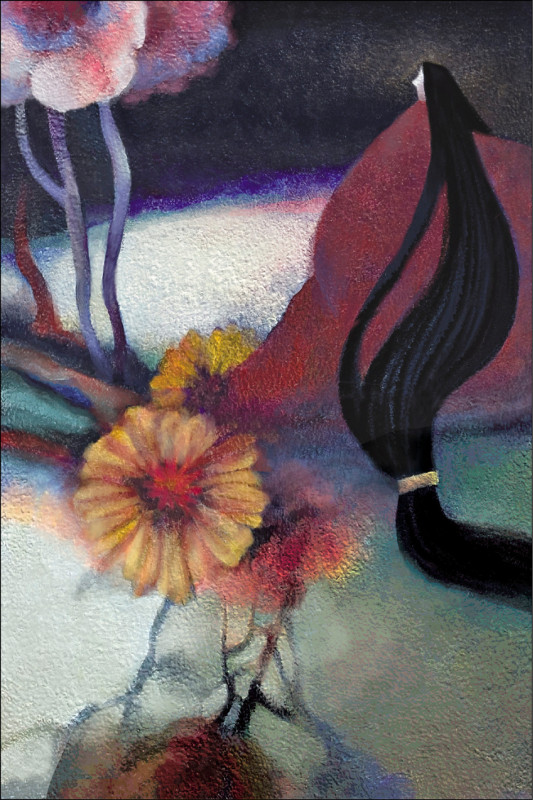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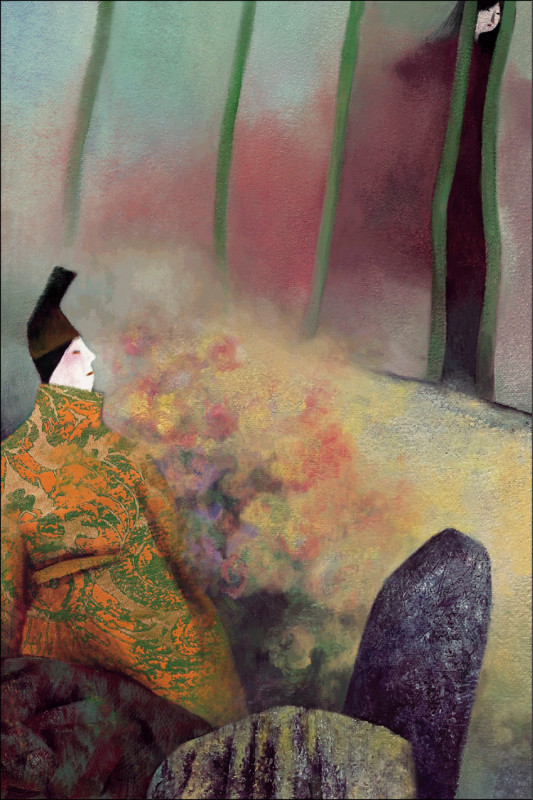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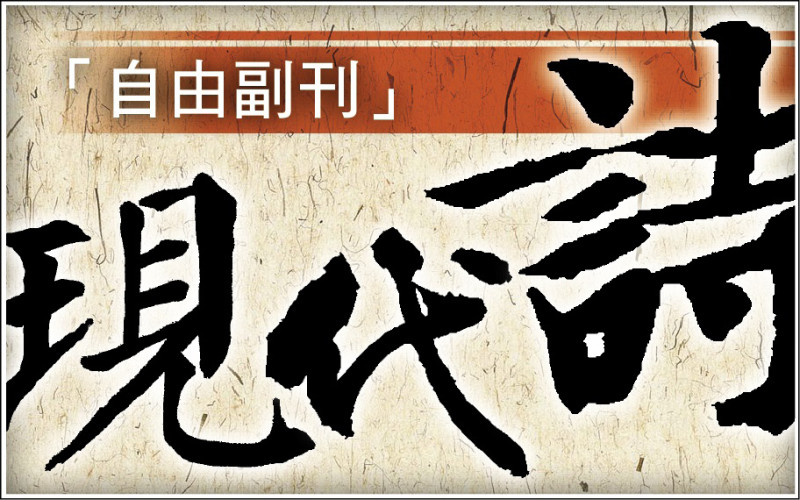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