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一屆 林榮三文學獎 新詩獎
首獎
潛入獄中記
◎李進文
帝國主義怎樣?你睡得好最要緊。
這些日子生病,你說眠夢會痛,但不必我來搖醒,
八字鬍吹出的口氣像魯迅。
真心話餓斃,唉,划入腹肚的番薯簽像絕句;
天堂或地獄不用聽診器,世間人勇健只要一張草蓆,
死活綑一綑,就結束日據時期?
最難消受是月娘,尤其牢牆外的童嘻──
長男志宏活二十一天。次男志煜活四個月又十二天。
四男賴悵活一年又九個月。長女賴鑄活二年又九個多月。
六男賴洪活一年又八個月。而且,你是醫生,
「我竟然是醫生……」你哽咽地說。
蚊蚋和跳蚤在硬頸插下的太陽旗,無非提示賴和先生
血的位置。病與責任令人軟弱,
不像你的小說;顯然祖父留下的拳譜你已荒疏,
反正練就一身正氣也踢不醒世界、揍不痛體制。
我看見你獄中床頭的心經、兒科醫書與顛倒夢想,
你也曾這樣軟弱渴求釋放,因為債
與親情一樣沉重,不是草蓆一綑就了事。
土地黏人都快五十年,你丟給誰養?
血紅的卷宗:「彰化警察署留置所」在大人桌上我瞥見
又驚見台語橫屍,就在和室地板下的密室。
舌,可以吊死賴和。你說:死不需要輸血,唯有愚昧。
四壁蕭索僅剩衛生紙,既勒不死,就留一截以書寫。
你問我怎樣來?噓!耳目眾多,只能長話
短說:我跋涉網路,攀漢詩、登台語,追蹤反骨
交錯的小說,以及信札和文獻,繞過你屋外那棵蘋果樹,
另一棵不是蘋果樹卻善心指路,又
在傍晚的懶雲掩護下,我潛入,帶一個口信
和一份報紙──不是你主編的,卻有八卦
山的消息,有彰化
一點點,一點點家鄉就夠你哭的。
報刊日期是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一號禮拜日勞工節──
(後一個禮拜不就是母親節?害你想起老母,真失禮)
頭條消息:勞工退休新制將上路,你細讀
多色澤的標題橫排不像遊行隊伍像一列電子花車。
唉愛、不愛在情仇兩岸嬉囂,而你屋外的落葉頭也不回,
悄悄掉落得像族群撕裂。財經版創啥貨?你問「網路」的台語
怎樣說?「春花──夢露?茫茫兮路?拐斷我的耳孔毛!」
第二次入獄(珍珠港事變當日),不想文學就想死,第九日
念佛號、讀陶淵明,看出你的心
以及肉體軟弱,我說:一些同志的批信被斜陽揭露,在書桌;
日頭撞上心頭,暝時留下一道淵藪。
怕牽累朋友?賴和先生你想太多,老友送報伕楊逵也沒怕過。
你必須以筆、腰桿和手術刀挺著……
「你必須回國──」我不會動員群眾接機,請安靜通關;
把靈魂分散活在某些人的肉體,只要有好靈魂就有好政府,
死亡不是絕症,會在另一處再生。
這個黨和那個黨在一桿稱仔兩端,愛與恨從不平衡。
我得走了,先生!口信已帶到。請把未標註日期的作品攜來,
國號不清楚就空著,等我們都確定了再一併填妥。
■李進文,1965年生,台灣高雄人。曾任職編輯、記者,現任職明日工作室總編輯。著有詩集《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不可能;可能》、《長得像夏卡爾的光》、散文集《蘋果香的眼睛》,編有《Dear Epoch─創世紀詩選1994~2004》等。曾多次獲國內文學獎。
得獎感言:
已經歲末了。回想一下,今年彷彿是我的「新詩年」,年初開春我出版了一本自己很喜愛的《長得像夏卡爾的光》詩集,年底又幸運地得到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的新詩首獎,這中間,我今年敢拿出來發表的作品也比以前多點兒了,這表示我比去年勤勞一些、進步一些。而這些,真的要特別謝謝給我機會的朋友,以及支持我的家人。
評審意見
對話、詮釋、辯證
評〈潛入獄中記〉
◎向陽
本詩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生平事蹟為題材,藉由賴和重要作品《獄中日記》為第一文本,採取與文本相互對話的後設書寫技巧,進行文本的再對話。賴和在日本治台年間的為義鬥爭圖象、文學書寫、編輯工作,以及對同志、家人的摯愛,透過在他過世(1943)六十二年後潛入「獄中」的「我」的筆下,一一浮現。獄中情節,宛然如真,賴和身影,躍然紙上,是一首能夠深刻描繪台灣歷史人物的好詩,也是一首能夠化史料殘篇為生動影像的佳作。
賴和一生,兩次遭日本當局下獄,一為1923年12月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第二次則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再度被拘,他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悲哀。本詩題目〈潛入獄中記〉,既是表露作者與賴和獄中文本的對話記,又有藉賴和獄中日記寄寓六十多年後的作者面對經濟面勞工失業、社會面族群相忌、政治面國家認同不一的感慨。在戰前與當代的時間換置之間、在真實與虛構的文本互為詮解之下,成功表現了歷史文本與現實世界的弔詭辯證,這是本詩最令人動容之處。而詩的用語,排除慣見的象徵筆法,融散文句式、小說敘事於一體,尤使本詩獨樹一格。 ●
二獎
La dolce vita
──義大利文,甜蜜生活之意
為我親愛的那人而作
◎凌性傑
我也會在生活的此地說他國的言語
讓脣齒輕輕開啟威尼斯與天空
陽光下橫掛著棉繩晾曬那些
一再被生活穿上又脫掉的身體
那些笑聲隔著門窗閃耀
玫瑰盛開一天有好多次
在臂彎所及開始一天兩個人
我要去哪裡?我們要往哪裡去?
兩種問法都教我們的人生離題
花園裡的歧路使我對你充滿鄉愁
除了眼前所見,我們已然一無所知
那是我和你之間,也是我們之間
一個世界瀰漫水霧
還有模糊的香氣
這時候如果沒有我,你要去哪裡?
如果我忘記你,無法分辨什麼是
生活、什麼是日常,什麼是去去就回
你願意為我把那些過往的事物一一
命名並且貼上重新使用的標籤嗎?
讓我無知的快樂著,想像世界靜止
同一時間做同一個人你也願意嗎?
你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他人
雖然有時兩個人不代表我們
但是用皮膚就可以理解所有
形而上的問題,至於形而下的疑慮
則在不斷起伏辯證的左胸底
我伸舌舔著單球冰淇淋
那是整座佛羅倫斯,文明的天氣
或者歷史的陰雨。當我們
並肩走向一個叫做未來的地方
教堂頂端又傳出信仰與鐘響
我只是這樣一個人信你不疑
在我們的境內有一種神祕
有一種美好的抵達我不想忘記
我們翻譯著彼此,做著同樣的夢
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所有的門
生活的甜蜜不在他方而在這
當下,讓我用聲音用簡單的思想
蓋一棟房子叫巴摩蘇羅,意思是
思慕太陽。哪裡都不想去了
就在這裡,餐桌上擺滿理想
我甘心在這裡把一生用完
就是在這裡,在睡眠之前
還有一點遙遠的光與暗
讓世間萬物安安靜靜
各自找到各自的房間
■凌性傑,1974年生於高雄。師大國文系、中正中文所碩士班畢業,就讀於東華中文博士班。曾獲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現任教於國立花蓮高中,著有《解釋學的春天》、《關起來的時間》。
得獎感言:
或許這是一個聲音與意義的結構,或許這是一個情感與思想的結構,而我試圖開啟它,繼續訴說生活種種。日常生活,幸運的是有日常、也有生活。我希望還有一些事物仍然值得我相信。人生而孤獨,可是許多時刻,我覺得欣然有託,生命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景觀。世間萬物亦有我們參與其中。走進未來,一定有什麼通貫於我,那一定是神祕且美好的。
評審意見
日常的艱難
評〈La dolce vita〉
◎李魁賢
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中奉勸年輕的詩人,「別寫情詩,起先要避免那種太熟悉與常見的題材;這(情詩)才是最難的」,又說「不要寫這種一般性的題材,而要追尋那些日常生活中給予你的事物;……以愛、平靜、謙恭的誠意,並且使用你周圍的事物、你夢寐的意象,以及你意念中的物象來表達」。
〈La dolce vita〉這首詩,對里爾克的話做了實證的詮釋,而又進一步反證了按照里爾克訂定的原則,還是可以寫好「一般性的題材」──情詩。能把一般性的題材,寫出超乎一般性的思惟和表達方式,令人感受到「愛、平靜、謙恭的誠意」,那「才是最難的」。
〈La dolce vita〉處理了「日常生活」的事物,平凡到幾乎「無法分辨什麼是/生活、什麼是日常」,但一種殷殷拳拳的恩恩愛愛,自然流露其間。這般「甜蜜生活」,可謂甜而不膩。採用平實的語言,襯托平實的日常生活,而自然的韻律感,似乎刻意但又不太固執的韻腳,甚至隱含的行中韻,配合著語言表達進行的順暢,在「說理」和「抒情」之間,達到極佳的平衡,充分透示了「愛、平靜、謙恭的誠意」和氣氛。 ●
三獎
尋找未完成的詩
◎林婉瑜
被書寫的母鹿穿過被書寫的森林奔向何方?/是到複寫紙般複印她那溫馴小嘴的/被書寫的水邊飲水嗎?/她為何抬起頭來,聽到了什麼聲音嗎?
──摘自〈寫作的喜悅〉,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陳黎.張芬齡譯
被書寫的母鹿穿過字裡行間來至
被書寫的森林:「這是火,火焰;聲,音樂,語言;
這是風,以及風的方向。」我跟隨鹿的足印,學習
辨認巨大世界更多陌生部分:星群座標,
葉的色澤,時間,曆法與季節;天,
日月,鳥以及飛行。(一行詩句的振翅
發動地球最遠處的颶風風暴)
鹿靜止於隱喻希望的辭彙旁(有沒有詩
足以召喚遠行的戀人,離散的時間?)踢踏,試探隱喻的強度
(以符號寫成,僭越符號?);被書寫的河流衝擊河床,
發出詩句被閱讀時的慨歎(記載深夜最末一秒與
凌晨的交界,海洋最遠與天的交界,理智
情感的分野,人與獸的分別);枝椏末梢,詩句變黃,落回土地
進入下一季輪迴(在一首詩的長度中經歷一生)
分行、斷句被輕盈躍過,鹿於留白處跪足
休憩(記憶起欲望、餓、痛、病,
老、死,以及重生);我走向下一次的詩句
夜間,筆跡涉足每條路徑,為事物命名(天空、土地、土地上的生命,
夜晚、白天、事或現實)夜鷺啣著思想的果實飛越我的額頭;
白晝,意義在日光下光合,將存在擴展得更為盛大(地圖未曾
標示森林盡處)。而我的步伐謹慎,如鹿的花色在夜晚仔細
被隱藏;而我的步伐堅定,如鹿知道每一個
納入眼中的目標,每次
前往的方向
靜聽,水流流過意義轉折處
水沖激岩塊發出血液衝擊血管的聲音
靜聽,被書寫的蝴蝶撲動翅膀
繞行尚未開放的花朵,飛行途徑構成神祕而隱喻的圖騰
昆蟲鳴叫如低吟經文。在一個被書寫的下午
或者是森林與鹿從真實世界找到我
將我寫入字裡行間?
被書寫的母鹿領我來至被書寫的森林,學習
廣袤世界更多陌生部分。我記得行旅最初
與最終,記得暗示與譬喻(和那些未及命名的)。雨季之後
天色的藍,燃燒過後餘燼的灰;藉描述浮現的
真實,藉描述而真實的想像,藉描述彰顯(或猶疑)的真理
我記得落筆前的猶豫,每一筆畫的堅定
眼淚般的墨水,墨水其下的眼淚;我記得鹿
和她的足跡
■林婉瑜,1977年生。曾獲時報文學獎,詩作入選《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詩卷》、《現代新詩讀本》等中外選集。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現為木馬文化出版社主編,著有《索愛練習》,編有《回家──顧城精選詩集》。
得獎感言:
滿高興在滿28歲前獲林榮三、時報等文學獎項,詩非為獎而作卻有獎嘉勉。年中去美國一趟,旅程有幾本詩集為伴,讀詩使我在異地安然;後來細想,其實文學也就是我精神上的家園、來處,我仰仗的事物。詩集《索愛練習》索冀時間、情感、想像、反問種種;而今我持續關注這些主題,在此詩中且擴及對詩的後設思索。詩不是刻意,僅是精神的自然反映。
評審意見
真理的條件
評〈尋找未完成的詩〉
◎鄭愁予
本篇作者首先在標題下引語是摘自辛波絲卡的詩〈寫作的喜悅〉,原詩的場景是一張寫詩的白紙(原始純潔的世界),「母鹿」(求生延代而又脆弱的命運),「森林」(自然界給予生命的維護卻又無助),這就是西方人文道德的視野,所以詩中慎用真理這個詞(真理在西方的哲思中,有多款寓意,可以是馬克思主義,一神教的經律,以及美學中美的極致)。辛波絲卡卻將自己在白紙這個純潔場景上主宰生殺的「欣喜」暗喻為對政治專制的反諷,說明當摹擬上帝權柄的同時也正是對抗上帝,只不過完成「人類之手的報復」。 本篇作者的詩想卻是借「母鹿」演出,而活動在「森林」的場景中,乃用明喻的力量羅列意象,突然間使場景廣大如宇宙洪荒,從風火聲籟到天象從晝夜到海天交際,以至夾述夾敘辯證思維中的主情主理、人性獸性、生命的困境和救贖,到倒數第二節:到「森林與鹿從真實世界找到我」大致可以從所列意象找出:水流──血液是長遠激情的,蝴蝶與花朵是美與性愛互動的,而昆蟲鳴聲則是生活日課的註腳,使人從吟聲裡解讀經文古典或宗教的傳承,也許這些才是尋找如何完成那未完成的詩的契機。所以前面三節的鋪敘便是作者懸宕的手法(未效隨辛波絲卡繞著中心捻攆子的巧匠手法),最後戲劇性地把被書寫的鹿和森林反轉過來成為書寫者,如此「母鹿」(此時是詩的慈念和靈思的化身)便從隱喻背後現身,帶領詩人去尋找, 並理出一串寫詩的關注。意味著詩應在求知性的,注重歷史的,強調真理的條件下完成,或者在這些條件中去尋的……這首詩的語言精度有些地方不夠(像鹿和母鹿不可換用),而詩語言明確度,未乖離理解邊緣,這些都是受評審人注意到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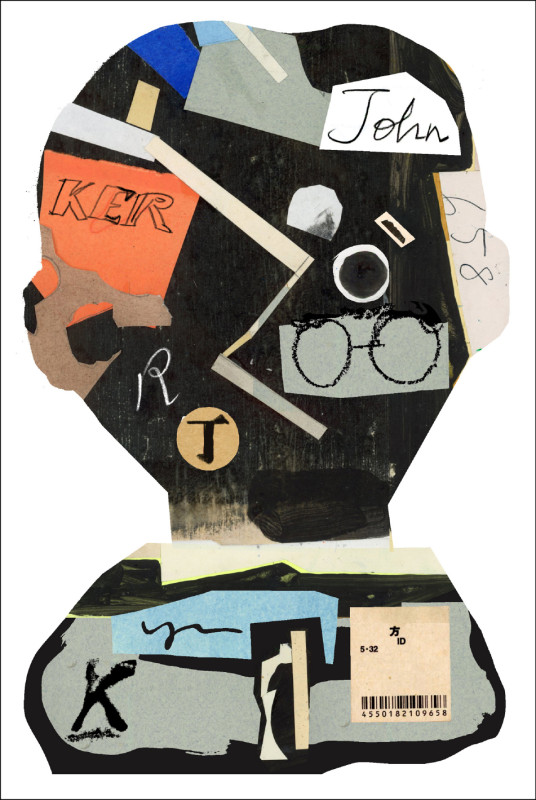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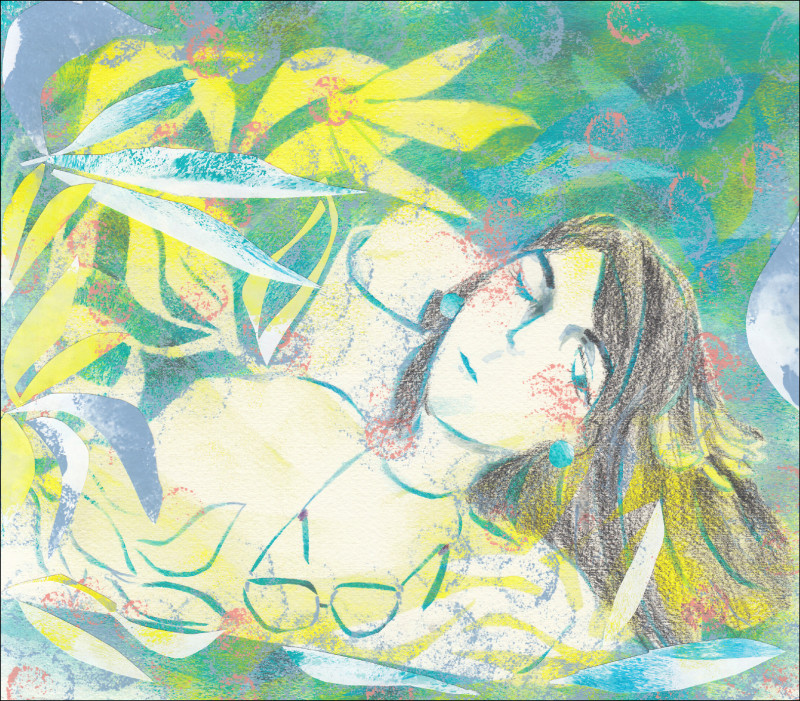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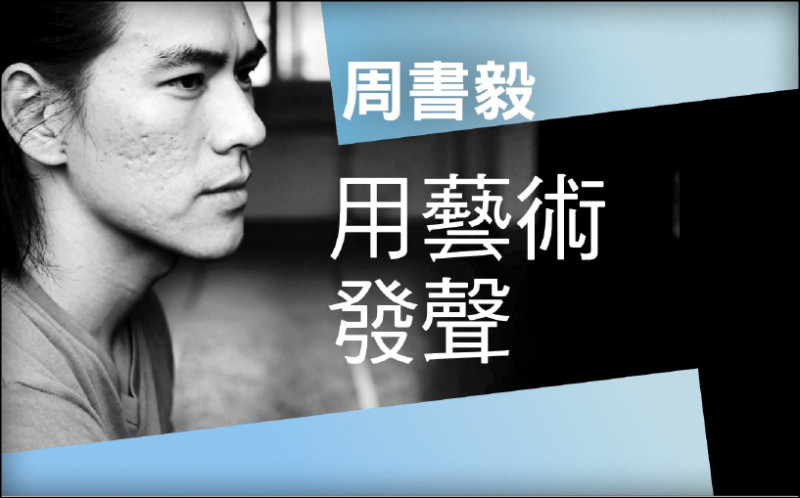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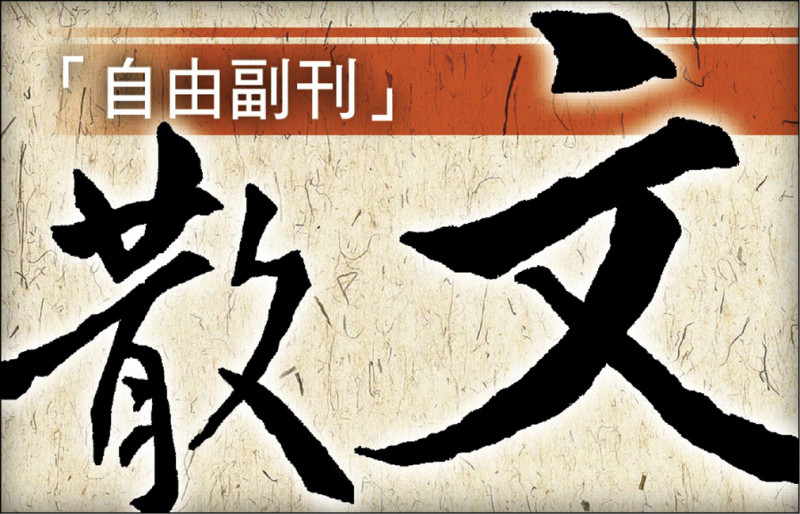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