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七宗罪】 貪吃之樂
◎焦元溥 圖◎顏寧儀
「無餐不歡;空腹不樂。」
在論文〈威爾第歌劇中的宴會與禁食〉中,音樂學者波松納提(Pierpaolo Polzonetti)以俄國哲學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格言開始,半開玩笑似地從這義大利巨擘作品裡歸納出七大「胃的音樂學法則」。「沒有什麼餐點會令人悲傷,但缺乏食物必然帶來痛苦」。前兩項開宗明義,點出食物之重要與用餐之愉悅。到了第三條,作者援引李維史陀(Lévi-Strauss,1908-2009)的人類學研究,認為共享飲食展現社會凝聚力;第四條則指名,只要有食物或飲品出現,「災難就不會立即降臨」。
唉,我多麼希望能夠同意波松納提的觀點。可依我看來,更接近事實的分析,是威爾第歌劇中,飲宴通常伴隨不幸。
要是加上〈飲酒歌〉(Brindisi),那更是災禍的保證。如此歌劇只有三部:匈奴王《阿提拉》歌還沒唱,預言者就告知血色凶兆;《馬克白》夫人花腔繞梁,篡位賊子卻見鬼魂現身;《茶花女》交際花舉杯逐樂,下一秒只見蒼白病容。若我們擴大到其他義大利歌劇,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董尼采第(Donizetti,1797-1848)《露克瑞吉雅.波吉亞》(Lucrezia Borgia)中也有〈飲酒歌〉,一曲唱罷竟見女主角送上棺木復仇,在場賓客全被毒斃。而莫札特《唐.喬望尼》最終場景,好色一代男在家縱情吃喝,三段助興音樂奏完卻來瘋女鬧場,接著更是廣場石像登門拜訪,將寧死不悔的登徒子拖往烈火地獄。就算只是有酒無宴,馬斯康提(Pietro Mascagni,1863-1945)《鄉間騎士》和威爾第《奧泰羅》中的〈飲酒歌〉也絕非善類:前者引出妒夫殺機,男主角隨之命喪刀下;後者本身就是陰謀,伊亞果的嫉妒讓所有人都跟著陪葬。
這一切舞台慘事,在在告訴我們宴會愈熱鬧,作曲家的音樂愈起勁,故事結局也就愈悽慘駭人。無論大餐或豪飲,最終飽食的總是死神。
正當的狂歡,我吃故我在
盛宴招致災禍,可不是義大利歌劇發明的玩意。「無論如何提心吊膽,人們還是不得不承認,若生活裡少了撒旦,就會乏味至極。」法國史學家米榭勒(Jules Michelet,1798-1874)侃侃而談,論證中世紀生活可以多麼悶煩:教會把人生看成試煉一場,小心翼翼不使延長,要求信徒順服等待、期盼死亡。這實在無聊到令人發狂,偏偏有人還信如此才能得到上帝獎賞。丹尼蓀(Isak Dinesen,1885-1962)《芭比的盛宴》裡那群「拒絕俗世朋友」,把「寒酸冷食配上一杯咖啡」當成珍饈美饌的挪威村民,就是頑固抗拒享受的清教徒。這究竟在怕什麼?教宗葛雷果里一世(Pope Gregory I,540-604)簧舌滔滔,把七宗罪都給了清晰註解。以「貪食」為例,他列舉五大犯罪細則:吃太早、吃太好、吃太精、吃太飽、準備太多。啊,以他所引之經文,信徒連找個調味醬都得下地獄,人世果然無間道。
但教會愈禁止,人們愈大吃。愈是天災人禍,就愈該及時行樂。1475年歐洲出現第一本以拉丁文寫成的印刷食譜,名稱就叫《正當的狂歡》,德文版甚至名為《道德上正當、合宜且受到認可的肉體歡愉》,作者還是梵蒂岡圖書館館長,等於要和神學家抬槓。或許我們應當反過來看,就是因為資產轉瞬即空,人民朝不保夕,既然災禍無可避免,那更是我吃故我在,絕不能放過任何大餐。如果你剛好有幾個錢,飯桌更是炫示財力的舞台,能被華麗裝飾的食材尤其可愛。「下水汆燙前先將天鵝吹脹及去皮,再將腹部切開,以叉子刺穿鵝身加以烘烤,並以麵粉加蛋調製成蛋糊塗抹表皮,同時不停轉動烤肉叉,將之烤至金黃色。如果你們喜歡,還可再將天鵝穿上牠的羽衣。為此在天鵝頸部需要別上木叉,使其頭頸筆直宛如活物……」15世紀中葉的《羅馬烹肉術》,就不厭其煩地教導讀者如何做菜如製標本。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中提琴協奏曲》引用日耳曼中世紀古調,第三樂章以民歌〈烤天鵝的人〉發展變奏,層層疊疊果如料理程序費功。更露骨的描寫則見於奧福(Carl Orff,1895-1982)〈布蘭詩歌〉:「我曾居住湖畔,健康美麗相伴……如今焦黑一團,烈火焚身燒乾;廚師將我翻轉,侍者端我備餐。悲慘呀!悲慘!」都說此鳥死前歌喉最靚,但這由男高音捏著嗓子,以假聲唱出的詭異曲調,配上合唱團「轉呀!轉呀!」的垂涎呼喊,顯然是最最悽厲的天鵝之歌。
而從天鵝的痛苦哀叫,我們也終將了悟,美食本來就代表殺戮。就算把烹飪當成藝術,也必須透過毀壞作品方能欣賞。難怪作曲家鮮少描寫食物。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的歌曲《美食》(La bonne cuisine),已是極為罕見的有趣嘗試:別懷疑,四曲〈梅子布丁〉、〈牛尾〉、〈土耳其雞胸〉和〈狡兔〉,歌詞真的就是食譜!作曲家順著食材準備與烹調步驟天馬行空,馳騁出奇幻誇張的音樂想像。但要說能讓聽眾跟著聞香嘗味,恐怕還是力有未逮。畢竟,聽覺和味覺,傳統上就被歸於美感經驗的兩端。所謂「美學」,主要也指視覺與聽覺的官能活動:這兩種感官通常伴隨空間距離,又和人體維生並無直接關係,向來被歸為知識層次的高級官能。反觀需要具體實感的觸覺與味覺,就多半進入肉體層面的低階討論。前者可做哲學思考,後者卻供道德批判。以形而上的音樂來描寫形而下的食物,本身就是悖論。
音樂如此,烹飪亦然
既然如此,那也就不能怪華爾頓(William Walton,1902-1983)和奧斯伯.史提威(Osbert Sitwell,1892-1969),要把史上最著名的滅國歡宴,描繪重心放在異教崇拜而非吃喝傾城。華爾頓是少數自學成才的作曲大家。牛津畢業後他結識家世顯赫且有文學長才的史提威姊弟。他們珍視華爾頓的原創才華,不只照顧其生活,更提供寬廣深厚的文化教育。當華爾頓以《中提琴協奏曲》等作品大獲成功,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合唱領域時,奧斯伯提議他就巴比倫覆亡夜,牆上現手寫下神諭的《舊約》故事創作,後來更親自剪裁1611年英王詹姆斯欽定譯本《聖經》,編整出《伯沙撒王的盛宴》唱詞。
這個故事之前不是沒有作曲家譜寫。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曾做清唱劇,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1865-1957)也寫了戲劇音樂,但再也沒有人能和華爾頓一樣,以強勁刺激的筆法描繪遠古異教世界的妖異傳說。奧斯伯的文本快刀斬亂麻,高度凝聚的結構,讓此曲一如作曲家所言,不像神劇或清唱劇,倒像「三樂章合唱交響曲」。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悲歌,聲情句句血淚。第二部分是伯沙撒王的盛宴。「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與這一千人對面飲酒。」金樽銀碗,吾王萬歲。此段旋律刺激銳利,流轉間又盡是史詩格局,既講述巴比倫城的奢華與罪惡,又一路逼出國王對異教偶像的敬拜:華爾頓苦思八個月,終能結合爵士樂手法與英國民歌素材,加上不惜工本的樂團配器,將黃金、白銀、鐵器、木頭、石頭、黃銅諸神一一以音樂膜拜。旋律寫得血脈賁張,絞盡腦汁的想像更成就豔麗繽紛的音色大觀,荒唐邪神淫靡混搭現代時尚音響,最後卻接上「牆上人手寫字,伯沙撒王當晚被殺,巴比倫就此分裂」的戰慄恐怖。第三部分則是以色列人的歡慶,管弦總奏配上管風琴,在渾然忘我、震耳欲聾的「哈利路亞」聲中歡樂結束。晚年華爾頓自己都說,無論他聽過幾次《伯沙撒王的盛宴》,每到結尾,他還是感到掩不住的興奮。
是的,掩不住的興奮。鋪張了那麼多樂器,設計了那麼多招式,還不都是要讓感官刺激無休,聽覺持續保鮮。音樂如此,上菜亦然,所有極工盡巧的縝密構思,都是為了搶在飽足感來臨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喚起食欲,塞進最多的品賞之樂。這樣看來,音樂和美食,美學天平上距離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遙遠。鋼琴家歐爾頌(Garrick Ohlsson,1948-)就認為,「不像美術或文學要把吉光片羽的靈感化為永恆,音樂和烹飪致力於剎那間的感覺,要在一去不復返的當下創造感動。」煎鵝肝的火候和捏壽司的力道,其掌握之精妙幽微,並不亞於鋼琴家對觸鍵與踏瓣的鑽研。更何況品賞食物可以是增強感受、析辨細微的最佳訓練。牛膝草和鼠尾草有何分別?茴香與荳蔻有何特質?都說裝飾音如香料能為樂曲提味,若真能搞懂各式食材,或許也就能判斷莫札特與海頓的曲式異同,以及拿捏蕭邦古典句法與浪漫精神之間的分寸。一如小提琴家史坦(Isaac Stern,1920-2001)自品酒中教導弟子塑造音色的祕法,鋼琴家羅傑(Pascal Rogé,1951-)也建議學生在研習法國音樂前能先了解法國烹飪藝術。鍋碗杯盤中蘊藏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地區特色與民族性格,音樂家在聲音中所思索的問題,答案可能就在刀叉間的香氣。
所以,貪食就貪食,愛呷就去呷。別管《聖經》怎麼說,去拜九天東廚灶王爺,年年都有糖可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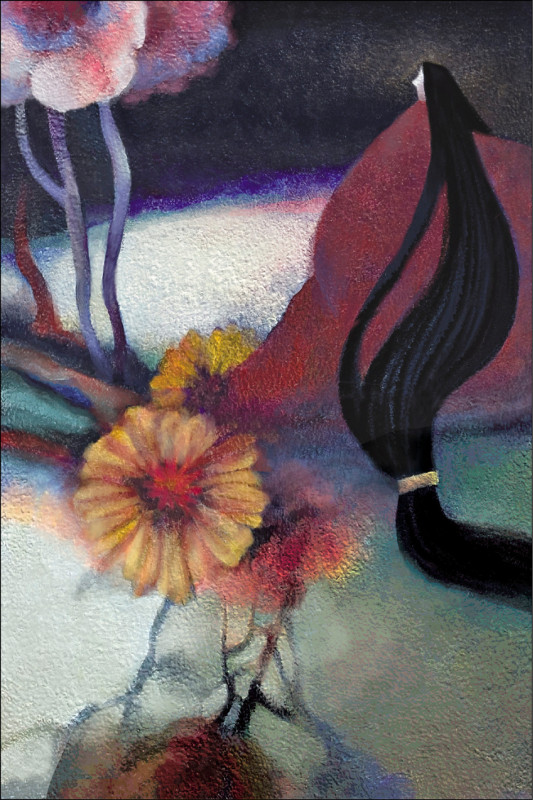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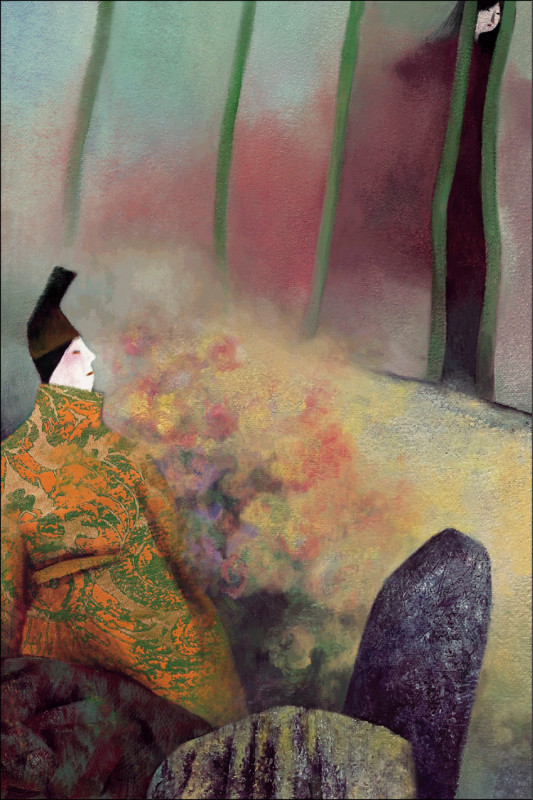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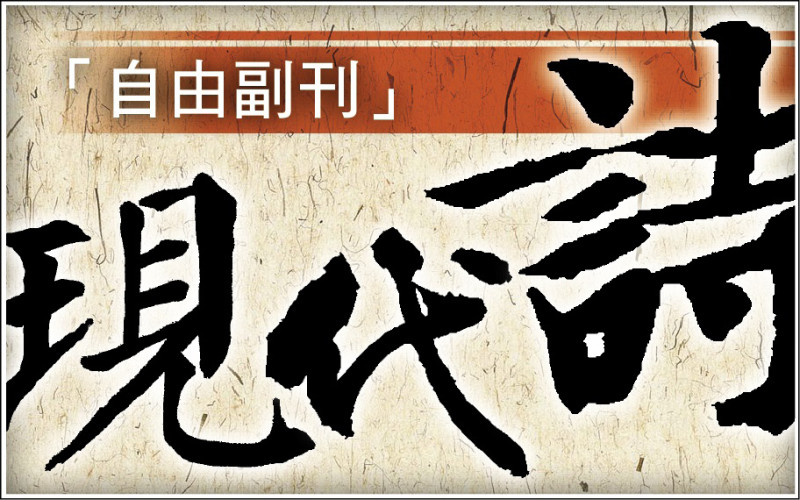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