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最後開的花
閱讀小說
◎片山恭一 譯◎陳寶蓮
連續一個星期的好天氣。報紙的天氣預報欄上,從北到南都是標著太陽記號。感覺永遠都是秋高氣爽的日子。不下雨,氣溫也不降,冬天永遠不會來。連白晝變短都無法想像。這永遠的秋天會一直持續到時間的盡頭。駭人的事件很快就過去了。心裡連像砂紙擦過的傷痕都沒有。同樣事情的重複。
只有由希永遠不會過去。她要求的安樂死離不開我的腦子。幸好,她最近身體上精神上都保持在安定的狀態,不再談到死。那時是一時興起嗎?我不認為。幫助自殺的問題和器官移植問題一樣,在醫療之路斷絕時必定出現。必須正面對應的時候總有一天會來。我不知道那時候怎麼選擇才好,也無法預測該怎麼做。
如果我答應幫忙,她剩下的時間會舒坦些。至少,可以消除呼吸困難的痛苦無限延長的恐懼,也因此有望減輕身體的痛苦。在她的病情裡,壓力使呼吸更加困難。
然而,實際的問題是,這事可行嗎?日本現行的法律,幫助自殺是要問殺人罪的。我不但會失去工作,甚至可能坐牢。更難的是,那條界線該畫在哪裡?我如何知道實施安樂死的時機?我能夠做出正是時候的正確判斷嗎?外行的我能分辨出再拖下去也是枉然的時點嗎?不論界線畫在哪裡,都會留下提早她死的遺憾吧。如果在我猶豫不決時她死了,又會留下讓她受到不必要折磨的懊惱。
我無法決定自己該採取的行動。關於她的死,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我即將要做的舉動本身毋寧更單純。幫助她死。但是我無法計算這單純舉動的風險。那個結果完全無法預測。而且是一翻兩瞪眼的賭博。最初交易的損失,事後永遠無法挽回。
我想起去醫院看她時那個計程車司機說的話。他在以前公司的人事部,有過裁員的經驗。那個假設問題「你會怎麼樣」的答案,「離開是地獄,留下來也是地獄。」……終極的二選一。必須從不想選的選擇中選出一個不可。像是弗雷德立克.佛塞斯(Frederick Forsyth)的書名。
天空飄著淡雲的十一月。星期天下午,出門隨便走走。我坐上電車,來到由希家附近的車站。以這個季節來看,天氣算是暖和。從咖啡店、漢堡店、還有好幾家手機店林立的景觀單調的站前走到大街,一彎進巷子就是幽靜的住宅區。直直的巷道兩邊是樹籬圍繞的舊式獨門獨院住宅。住宅後面蓋著連棟的中低層公寓。再仔細看,這景觀和諧的路上,處處可見像是蛀牙銀套子般的小巧整潔新樓。大概是住戶年紀大了或是往生了,兒女世代趁機處分舊屋改建的。
由希的家也在其中。舊的石柱大門後面,是一段高低差不大的石階路,兩邊是修剪整齊漂亮的杜鵑、刺葉桂花盆栽。凸出的弧形玄關裡面是個厚重的大門,門邊是她母親精心照顧的秋海棠。半掩在辛夷和橘樹後面的房間,是她的臥室。她當然不在家,屋子裡面沒有人影。我不經意地瞥一眼,把房子的樣子收進眼裡,像路過的人沒有停下、逕自走過。
走在綿延的坡路上。沒有特定的目標。我為什麼去她家?沒有任何目的地去她不在的家。或許就是知道她不在才去看的吧。將來有一天,她真的不在了。
去看她也見不到她的日子將永遠持續,直到我停止去她家的那天為止……是一種預備演習嗎?好對「她不在了」的未知事態做準備。為了盡量縮小現在和未來的落差。就像登山家讓身體適應稀薄的空氣做為高山症的對策一般。
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家眼熟的餐館前。外表看起來像間寺院。入口很窄,兩邊是普通的民宅。沿著土牆夾道的小路走進去,店面意外的寬敞。時間雖早,但是累了,決定先吃晚飯。
我招呼女服務生,坐在面向庭院的位子。我記得小窗外的那個石燈籠。和上次一樣,我點了店裡的招牌菜。不久,服務生端來啤酒和開胃菜。
「請慢用。」一切都沒變。松樹的鮮綠,還有紙窗阻礙下不夠寬廣的視界。除了由希不在這裡,一切都和幾年前來時一樣。大概菜色也沒什麼改變吧。
前菜之後端上來的生魚片,由希只挾起一、兩片。茶碗蒸倒是吃個精光。慢慢吃完一碗燴飯。沒有碰天婦羅。
「可以的話,你吃!」她把沒碰過的食物推到我面前。
「妳不多吃一點不行。」我隨意夾著剩下的菜來吃。老闆娘很善體人意,先為她上甜點。黑芝麻凍加甜瓜和梨子。是那樣的季節。我思索那時她說的話,立刻想起來。我獨自笑著。她提起養蝌蚪的事。
現在幾乎都只有暗溝了,但我們小時候市區裡到處都有小河流過。還有狐狸和樹林,也能採集昆蟲。我就讀的小學附近有個池塘,孩子們只用竹竿綁著繩子的簡單工具,就能釣起鮮紅色的美國螯蝦。她的故事也可以歸入那個少年時代記憶的一格裡。
「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假日,我們一家人開車去兜風,途中,在路邊的田裡發現蝌蚪。」她結結巴巴地說,「我爸突然脫掉鞋子走進田裡,撈起十隻左右。
我媽和我看呆了,因為他實在不像會做那種事情的人。」「那情景很超現實。」「可能是為了讓我高興。」「然後呢?」「我剛開始時不喜歡,但是摸過以後,覺得它們好可愛,吵著要養,於是把蝌蚪裝進所有容器帶回家。」「開始養東西了。」「我把它們放進水槽裡,到寵物店買飼料餵它們。」「無法想像妳照顧蝌蚪的樣子。」「我用自己的方式認真照顧它們,」她有點意外地說,「我爸看到,說這樣很難得,用日記記錄下來怎麼樣?」「觀察日記嗎?」「我每天觀察它們腿長出來的樣子,寫在筆記本上。」她做個呼吸,「你知道蝌蚪一定是左腿先生出來嗎?」「不知道,」我笑著說,「這麼規律嗎?」「不知道,但我觀察的蝌蚪都是這樣,沒有一隻例外。現在想起來也覺得不可思議,自以為有了驚人的發現,把筆記本拿給老師看……」「他恭喜妳,說這是諾貝爾獎級的大發現?」「只是很普通的評語,妳觀察得很仔細。」「他不知道這個發現的重大嗎?」「誰知道,他是理科老師耶,我很失望。」「大人就是這樣拔掉孩子的創造之芽。」「害我好辛苦地去放生長大的青蛙。」我露出訝異的表情,「那是土蛙,」她說明原因,「是不棲息在城市裡的蛙類。如果放生在住家附近,它們會掠奪本地的青蛙繁殖場,必須把它們放回原來的棲息地不可。」「理科老師在某些地方是頗專門。」「對才小學三年級的孩子說這些?」「那妳怎麼做?」「我爸開車載著放進幾隻大土蛙的水槽,載到當初抓到蝌蚪的田裡去放生。」服務生把我的甜點端來。我想著每天盯著水槽觀察蝌蚪的小由希。當然,我不認識那時候的她。我們相遇是在上大學以後。但我卻感覺好像認識小時候的她。她像只讀了一學期就轉走的同學留在我心裡。
她雙手包著茶杯,從紙窗縫隙茫然望著外面。甜點盤子裡留下沒有動過的甜瓜和梨子。
「吃點水果吧,」我勸她。
她沒看甜點,而是看我。
「怎麼了?」「沒什麼。」不久,茶杯端到嘴邊,以分不出是溫還是燙的表情無聲地喝著。
服務生來收餐具時,她的菜還留著。
「吃得不多哩!」服務生說。
走出玄關時天色已暗。灑水的石板路柔和地反射照在腳邊的燈光。院子裡的松樹頂端映著屋簷漏下的黃昏陽光。院子角落放著一個小石磨。裡面有水,旁邊備有竹勺。她像發現什麼,走向石磨,舀起一勺水,蹲在地上,灌進鋪在腳邊的圓石上,然後回頭看我,兩眼發光說「你看!」我蹲在她旁邊,仔細傾聽,聽到深邃的鈴聲。好像是水滴到埋在地下的甕中的聲音迴響。她告訴我這個裝置叫做水琴窟。
「我在電視上看過,這還是第一次看見實物,就離我家這麼近。」甕的產地是四國的香川還是德島。是從那裡大老遠地運到武藏野附近嗎?我接過勺子,也舀水灌下去。不是水多聲音就大,這樣反而會彼此排斥,變成單調乏味的聲音。第二次我珍惜地把水一點一點地灌下去。
「我在一本書上看過,水流到地下是為了傳達對死者的思念。」她凝視滲入小石頭之間的水說,「或許水琴窟本來也有這個意思。」我把勺子遞給她,她輕輕搖頭說「夠了」。我把勺子放回石磨,站起來催促她離開。
「我得這個病時,心想能活到三十歲嗎?」她沒有起身,「幸好能再見到你,帶我去了很多地方……」話聲突然歇止。遠處的湖面微波盪漾。
「想再活十年,很貪心呵。」「又在想無聊事了?」她沒回答我,只是仰臉望著我。
「我要是健康的話,會想其他的事情。」她的視線沒有挪開,「雖然是帶病延年的人生,我還是有自己要想的事情。有太多了,可是……什麼也沒做的都過去了。」四周已完全暗下來,我朝著車站的大致方向走去。不知何時下雨了。雨絲不大,街燈照見的部分雨絲看起來透明。
不知道天空在哪裡。地面與天空之間籠罩著朦朧的霧氣。無數的雨滴以隨性的角度切入霧裡。
路旁的房子門窗緊閉,像是害怕潮濕侵入似地,安靜無聲。雖然亮著燈光,但是窗簾緊閉,傳不出一句話聲。葉子掉落的常春藤像噁心的生物爬在油漆斑駁的牆上。橫巷中偶爾閃出一條人影,消失在小雨中。轉角的麵包店,隔著寬敞的玻璃窗射出帶橙色的光。我經過時,窺看店裡,沒有顧客,像是老闆的男人獨自默默地在櫃台整理發票。那個孤獨的安靜方式給人超越時間的印象,好像單獨切下那一塊,就是一幅奇里科(Giorgiode Chirico)的畫。
漫步雨中,想起和由希去過的地方。
雖然是不值一提的地方,沒什麼新鮮的事,但再小的細節都令我懷念。大概不再有機會一起重遊舊地了吧。她說的話、小小的動作、微笑時也像悲哀的表情……不久都要失去了。一旦失去的東西,再也不會回來。這麼單純的事情卻讓我感覺像是醉得腳步不穩,每跨出一步都像走在浮橋上那樣放心不下。
雨勢沒有變大,不曾停歇地繼續下著。走在頗有年歲的櫻樹下。不知要往哪裡去。沒有計程車經過。順著路走下去,應該會到大街。走過幾個街區,碰到一個小兒童公園。水銀燈下,不鏽鋼滑梯發出暗淡的光澤。公園四周也種著櫻樹。最裡面那棵樹幹特別粗,輻射狀岔開的樹根四處隆起泥土,像從地下冒出來似地。粗粗的樹幹從一半高處向上開枝散杈,正是落葉時節,還有些葉子留在枝杈上。沒多久那也會飄落散盡,讓位給新冒的芽。
我停在公園前,仰望樹梢。跨過低矮的柵欄,走到樹旁。輕輕觸摸光澤濕亮的樹幹。吸足雨水的樹皮變得柔軟。我閉上眼睛,集中意識。冰涼的觸感中感覺有某種纖細的東西流過。是這像在運送長眠地下的死者想法般的流動,告訴櫻花樹到了春天就綻開淡粉紅色花的嗎?由希會活到那個時候嗎?會留在我此刻駐足的這個世界嗎?觸摸樹幹許久。冷雨打過長著小樹瘤的樹皮,有微溫的觸感。我像沙漠植物尋求水分般吸取那份溫潤。水的味道變濃。被那味道吸引,想起雨季時兩個人去鎌倉看鳶尾花的事。那是什麼時候呢?回溯記憶,是前年的梅雨季節。不過是兩年前,她還能做那些事情。於是,我又陷入往事難追的思緒裡。過去的歲月沉沉地壓在肩背上。
那不是特別有名的景點。是間不在一般觀光行程上的小廟。穿過山門,通往大殿的路旁開著繡球花。細雨滋潤了雨天微光中的繡球花朵,幻化淡紫天青的色澤。寺裡的池塘蓮葉蓬蓬,碩大的錦鯉優游其間。我們撐傘走過石橋,欣賞細雨輕打的鳶尾花。
大殿像在進行佛事。低沉的誦經聲穿過雨幕流洩而出。她突然問我。
「你認為有天堂嗎?」孩子氣的問話中隱隱帶著迫切的氣息,緊緊扣住想付之一笑的我。因為是微妙的問題,我無法立刻回答。沉默之中,她又說:「我剛上小學的時候,家裡養的狗死了,是在我出生前就養的蘇格蘭牧羊犬,已經很老了,我懂事以後牠就一直在我身邊,對牠的愛戀自然也深。」「妳一直都有養狗。」我說。
我聽她說,最後養的那條狗在她不能親自照顧時請朋友領養了。
「牠要死前的幾個禮拜,要帶牠去散步,牠都不肯走出小屋,食物也幾乎都剩下沒吃。」她繼續說,「好像也不是生病,獸醫說只是年老體衰。最後那幾天時呼吸也困難,經常發出微弱的聲音,像在哀嚎。一聽到那聲音,我就難過得受不了。爸媽說打針讓牠安樂死好了,我當然反對。我也知道牠很痛苦可憐,可是打針讓牠死,更可憐。就算牠自己希望那樣,我也受不了。」她像徵求同意般抬起臉,我默默點頭。
「我媽說,希斯上天堂以後就沒事了……希斯是牠的名字。和艾蜜莉.勃朗特小說中的主角同名,是我媽幫牠取的。」她像在追憶名字喚起的狗的風貌。我思索小說的內容。我小時候讀過文摘版的《咆哮山莊》,但記不得內容了。
「我從小起就聽了很多有關天堂的事,」她繼續說,「我也相信天堂。認為實際上是有那個地方。在那裡,每個人都很幸福,是沒有疾病痛苦的好地方,我腦子裡知道希斯也會去到那裡。」她猶豫地停下來,稍微降低聲音說。
「爸媽趁我睡著的時候找獸醫來,打針讓牠安樂死。我醒來時,希斯已經死了。那是預料中的事,我沒有責怪爸媽,因為我知道他們也是出於無奈,只是我不能接受眼前發生的事情。」我提醒她注意腳邊。她停下腳步,看著前面的水潭。然後抬起臉,茫然望著山門。清幽的寺院裡細雨無聲地飄落。
我的腦子和周圍的景色一起被白得透明的雨絲封住了。她再度舉步,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地說。
「那天是星期天,我比平常晚起,確認狗死了以後,也沒去摸摸牠,就折回自己的房間,趴在床上一直哭。哭了好久好久。我邊哭邊想,我為什麼這麼傷心呢?希斯上天堂,應該變幸福了,我也這麼相信,難道是為了別離而傷心嗎?是為了不能再和牠一起玩、摸牠的身體、聽牠的叫聲嗎?我想當然也有,但這不是真正的理由。我發現這之間的不同。那天,我在床上發現我為狗死那樣傷心的真正理由。」她那清澈的眼睛看著我。瞳孔深處隱隱徘徊著怯弱的陰影。
「我無法相信有天堂,我心裡很清楚。」她移開視線看著遠處。
「直到現在我也無法相信,從狗死的那天以來,一直沒變……我無法相信天堂的存在。」我不覺握她的手。她沒有反握。頭髮裡雜著白色的東西。那是雨滴反光。她轉過頭,和我視線交接,我沒有擁她入懷。不久,不約而同地邁開腳步。
片山恭一
(katayama kyouichi,1959-)
生於日本愛媛縣。現居福岡市。九州大學農學部畢業後, 於1986 年以《跡象》一書榮獲「文學界」新人獎,正式步入文壇。
2004年因其《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改編的電視劇及電影熱映效應,點燃純愛小說熱潮,創下321萬本的銷售佳績。主要作品有《世界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轉動著》(新潮社出版)、《別相信約翰藍儂》(角川書店出版)。
以及已發行中文版的《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滿月之夜,白鯨出沒》、《雨天的海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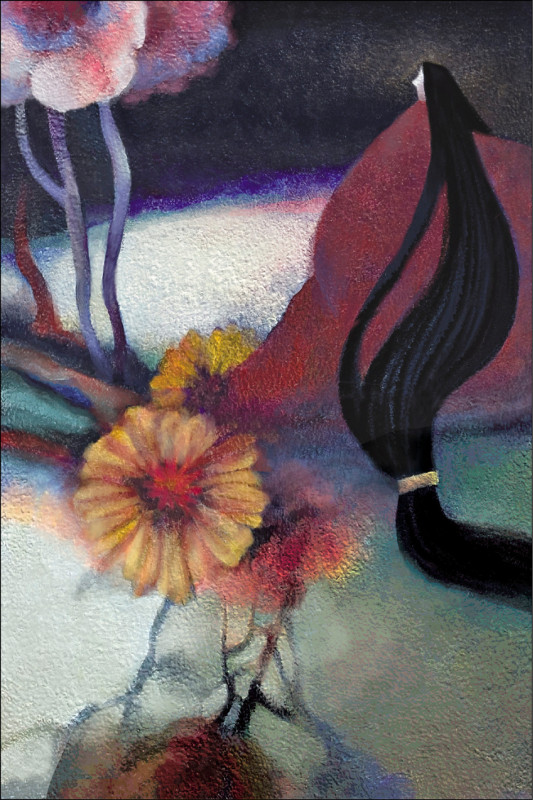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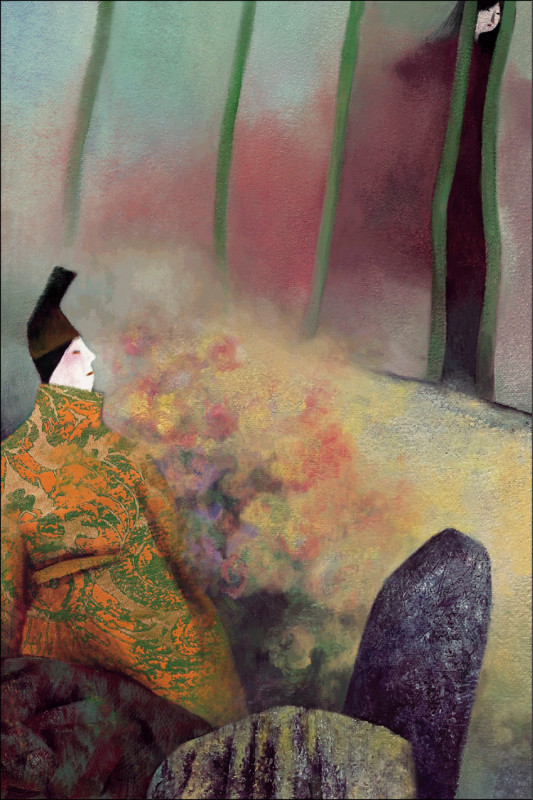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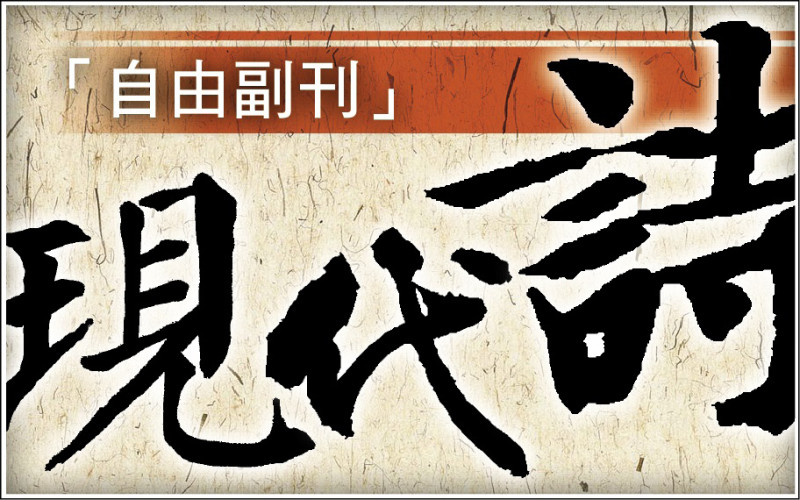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