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老房子的外婆麵
◎廖之韻 圖◎王孟婷
記憶中有一幢老房子,獨門獨院的,除了推開大門後的前院,還有後院,把主屋像擁在誰的懷抱裡一樣包圍在中間,而主屋不是現在流行的透天厝,是帶著木造印象,但實際上是磚瓦建造的,有著三角形屋頂的平房。或許是因為那支撐整體的屋樑過於顯眼,總會讓人以為這是個木造房子,甚至聞起來也有一股舊木頭的味道。
老房子是嘈雜的。地板上同時會響起好多腳步聲,紛紛踏踏的;空氣裡不時有誰隔著房間叫喊另一個房間的人,要不就是客廳裡的電視平劇節目傳出青衣花旦等的伊伊呀呀;黃昏時,賣甜饅頭的老伯,踩著機器腳踏車也來上一段特價叫賣;夜再深一點,連後院大水溝裡青蛙也唱起了合奏曲,伴隨發春貓兒的悽厲嘶吼,是不得安寧又習以為常,一覺到天明的夜晚。
吸收了各樣聲音的老房子,同樣的也飽含各式氣味。光是進進出出十來人的體味就夠多了,更別說前院的夜來香飄送進來的幽香,還有後院桑椹熟了的香甜味,甚至堆放著雜物但從前是雞棚的小竹棚,似乎還都留著雞臊味。
或香或臭的味道交雜出老房子曾經的人事,儘管事過境遷,某一年曾經盛開到令人聞了暈眩的夜來香,或是一日之間突然沒了的桑椹樹,似是融入老房子的某處了。然而,怎麼樣也比不上屋子最末端,廚房裡的食物滋味。
廚房連接著後院,有兩道門,一道紗門,一道木門。木門平時是敞開的,用一塊磚做門檔,只有晚上就寢或是沒人在家時才關了上鎖。
紗門似乎比木門來得可憐,誰經過就是順手一開一關,也不懂得輕聲開放,孩子們往往呼嘯而過,就是一陣乒乒乓乓的,偶爾外婆聽得受不了會叨念上幾句,但才幾歲大的孩子怎會記住呢?再說,把紗門甩得乒乒乓乓,其實還滿有快感的。
唯一能把脫韁野馬般的我們拉回來的,是吃飯時間。吃飯時間一到,菜都上桌了,怎樣也得放下手邊的事,乖乖坐到餐桌前。不然就等著聽到自己的名字從飯廳喊到客廳,從巷子口喊到巷子尾,還會有熱絡的鄰居路過正在遊戲的國小籃球場時,順便通知一聲:「某某某,你們家在喊回家吃飯了。」但是,坐上飯桌後,可千萬不能先夾菜吃,要等輩分最長的大人(通常是外公與外婆)都坐定了,才能動筷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從小吃飯就吃得特別慢,所以通常是最後一個下桌的。很多時候外婆會坐在一旁陪我,順便把剩菜撥一撥或清一清,就像普通家庭主婦常做的那樣,見著盤中留下兩三片菜葉,或幾塊燉肉,丟了可惜,再吃一餐又嫌少,就統統又進了她們的肚子裡。外婆也是這樣,但她揀著剩菜吃時,不像是為了「清光」什麼,反倒有著一分悠哉,像是古早時候一邊聽戲一邊就幾碟小菜和一杯好茶的公子哥兒,或是幾個婆婆媽媽吃著零嘴閒聊的午茶時光,那樣不覺得是在面對一桌子殘羹剩菜。
母親說外婆也算是千金大小姐吧!聽說曾外祖父是昆明的商人,在昆明那個四季宜人又繁榮的大城市,加上做生意的人勢必交遊廣闊,見的世面也比較多。偶爾,外婆看到現代人賣玉賣得貴,還會嗤之以鼻說,在當時他們那裡,玉掉在地上都沒人撿,隨便一個孩童的帽上都鑲著一塊玉。不論她說的是真是假,或有多少誇大成分,但也可見外婆是生長於怎樣豐饒的地方。
少女時期的外婆就被曾外祖父帶著上餐館、進咖啡館,連與做軍人的外公約會,都是相約於某個咖啡館內,點一杯咖啡、談談心。在咖啡館約會即便是今天,也算情侶間一件很浪漫的事,別說在民國初年有多時髦了。
或許,正因為成長背景的關係,即便嫁給了一位軍人,然後跟著政府來台後,靠著外公的津貼與自己在育幼院做老師的薪水,在不算優渥的日子中又要拉拔十個子女長大,按理,生命之光應該早被消磨殆盡。但是,等到我懂事後認識的外婆,怎麼看都在強悍中透露著一股優雅與嬌氣,就像老相片裡的大家閨秀,始終透露出淑女的端莊氣質。
然而,外婆卻從來不提她的出生背景,每次在桌旁陪我,一面吃著肉末,一面總愛跟我說過去逃難時的故事。說怎樣把金塊藏在襁褓中的姨媽的棉襖裡,怎樣又暈又擠得坐船到台灣,諸如此類每天聽下來,聽到都會背了,但她仍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像個說書人般「說故事」。小時候聽起來,真的像在聽故事一樣,不覺得這些歷史記憶有何珍貴之處,但長大後,卻又焦急著當初沒有聽她說完全部的細節;等到思念時,往往為時已晚,可我還有好多興趣想知道外婆的「故事」呢!融合了二十多個民族的雲貴地區,菜肴料理也是那樣充滿變化與獨特滋味。現在街上三、兩步就可見標榜著「滇緬菜」或「雲南菜」的飯館,裡頭不外是賣著酸中帶辣的熱炒等菜肴,每逢路經這些館子,或是進去點上幾樣來嘗,總會不禁跟記憶中的味道做比較,不斷往記憶底層挖掘,試圖找出同為雲南人的外婆的料理,與現在街上常見的雲南菜有何異同,而內心也總會納悶著:「外婆有做過這種口味的料理嗎?」答案往往是模糊的。外婆是雲南人,外公是浙江人,從中國來台灣後又必須配合著這裡的食材,又要迎合外公的口味,外婆的料理似乎跟街上賣的「雲南菜」有所出入。
然而,再仔細探究,外婆也嗜辣,與外公做的帶著酸甜味兒的江浙菜又有些許不同,而且她幾乎什麼都敢吃,這倒像極了印象中的雲南料理,連昆蟲都能裝上一大盤端上桌。
幸好外婆始終沒有讓我們在餐桌上面對一盤駭人的不知名蟲類,頂多只會出現豬嘴唇之類的食物。她一面用刀切片,一面用手拿了嘗,直說好吃,還訕笑只敢看而不敢吃的我笨,說我不懂得吃。在我看來,一個孩子若是沒有極大的冒險精神,大多不會輕易嘗試豬嘴唇這樣的食物吧!撇開一些讓我敬而遠之的料理不談,外婆做的菜可還真好吃!一盤肥嫩的蔥油雞,曾讓我捨不得放下筷子,肚子明明吃到撐了,還貪戀著盤中傳出的蔥絲混著的雞肉香味,十足一隻饞貓樣。長大後照食譜作了幾次蔥油淋雞,雖然味道也不錯,但就是做不出當時的蔥油雞味道,不知道是美化了記憶,還是外婆真有什麼獨家祕方,現在也不得而知了。
此外,豌豆粽與三角糖包,也是我念念不忘的。端午節前一星期,老房子的後院就會出現用臉盆盛水泡著的粽葉,入蒸籠後,陣陣粽香頓時瀰漫整個屋子,雖然天氣炎熱,但聞到這味道卻有種幸福的感覺。除了一般包五花肉、花生、香菇、蛋黃等的肉粽與什麼都不加的鹼水粽,外婆的粽子還多了豌豆粽這一味。像是市面上常見的花生粽,但是把花生改成了青豌豆,與糯米拌勻了包在粽葉裡,除此之外什麼都不加。單純的豌豆、糯米與粽葉,蒸熟後是那樣純粹的香,倒是解了肉粽的油膩,又帶著健康概念。
三角糖包則像是包餃子或做肉包時,順便做給孩子們的甜點心。與做包子相同的麵團,一樣稍微壓平桿圓了還留有厚度的麵皮,餡料卻不是絞肉,而是櫃子糖罐裡的紅砂糖。一大匙紅砂糖就這樣直接包在裡面,再用手指頭捏緊麵皮的三個角,成為三角形模樣,但在最頂端又稍稍露出個縫,等到蒸熟了,糖化了,這道縫隙隱隱透出紅砂糖融化後的晶瑩色彩,誘人在還沒咬下前,先用舌尖舔上一口。但是,要小心燙!三角糖包裡的糖,溫度比想像中高上許多,也正因為如此,每個吃著糖包的人無不一面吹著氣,一面臉上又是滿足的笑容。
三角糖包與豌豆粽現在偶爾在市面上還會發現有在販售,雖然味道肯定與外婆做的不一樣,但也算能一解剎然上湧的懷念滋味。然而,「外婆麵」卻真真切切只能在記憶裡尋獲了。
「外婆麵」算起來該是我給起的名字。偶爾,老房子裡的人會不那麼規矩得都圍坐在餐桌前吃飯,或是外婆偷了個懶,我們的餐食就不再是菜配飯,而是一盤水餃,或一碗麵。外婆煮麵十分隨性,有什麼食材就煮什麼麵,但又與什麼都加的什錦麵不同,她煮的麵簡單許多,雖然都說不出名稱,但也各有巧妙。有一回,外婆說要煮麵,問我們要吃什麼麵,我馬上憶起前些天吃過的,加了些許白胡椒粉的麵,但無可奈何年紀小不會形容是什麼味道,解釋了許久,不斷說著:「就是上一次吃過的那種外婆麵啊!」加上我又嘴甜,總是說最好吃的是「外婆麵」,從此「外婆麵」在家族中流傳開來,成了外婆煮的麵的代名詞,可以指很多種不同的口味;但是奇妙的是,只要是我跟外婆說要吃「外婆麵」,她就一定會煮出我說的那一碗「外婆麵」,也就是最初我說不上來是什麼的那一碗麵。
小時候說不出來「外婆麵」是什麼,大了後依然不會形容是怎樣的滋味,似乎刻意把它收藏在心底深處,就怕放在外面會被遺忘了,每次總要等著吃到了,才會笑開了的說:「這就是『外婆麵』!」從昆明來的外婆所做的菜,究竟是不是所謂的雲南料理,在走出吃飯的雲南館子後,對我來說已經無所謂了。隨著老房子改建的大樓愈來愈高,外婆看起來卻愈來愈瘦小,直到有一天隨著春雨埋進了墓塚,外婆的料理似乎也跟著失傳;我多後悔沒有趁著她還在時多跟她學一些手藝。
那神祕的只有外婆一人知道配方的「外婆麵」,那熱鬧的老房子,宛如散於風中的花兒,只在某個等候紅路燈的路口,悄悄地飄落肩上,成了嬰兒般的胎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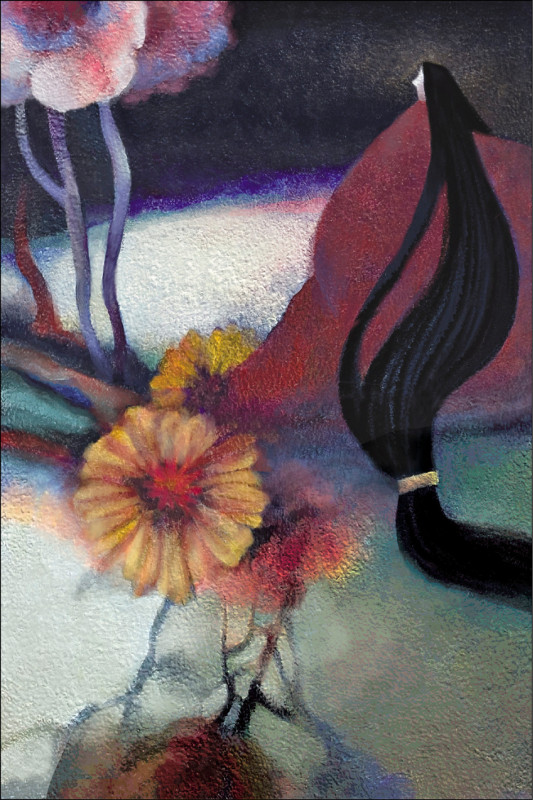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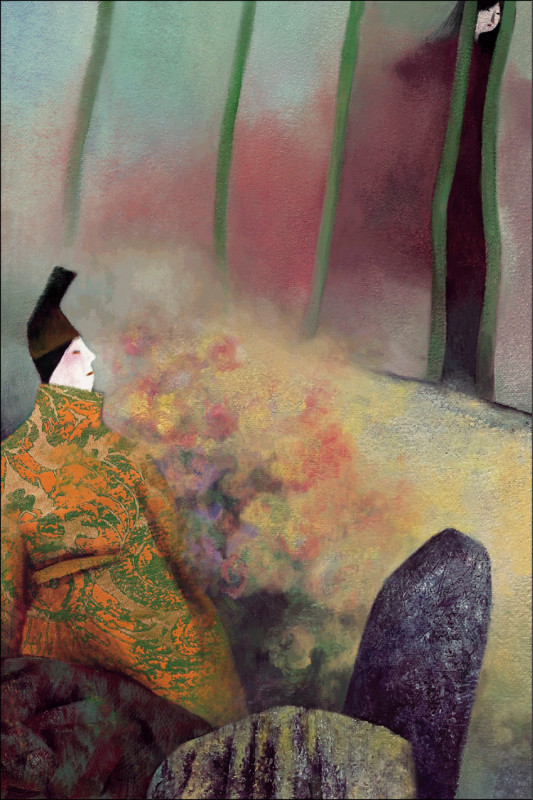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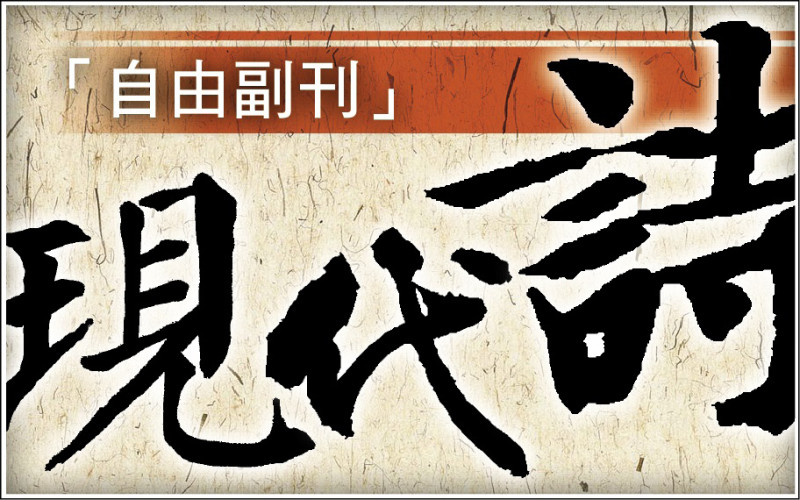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