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草木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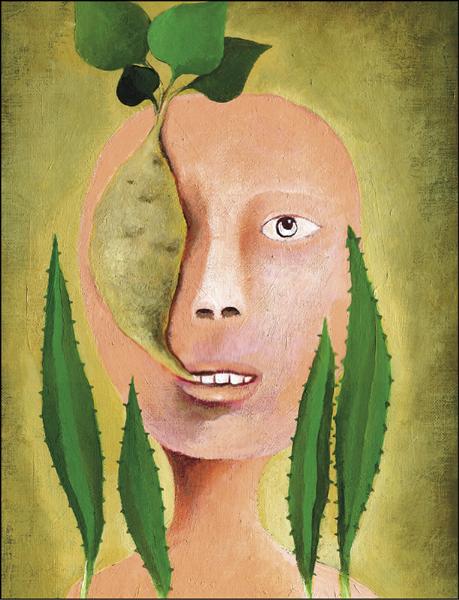 圖◎王樂惟
圖◎王樂惟
◎李喬 圖◎王樂惟
前言
2014年8月,我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情世界──回到未來》完成了。
──本來在腦海「排隊的」還有三個素材;第一個「進場」的《荒城之怨》,寫了近萬字,這時心中靈思一閃,把它撕了。這些作品,自己清楚,形式內容主題,已然不能超越前作十多部長篇作品,那又何必狗尾續貂?於是決定「李喬長篇小說」就此收場。
我已八十一歲,叫做暮年,晚年也。
一生歲月,除了服役三年,兼課與主持電視文化性節目,在北市混了十年之外(夜宿北市鮮有連續兩夜),我的生活園地、觀察、思索環境,都在苗栗「山線」這個空間。長年習慣於沉思冥想的人會知道,處身的空間,連思想意念都會受到影響甚至「造形」的。
我來自深山僻壤,初中階段讀的「蠶絲科職校」,以上山採野生桑樹葉為主。二十五年教職一直在苗栗鄉間,退休三十二年了,始終不離四面環山,青翠田園的苗栗公館地段。朋友很少又都在外地,子女更是散居四方。一隻家犬,妻子專寵,我這個人,書房群書外,最親最密的還是草木與群山──群山,草木填滿我心靈內外。我有時晨晚感覺又置身童年時期那種,身心內外都是草木,而恍然彼此一體的感與受……
人類存活基本是草木所賜,而人類以草芥為鄙卑的代稱。不知他人感與動如何,我一生尤其到了老年,日夜時分,是滿懷對草木的感恩;草木與我的種種,在老年歲月,幾乎取代我人世的點滴……
菅草
我記憶的底層,最清晰而「豐富」──浮上來的是菅草,菅草叢、菅草「排」,滿眼的淡白淡黃菅草花叢(又稱芒花,客語稱「娘花」)。
我的童年故鄉在苗栗草莓勝地大湖鄉之東,「番仔林」是跟泰安鄉接壤的地方。台灣歷史上有原住民「漢化」的名詞;我這一群是「番化」的漢人。(番,原字是蕃,歧視味太重,所以拿掉草字頭。)
──實際上「番仔林」是泰雅人舊居地,無論耕作打獵都不適合而遷徙;漢人得到默許才移入的。
這段交代是在說明:「當年」番仔林是真正荒山莽野。那樣的山野,草本植物最強悍的就是菅草。
在我童年記憶中,茅屋住家外面,除了造林全力照顧的「福州杉」,小庭院(客語「禾埕」),一角菜園之外,蒼青巍峨高山下,就是無窮無盡的草萊;眾草中占居老大的就是密集菅草;高一至三米,抽出草鞘的雙刃葉面指天直立,三分之二之後才微微橫挺或下垂。
何以以雙刃形容菅草?因為兩邊葉緣有細密的「葉齒」,尖銳不輸鋸齒,不小心一碰觸,必然流血一片。還不只物理性的傷與痛,而是其痛超越常態。因為菅草葉緣的小鋸齒上含有「矽質」;破皮觸及肌肉所以……
這是菅草族自衛本質吧。
而我的童稚歲月和菅草、菅草叢關係密切……
五、六歲以前的小孩,在我那年代在家難免捱打。我的情形比較幸運:哥哥只被賦予稟報弟妹該打的「案由」,至於動手則不許──而由老爸老媽「執行」。
我家屋後的菅草常被修理,所以身材沒有那樣雄偉,菅葉比較細瘦下垂,但是還是茂密濃厚。
我捱父母修理,除痛疼難忍哭叫幾聲外,總是躲在屋後矮叢的菅草「家裡」,幽幽細哭「療傷」。
另外就是,父母吵架,父親偶爾會動手;偶爾的偶爾媽媽也會還手。
這時我逃離「災區」之道就是躲在屋後菅草叢裡……
「他她相打,哼!不好!」我在草叢裡忍不住呵斥。
「呼──呼!」小菅草好像回答我。
「他她仰般會相打?」(仰般:為何)。
「吁吁……呼苦……」
「……得人惱!」我向菅草說:好討厭!
我說著,左手向身邊小菅草們揮去……「哎唷!」
我左手背疼痛!喔!兩道刮痕,小菅草葉割我!
「吁嘻……」小菅草葉左右上下翻飛。
我要打它!打……它打我做什麼?我伸腿滑著脫出菅草叢。
「我沒有打你……啊!」我正開口責備,卻發現「情況」:小菅草叢上段,裡面,那高壯的菅草幹被「伐掉」一大片,葉片削掉,比我還高的菅草稈半乾指向天空。
「……是你們……」我好像聽到它們……
是啊!是爸爸砍伐它們……
我想我不能怪小菅草割我手背……
我還是常常喜歡躲在菅草叢裡:卻也學到技巧:不要惹那雙面刃的「葉刀」,鑽進菅草叢底下,一些乾葉就不怕了。這裡好像老鼠小蟲也不敢進來,乾乾爽爽的;下小雨雨水也進不來。
菅草叢下,比外面人間安靜安全多了。這一念一直到老常存心底。
有趣的是,我的性格,我的人生,某些方面有像菅草或菅草叢。簡單看:社會人叢比菅草叢複雜多了,可怕多了。
菅草屬「禾本科」。早年在台灣,織菅草為防風牆,甚至屋頂牆壁都是菅草編造的。牛耕年代,芒草(菅草)是耕牛主要飼料。
秋天山邊菅草花(芒花,娘花)一片一片淡黃或淡白茫茫,好看,也引人心焦(愁)。
童稚歲月,我最親近的就是菅草,而我這個人種種似似有些菅草質地。菅字客語是「官」;本音就是「官」。查段注《說文解字》可證。
蕃薯
蕃薯,近年稱「番薯」,大概加草字頭,「蕃」有野蠻未開化意。向來在台灣稱呼「外來的」,或外來種植物都加上「蕃」字;例如「蕃豆」、「蕃瓜」(南瓜、「蕃石榴」(石榴)、「蕃蒜」(芒果)、「蕃鴨」等。坦白說,受過文字訓練的人,硬以番代蕃,頗有意象模糊之感。
在客族老一輩人對於「蕃」的「感應」,除野蠻之外,指人「蕃蕃」卻有正面稱讚意:形容正直坦率,不拐彎抹角的人格特質……
蕃薯在我生命史上是最大的「恩物」。
本人十二歲以前很少「碰過」稻米,主要裹腹物就是蕃薯;補助食物是藕薯,「生香蕉」(未成熟的)等。
那個年代窮人靠蕃薯填腹,很平常;我同住山村的人大都這樣,不過我家境況更嚴重。
家父參與「農民組合」,又是地方頭頭。1928年2月「大湖農組分部」成立,次年「二一二事件」發生,家父就被「限制住所」,租田為佃無門,只能在原住民近鄰面積約十五、六甲山坡地「種植杉林」,期間二十年──替「頭家」管理除草。杉木出售時,主佃七三分配。這期間地主賜留約兩分地植種蕃薯為生,另外就是巖石嵯峨,或溪水邊緣不穩狹隙種幾叢綠竹麻竹,桃李蔬菜等。這就是我童年活命「資源」。
這一段交代可知,那近兩分地薯園是我家活命唯一倚靠啊。蕃薯是「活命恩公」。
蕃薯,旋花科、牽牛花屬。早年只有「紅蕃薯」、「白蕃薯」兩種。現在以人工配種產生多種色澤與食用重點不同蕃薯了。那個年代種「紅蕃薯」算是奢侈品──紅薯較甜但產量少。現在有白紅黃橙紫各種顏色;還研發「食葉種蕃薯」。
在那個年代,蕃薯葉是主要「蔬菜」;採摘時很小心,不能一叢全採,而是分散各摘幾片──怕傷害整叢的成長。
蕃薯是主食,形式上可不能每天三餐食用相同「形式」。平常是:早餐,蕃薯剁成三角四角形小塊「煮湯」,和湯食用,中餐吃整條連皮煮熟的蕃薯,晚餐講究一點,有時享用烤蕃薯。三餐都一樣,唯一「配料」是鹽巴。
在特別的日子可以吃到「蕃薯餅」──製作工程不簡單:找到空魚罐頭,去上下底、拉平,然後以粗鐵釘,一排排釘穿,找到寬十公分左右,長五十公分,厚一公分半左右的木板;木板中段挖掉略小於打好洞鐵皮的「空間」,然後把穿孔的罐頭鐵片釘蓋那個空間,那釘孔的反面要朝上。
「刷板」一頭抵著放在地上的盆子,人,坐在盆子邊,左手扶著「刷板」,把洗淨的蕃薯由上而下在「刷板」上刷搓──部分經刷板掉落盆子,部分從刷板兩邊落下。總之都成小碎片或粉末了。
把刷成碎片的蕃薯捏成小拳頭狀,鍋裡澆少許油,鍋子熱了,薯團下鍋,略予壓扁──火不能太猛,不然油不夠多,薯餅瞬即燒焦了。這是不得了的美食。在我們來說。
如果沒有油煎餅,那就搭架炭烤也是不錯的。
最奢侈食法是,盆子裡碎薯上澆七分滿的清水,然後輕輕攪和,之後碎薯以「漏杓」撈起來。再一道手續是:拿來另一盆子或水桶,上面蓋一層紗布,把除掉碎薯的──略濃的粉水輕輕倒入,這樣碎薯除淨,留下才是沉澱的薯粉。薯粉沉澱了,最後上面的淨水倒掉,桶底成塊的「蕃薯粉」現形了。那是那個時代窮苦人頂級食品,各種烹法在此不贅。
──現在郊遊賣點是「炕蕃薯」。蕃薯以草木燃燒過後成為炭火或餘燼狀態,蕃薯投入,然後外蓋乾土,約十餘分鐘撥土取薯,那冒煙的「熟蕃薯」真正是人間美味。
不過在我童年,記憶中少有這樣「奢侈」享受。最難忘的是「生蕃薯充饑」:我山居外出,先要走半小時以上陡坡──以七、八歲學童行走,到國校要兩小時。清早下陡坡,坡底有一座伯公廟,我們會從書包拿兩條生蕃薯藏在廟對面草叢中,「用途」是回家上坡前啃啃生蕃薯補充體力也。記憶中,那生蕃薯不曾被老鼠之類偷走,很感謝。
有一台灣式笑話:某日某王爺郊遊,誤了回府時間,只好借宿農家。無肴招待,只好從「豬菜」──蕃薯莖葉中挑選較鮮嫩的炒為一碟奉上。王爺驚為天下名菜。問何名?答說「過溝菜」。插種蕃薯以土壟形態栽種,莖葉往往越過隴底攀到隔壁壟上,聰明農婦說是「過溝菜」。
現在食品科學昌明,知道蕃薯葉是特優蔬菜,而蕃薯的營養價值高過「白米」多多。
──在孩子進國小國中年代,午飯晚飯,老婆經常會在米飯裡夾雜幾塊「黃蕃薯」──那年代最受歡迎的蕃薯。孩子們盛飯時往往為爭奪「黃蕃薯」而吵成一團。我會真正勃然大怒。我自己盛飯一定會「避開」蕃薯。妻兒知我「怪癖」,替我盛飯時也知所迴避。
然而近年來,連著兩、三天菜飯中不見蕃薯影子,我會惱火色變……
蕃薯謙卑地成長地下,「土土形貌」而營養豐富,便宜好吃,人人可以享用。
台灣形貌像蕃薯而盛產蕃薯。我是吃蕃薯長大的,我這個人內外都有蕃薯的質性。我愛好蕃薯,我疼愛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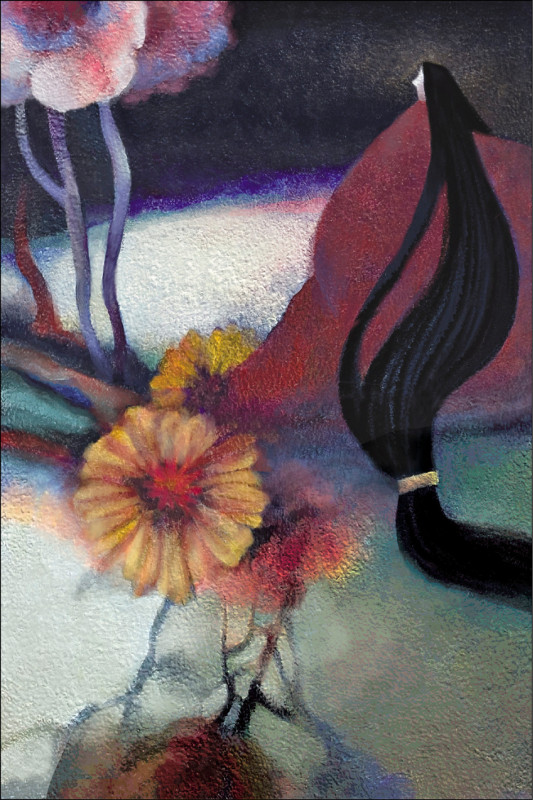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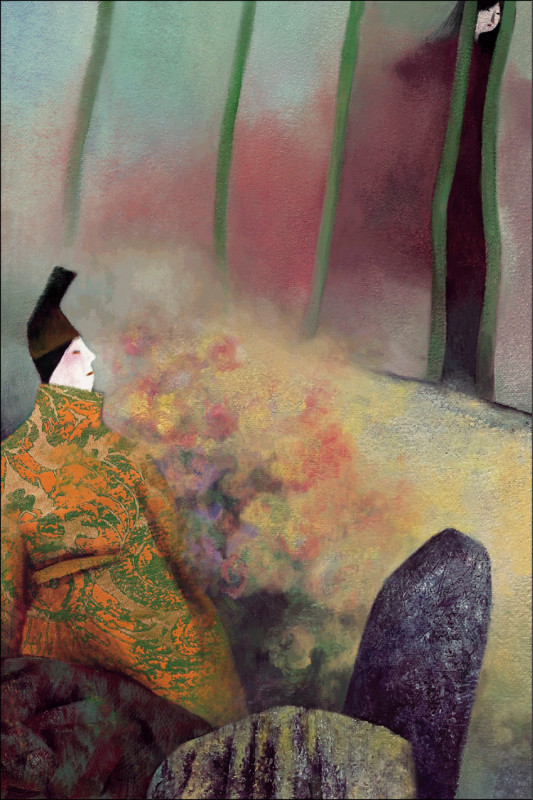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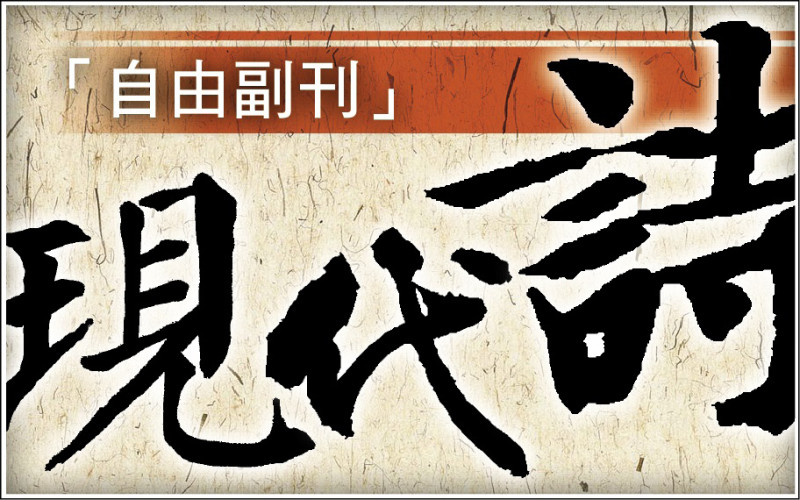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