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書與人】有能力愛人,故鄉就無所不在 - 阮慶岳談《黃昏的故鄉》
 小說家阮慶岳。
(胡舜翔╱攝影)
小說家阮慶岳。
(胡舜翔╱攝影)
專訪◎楊隸亞
 新作《黃昏的故鄉》。
新作《黃昏的故鄉》。
阮慶岳(1957-)的「東湖三部曲」《林秀子一家》、《凱旋高歌》、《蒼人奔鹿》,以及長篇小說《重見白橋》距離現在約有十年了。建築領域出身的他,待過建築事務所,也在大學任教,同時還是小說家,橫跨多重領域的他,在各種角色身分裡游移自如,只要是曾經讀過他作品的讀者們應該都會非常驚訝,他竟是如此擅長描寫女性角色,例如曾滿足、林秀子,那些形象飽滿、愛中堅毅的女人們。
故鄉在孕育發芽
打開《黃昏的故鄉》,這是阮慶岳睽違多年再次出手的長篇小說。這次他寫故鄉,卻一直不斷寫到女性的身體。主角惠君從南部小鎮嫁到北部大城市展開婚姻生活,走得愈遠,身體意識卻愈強烈,童女時期海邊的性啟蒙、同性密友的性愛遊戲扮演,撫摸自己隆起的肚腹,不斷思念起記憶中早已消失去向的母親。問及書名的靈感由何而來?阮慶岳說男歌手文夏所演唱的台語老歌〈黃昏的故鄉〉本來是日本曲,同一個曲調經過好幾重的編寫演繹,改詞、改曲調,其中也增添多重意味,從鄉愁、政治、感情,轉了又轉,每一種相異的轉喻,卻不約而同指向心中不可言說的祕密。
那麼,小說《黃昏的故鄉》裡隱藏的祕密是什麼呢?為何在其中尋找「故鄉」的蹤跡,卻不斷發現身體。故鄉跟身體之間有什麼關聯性?對60年代的女性而言,身體就是一個禁忌話題,總要閃躲、迴避,女性無法勇敢主動地討論身體,就好像在某些年代裡,或某些敏感的時刻,我們無法坦率大聲地討論故鄉。「我來自哪裡?」、「你又是什麼人?」是否必須回溯原鄉,來一趟時光之旅,重新打開母親的肚皮,才能明瞭血脈裡的來去始末。
談到「母親」的形象,阮慶岳笑著說,「曾經研究我作品的評論者認為,我的作品中似乎有戀母的傾向存在,但是事實上真實世界並沒有我的小說裡可直接對應的人物。」《黃昏的故鄉》裡的母親惠君,是一個普通平凡的媽媽,沒有很高的學歷,可是卻能扛起家務與責任,撐起家中經濟、照顧家人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母親就是這樣子,她處理日子中的每一件事,她愛你。這就是最好的媽媽。」那個年代的母親都有相似的共通點,面對人生的抉擇往往擁有很大的直覺、勇氣,在生活裡似乎永遠沒有後悔與懼怕。
鄉土寫實裡的神邏輯
初讀《黃昏的故鄉》前幾章,會以為這是一本偏向鄉土寫實的小說。尤其書本封面乍看是如此「60年代」、「台灣味」。聊到小說封面,阮慶岳表示這是由王志弘設計,封面的字體是最特別之處。看著書本封面伏在黑夜上方,變形的月亮,看似三角形卻不對稱的道路、壓著深沉的海浪。字體則很像60年代或70年代街頭商舖的一些招牌字樣,即使表面的懷舊意味濃厚,但也不全然走「復古風」,不對齊的邊界與特殊剪裁,從最細節之處,反映出一種同時兼具復古與現代的衝突視覺。尤其是書腰,月亮像黃色檸檬,正在變形吞吃日子,好像是逝去的時光啊。
這種奇妙的怪誕感有沒有存在小說情節裡呢?小說的其中一章〈記憶與夢境(病者與傷者)〉突然跳脫前面好幾章的寫實手法,大膽地奔向現代哲學的思考對話,透過父親與兒子爬山的經過,進入完全精神抽象式的空間邏輯。小說裡的父子透過步行向山上走,試圖尋找古早時期已經消逝的泰雅族狩獵場,阮慶岳使用大量神諭式對話,文字節奏充滿音樂性,特別是由兒子口中說出來的對白,也極具神性,充滿寓言啟示的語言。兒子說:「病者只剩餘著記憶的能力,傷者卻依舊可以倚賴夢境過活。記憶本是屬於人間塵世的,一如真理只能屬於死亡;而夢境與想像同樣有著神性的翅膀,是蒙受到天使祝福的,也有能力到達那急湍河流的彼岸。」
為什麼要這麼寫呢?「我一直在思考,小說還有多少可能性?」阮慶岳這時有點嚴肅地說,「小說如果只是寫實白描、敘述人間事,日常生活或者已發生過的瑣事,這不是小說這個文體的特質和使命,小說家甚至必須更有使命感,不僅僅是描繪人間事,必須要有意識且有責任。」難道是要進入神的領域?「是的,類似神學或哲學的部分。」他說。因此,不僅是兒子,連父親也夢見自己變身為一株巨大的蝴蝶蘭,妻子惠君與兒子都變成蝴蝶,在他身旁飛繞。這種種無疑是對生命本質再次的深層思考,看似荒謬怪誕,可獨立於整部小說的大架構之外,但存在其中卻也沒有違和感,這種超展開的「神邏輯」,甚至為故事增添相當現代主義的色彩。
無因的惡,純粹的善
「《黃昏的故鄉》裡面的小兒子,是一個純粹的善者,有點像賈寶玉。我發現要寫一個完全善良乾淨的人,其實是寫作裡最不容易的事。」阮慶岳緩緩道來。「因為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這樣的人物,即便有的話,幾乎也只是存在於小說或電影故事裡。」如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潔淨與髒汙,罪責與救贖,有時候人們做了惡事,但卻是毫無動機的、沒有任何原因,不存在所謂邪惡的意念。在小說接近尾聲的地方,惠君的兩個兒子唯實、唯虛在音樂與迷幻的氛圍裡發生了不倫肉體關係,從取名的層面來看,這兩個角色性格很像鏡子,唯實代表人的現實面(肉體),唯虛代表人的靈性面(神性),「這世界上沒有完全虛、完全實的存在,虛實終究必須互相結合。」阮慶岳說。
如同賈寶玉一樣純善的小兒子,毫無怨言,給予了自身的全部。「愛是從被動的接受轉成主動的付出。」充滿溫柔的母性,就像母親,就像故鄉,愛裡有能量也有拯救。純善的兒子救贖了母親,象徵肉身菩薩的母親也給予兒子無止盡的包容。「如果有能力愛人,故鄉就無所不在。」阮慶岳在訪談的最末說出了這句話,那時咖啡店外已是黃昏時分,他背起帆布包,調整帽沿,走向城市的另一端,街道上所有黃昏的影子彷彿都被他拉得更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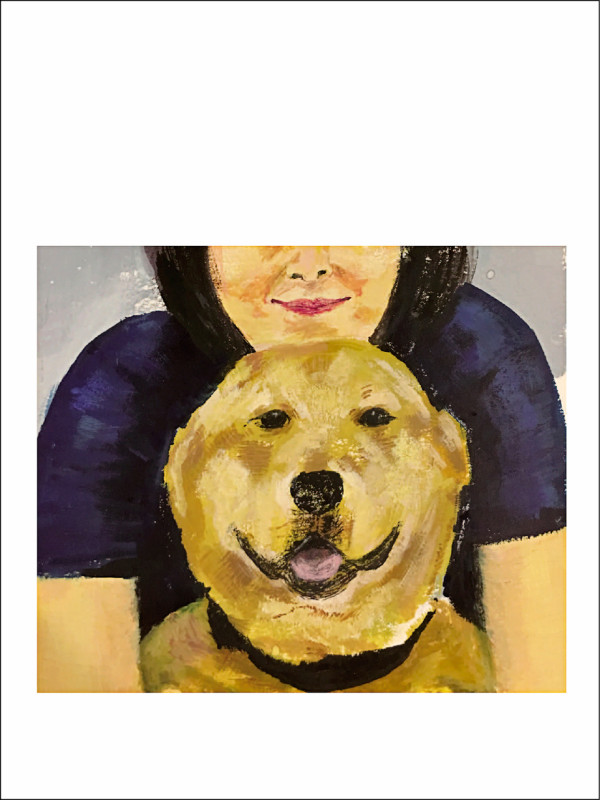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