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鬥陣寫作俱樂部.新詩篇】 凌性傑/在顯微與放大之間,那些我想說的
 ◎凌性傑
◎凌性傑
◎凌性傑
如果一整個宇宙可以凝縮在一首詩裡,我想那是一件很美麗的事。梁靜茹〈情歌〉是這樣唱的:「一整個宇宙,換一顆紅豆。」詩歌做為一種藝術形式,首要任務是喚起直覺與感動。創作者在語言文字裡轉動宇宙,調度時間,噴發畫面,放置聲音,把看似無跡可循的事物統合起來,藉此傳遞某些神祕的訊息。
這些訊息的作用可能是顯微,也可能是放大。閱讀匿名參賽的文學獎新詩稿件,我像是迎接無數的顯微鏡或放大鏡,在有限的訊息裡去探測寫詩的人究竟在想什麼。對我來說,詩心與文字技術的密契,可以縫合世界的裂痕。當個人覺知一一變成可說的,並且在訴說的同時建構美麗的秩序,心領與神會於是都變成藝術。在詩的形式裡進行溝通,我偶爾會對過多的裝飾音感到不耐煩,偶爾會被意象亂流打敗。太過工整的作品讀來也令人疲憊,我想,一首好詩不能只是設計精巧的「換句話說」,也不能只是沒話找話說(虛張聲勢)的戲法。
我喜歡的詩,讓我知道什麼是可以看見的,也讓我知道看見的背後還有許多看不見。我喜歡的詩同時讓我聽見――聽見在快與慢之間,專屬於詩人的呼吸與心跳。聽見詩人與世界對話,微言之中有大義,產生無窮無盡的回音。比如朱國珍的〈Nhari〉:「Nhari,Nhari――/太魯閣族語:快/快,貨櫃車/快開,火車快駛/沒鋪枕木的軌道,小米田/那邊再過去那邊,呼吸/除草劑,焦枯的青春」。以一種簡潔明快的語調,把我帶進思索的歷程裡。又好比鄭聿的〈普快狀態〉:「世界就是這樣/我也是這樣/成為一部分的」,詩裡以普快列車的行進狀態,暗示了生命的遭遇,任憑讀者馳騁想像。零雨〈頭城――悼F〉也是在講搭火車:「列車長來剪票了不知為什麼/他說了謝謝又說旅途愉快/而那正是我想對你說的」。語言是這麼乾淨,將生命雜質過濾殆盡,透過極簡與留白運載暗示,彷彿此心之外再無他物。
只是,此心瞬息萬變,所遇都將成為遺跡。有話想說的時刻,在語詞裡讓世界顯微或放大,說得快一點或慢一點無所謂,那可能就是我最喜歡的,詩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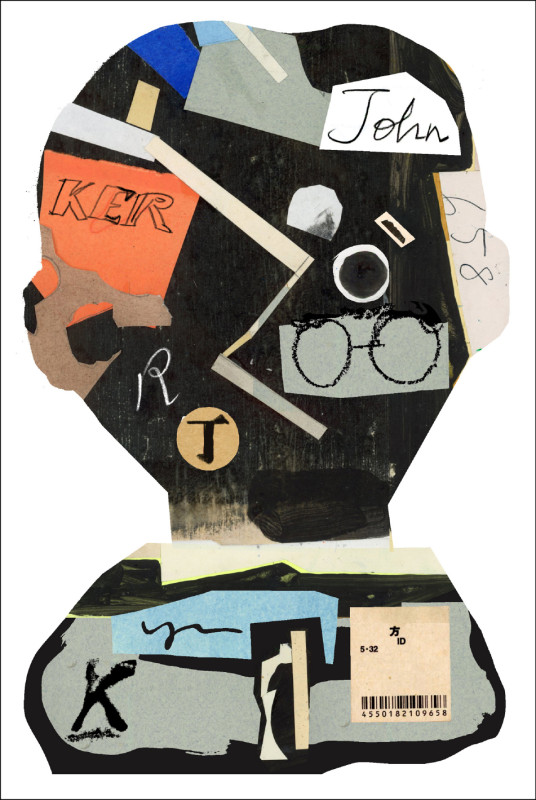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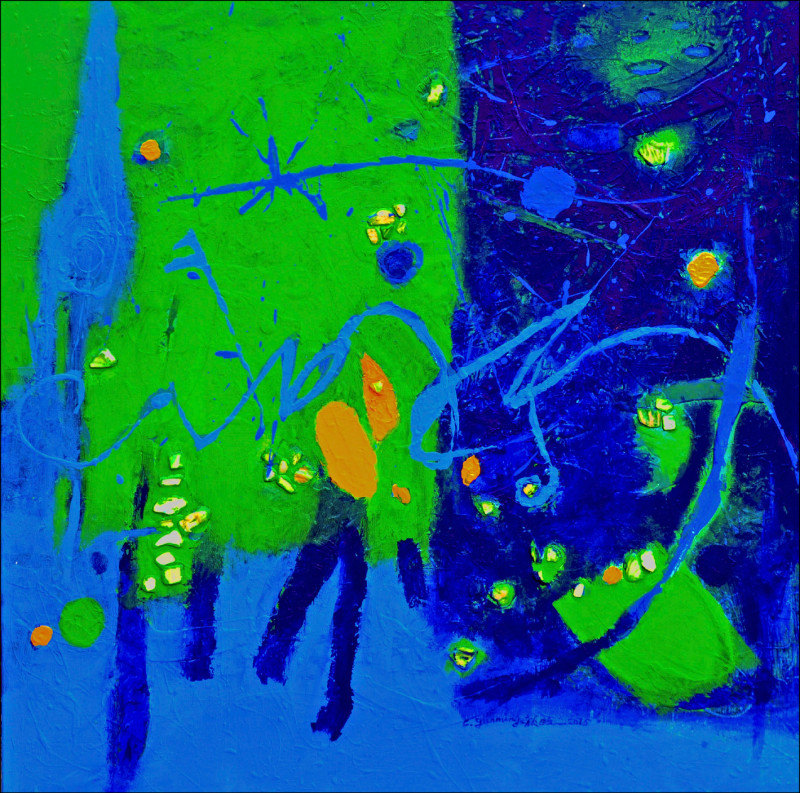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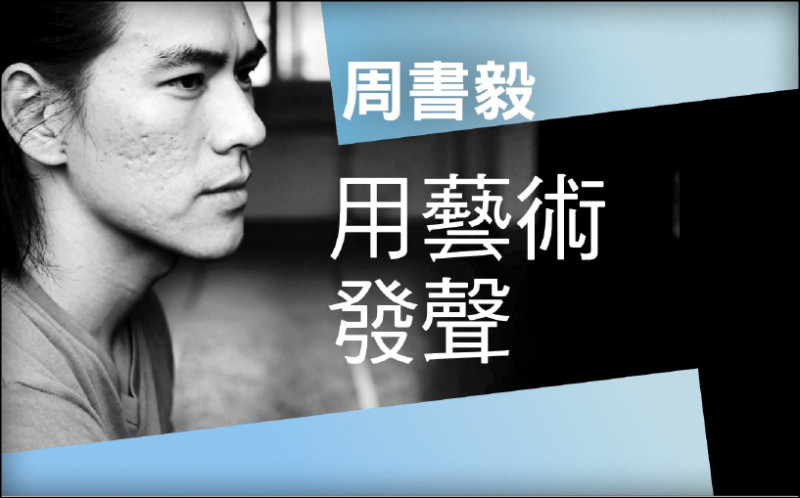
網友回應